1941年,女干部朱凡被俘,为让其招供,日军在监狱中对她施以酷刑,但朱凡宁死不屈,日军怒了,气冲冲地把她拉到湖边,将其双腿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,大吼道:“你说不说?不说我可要开动游艇了!”
脚边,两根粗粝的麻绳死死缠住女子的脚踝,另一头系在两艘汽艇尾部。女子叫朱凡,才21岁。
宁波码头、上海滩、日寇炮弹,这三样东西撞碎了她金丝笼般的少女时代。
朱凡原名陆慧卿,生来含着金汤匙。宁波开明的商人父亲把家业搬进上海滩,十里洋场灯红酒绿,她曾穿着柔软的苏绸,指尖划过进口钢琴的黑白键。
1937年淞沪会战炸碎了玻璃窗,也炸碎了她家的纱厂。
那个傍晚,机器残骸在燃烧,烟尘遮蔽了晚霞。父亲一夜白头,蹲在瓦砾堆里,摸索被炮火熔掉的账本。
钱没了,琴声断了,朱凡的世界掉进冰冷的湖水。
没了工厂,陆家窝在拥挤的弄堂里。放学路上,朱凡总要绕到废弃的纱厂门前。
焦黑的铁架像巨兽肋骨刺向天空,乞丐在墙根瑟缩。
一个拉黄包车的邻居大爷咳嗽着说:“囡囡,日寇的炮弹不长眼啊。”墙头贴的抗日传单被风掀起一角,油墨印着“不做亡国奴”。她轻轻摩挲那排铅字,字字滚烫。
复仇的火种在灰烬里爆燃。她钻进图书馆读报,眼睛粘在“平型关”、“游击战”的铅字上。
共产党人的演讲挤爆租界小礼堂,角落里这个富家女踮着脚尖,听到“解放”两个字时,心跳如鼓。16岁生日那天,她把名字“陆慧卿”亲手写进入党申请书。
朱凡这个名字,就是句斩钉截铁的宣言,舍弃前尘,做凡人中的星辰。
1938年底那个寒夜,朱凡第一次入狱。作为苏常太地区区委书记,她赴上海联络却被叛徒出卖。
老虎凳轧断骨头时她咬碎嘴唇,铁钉钉进指尖时她盯着牢房天窗,窗外是灰蒙蒙的上海天空,她想起父亲佝偻的背。
连续七天刑讯,血痂糊住眼睛,宪兵队长拍桌大叫:“她当自己是块铁!”
三年零八个月,苏州监狱的铁窗没有冻僵她的血。
1941年深冬,新四军奇袭镇江监狱。战友撞开牢门时,朱凡蜷在草堆里,枯瘦如柴。
没人敢信这个眼神呆滞的姑娘竟是区委书记。
她整夜整夜惊醒,牢房的老鼠啃噬声和皮鞭呼啸声纠缠在噩梦里。
只有后腰那道刚结痂的烙铁疤提醒她:你还活着,你的战斗没完。
重回芦苇荡游击区那天,朱凡仰头大口呼吸着江南湿冷的空气。
胸腔里像有只攥紧的手终于松开。她执拗地站在寒风里,细瘦的手指攥成铁拳。
1942年盛夏蝉鸣震耳,太湖边一座破败尼姑庵成了死亡陷阱。
朱凡踏进庵门便心跳骤停,窗外芦苇倒影异常晃动!日军钢盔的冷光刺破门缝。情势千钧一发,新四军首长就在屋内开会。
她猛然撞翻供桌,烛火泼在幔帐上腾起烈焰。
“着火了!快撤!”自己却抓起桌上的驳壳枪,边朝庵门射击边厉声嘶喊。
子弹撕碎木门,她的肩膀绽开血花。冲锋的皮靴声越来越近,她最后砸烂电台,拔出仅剩的手榴弹拉环。
"护着首长过河!别管我!"这是战友跃入水渠前听见她最后的嘶吼。
枪声沉寂后,日本人拖出那个血人时一阵哗然。
"老熟人"宪兵队长狞笑抚摸她的枪伤:"三年前的滋味忘了?"苏州监狱全套酷刑轮番上演,烧红的烙铁压在旧疤上吱吱作响,朱凡昏死又被冰水泼醒。
当带钉的木棒砸碎她膝盖时,她喉咙里滚出模糊字句:"中国......必胜......"
7天后,所有刑具在朱凡面前失效。审讯室墙上日历被血指痕抹去三格。
绝望的日军拖她到阳澄湖边,解开她血肉模糊的双腿,两条血痕蜿蜒在沙地上,像两道决绝的省略号。两艘汽艇轰鸣待发。
军官揪起她的头发:"名字!上级!给你最后五秒!"浑浊的湖面倒映着硝烟天空。
朱凡嘴唇蠕动,众人凑近,却听见她哼起不成调的苏州小曲。
那是她六岁在纱厂后花园,奶妈教她唱过的童谣。
五秒死寂。军官摔掉烟蒂,汽艇油门轰然踩下。
巨大的撕裂声中,湖水瞬间翻涌起两股猩红湍流。岸上日军集体转身呕吐。
朱凡的血染红湖水三天才散,那年她才23岁,没有留下遗照。
上海老宅抽屉深处埋着一本缎面日记,稚嫩的笔迹写着:"若国家需要我的血,我愿为燎原星火。"
七十年后,阳澄湖旅游区的汽艇拉着游客欢笑掠过当年血染的水域。
导游不会指着一处无名湖岸说:1942年夏天,一个叫朱凡的姑娘曾在此处粉身碎骨。
但无数个"朱凡"没入黑暗时的微光,早成了这土地最硬的脊梁。
我们习惯宏大叙事里的炮火硝烟,却容易忽视那些被碾进泥泞的个体命运。
朱凡的壮烈不是突然爆发的火星,而是她亲手点燃的燎原烈焰。
炮弹砸碎钢琴,就拿起枪;酷刑裂其骨,信念亦不折。
这才是最触动人心的力量,是穿透时空的精神丰碑。她短暂的一生如同一把解剖刀,割开那个时代的黑暗,照见理想主义最纯粹的光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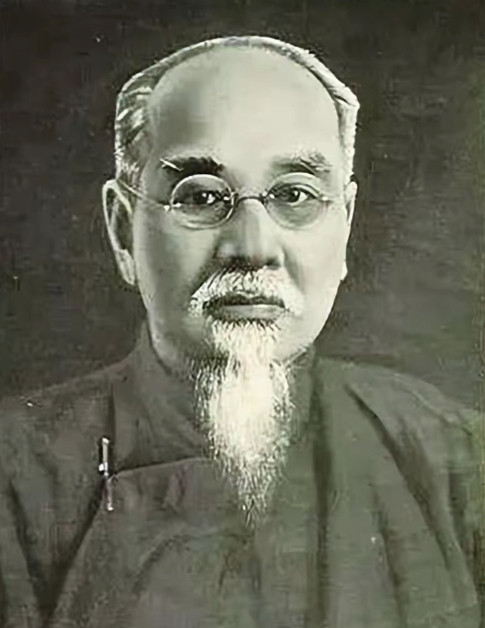






用户18xxx64
抗日英雄,永垂不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