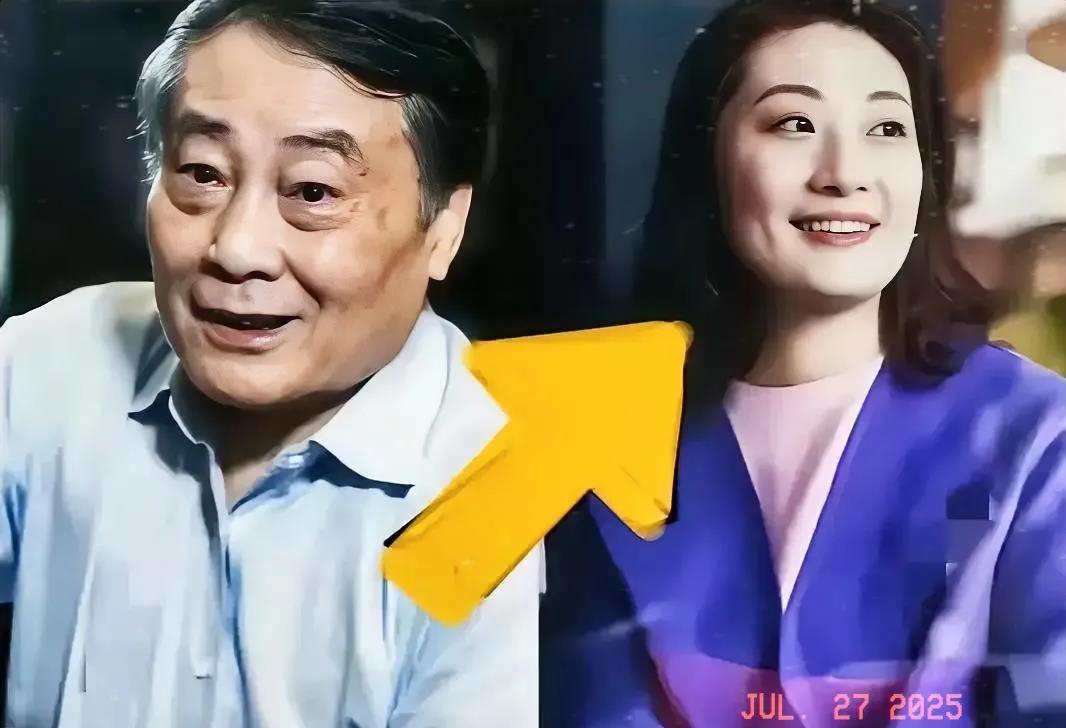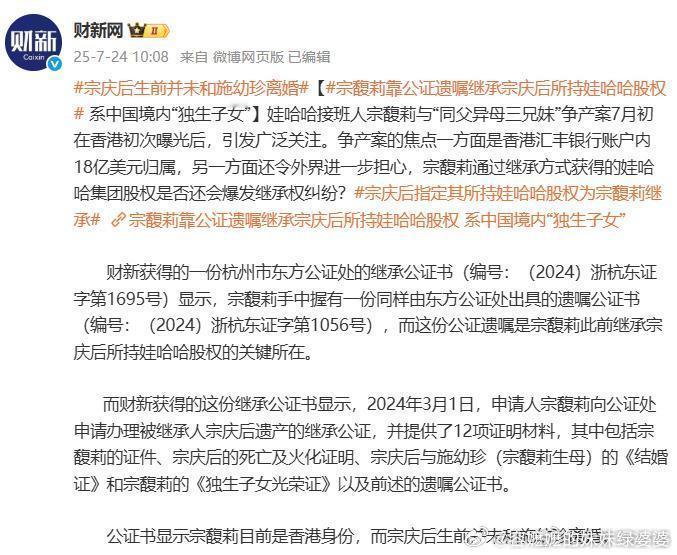1983年,84岁张大千在台北荣总病房病逝,他的遗嘱很快在报纸公布,令人惊讶的是,张大千将遗产分为了16份,其中15份是给陪伴张大千到最后的徐雯波和14位子女,余下一份,则给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孤独老妇杨宛君。
杨宛君是谁?张大千生前最后数十年在台湾风光无限,家财万贯,这位北京的妇人怎会占据遗嘱的一角?
时间倒转半个世纪,1935年的北平,天桥杂耍场旁的小戏园子里锣鼓喧天。
台上亭亭玉立的是京韵大鼓新秀杨宛君,芳龄十八,一曲《黛玉葬花》唱得哀婉凄绝,嗓音清亮,眼波流转处尽是灵气。
台下一位留着长须、目光炯炯的中年男人看得出了神——他就是名满画坛的张大千。
那个夜晚张大千彻夜未眠,次日一早,一幅惟妙惟肖的杨宛君仕女图,被恭敬地送到了她手中。
看着绢纸上那个宛若天仙的自己,杨宛君心头一颤。
可对方已有两房太太,年龄更比自己长了整整十八岁……这哪是一般姑娘敢走的路?
张大千没放弃,他搬动了二太太黄凝素亲临杨家说媒。
“妹妹放心,大千是真心的,必以正妻之礼相迎,婚事由大太太曾庆蓉亲自操持。”
这份许诺彻底击垮了杨宛君的犹疑,那一年,她放下蒸蒸日上的事业,成了名画家张大千的三夫人。
初嫁的光阴确实绚烂,张大千宠她至极,爱吃的点心,特聘的厨子;采风游历,总要带上她一路同行。她以为这份浓情会持续一生。
命运的转折点在西北风沙中到来,1941年,一心追寻敦煌壁画的张大千决意西行,目的地是莫高窟。
黄沙漫天、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挡不住杨宛君的追随。
她不知道这次旅程竟会拖上三年。敦煌缺水少粮,风沙似刀。
除了当助手,她还要在寒冬清晨烧水为丈夫化开冻墨。风沙和寒冷侵蚀着她曾经鲜亮的容颜。
“跟着他在那洞窟里待着,四面都是佛爷,灰都呛人……”杨宛君晚年如是回忆敦煌的日子。
那三年,她以健康为代价守护了丈夫的艺术追求。
张大千摹得数百幅壁画,声名更上层楼,杨宛君的青春却永远埋葬在塞外风沙中。
风光回京不久,感情冷却的迹象悄然显露。
更大的风波在几年后席卷张家,1947年,48岁的张大千热烈痴迷上了女儿的同窗好友,年仅18岁的徐雯波。
这一次,杨宛君成了反对最激烈的人。“他又要祸害别人家的好姑娘!”她不希望又一个少女重蹈自己的覆辙。
只是张大千心意已决,顶着全家反对,徐雯波终究进了门,成为张家的第四位夫人。
杨宛君在丈夫心中的位置,早已随年华老去与容颜不再日渐下滑。
历史的洪流很快汹涌而至,1949年,动荡局势迫使张大千必须离开大陆。仓促中,他只弄到三张飞往台湾的机票。
生死离别的时刻,张大千面临痛苦抉择:妻儿太多,机票太少。
那天晚上,家里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。
张大千紧锁眉头,最终开口:“宛君……你留在北京,照看老宅吧。”这句话抽干了杨宛君全身的力气。
被留下的杨宛君只喃喃问了一句:“这一留,得多少年?”张大千沉默无言。他留给北京的最后一句嘱咐是:“等安稳些,我来接你。”
这一句空话成了杨宛君余生最深的羁绊,张大千在台湾徐雯波的陪伴下如鱼得水,再度开创事业高峰。
而杨宛君一个人在北京,守着空寂的院落。
她等啊等,等来的却是两岸隔绝的消息。
曾经的“三夫人”成了敏感符号,一度生计艰难,靠变卖旧衣物、做零工度日。
岁月将昔日的才女佳人,熬成了北京胡同里一个沉默寡言的孤寡老人。
1983年4月,辗转传回的消息证实了张大千在台湾去世的噩耗。
几个月后,一封意外的台湾来信告知她:那位已远别三十四载的前夫,在遗嘱中划出了一笔遗产留给她。
握着那份遗嘱通知书,杨宛君在清冷的小屋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没有激烈的悲喜,只有彻骨的冰凉穿透了三十四年的孤寂时光。
“他这算什么呢?”是补偿戈壁滩上蚀骨的风沙?还是慰藉几十年独处的荒凉?亦或仅仅是一次迟到的良知发现?
那一份冷冰冰的金钱,与她付出的青春、健康、无望的守候相比,显得如此空洞而苍白。
张大千画过的仕女图千千万,唯有杨宛君这幅,被他亲手绘下,又亲手褪去了鲜活色彩。
那份遗嘱中的十六分之一,犹如一枚迟到数十年的印章,盖在了一幅早已暗淡斑驳的人生画卷角落,诉说着一段早已破碎、却始终未能真正尘封的往事,以及一位女子在时代巨浪中被轻飘飘抛弃的苍凉一生。
杨宛君最终活到了1990年代初,晚年的她极少再触碰往事,唯有谈起敦煌风沙时,浑浊的眼中会闪过复杂的光芒。
那束光里,有痛苦,有倔强,或许也有一丝属于青春年代的痴迷,早已风干在岁月的尘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