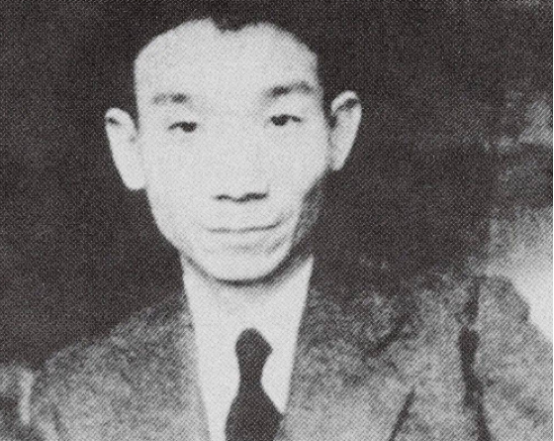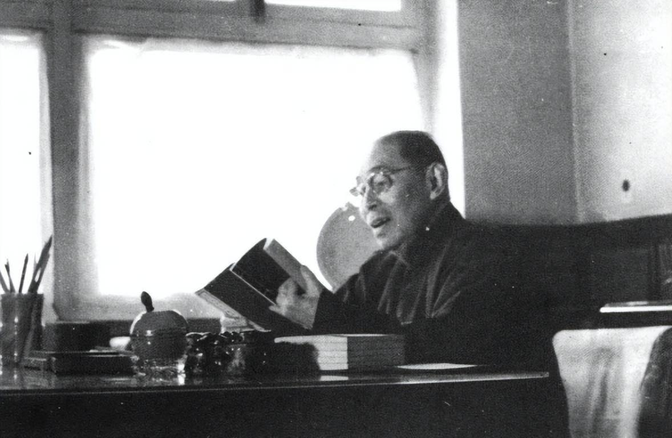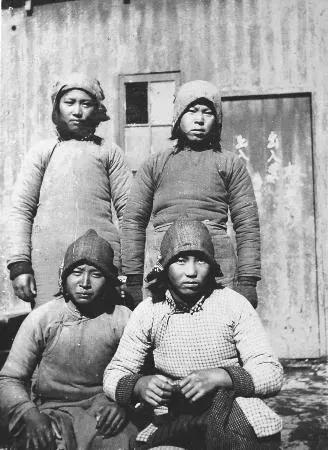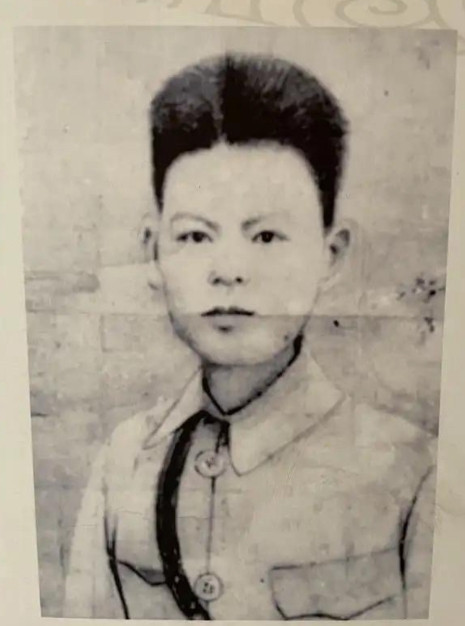1919年,20多岁的郁达夫直接跑到了青楼寻欢,但他向老妈妈提出一个奇葩要求:找一个最老且最难看的姑娘过来服侍他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城里,青楼街上人来人往,这里本是个靠脂粉和笑脸堆起来的销金窟,却在这天遇上一位奇怪的客人。
二十出头的郁达夫裹着灰布长衫,额头渗着薄汗,风风火火跨进了一家青楼的门槛。
老妈妈堆着笑迎上来,却听见这位年轻客人张口就要找最年老、最不好看的姑娘。
她捏着手绢的手指抖了抖,她在这行当摸爬多年,还是头回听见这等荒唐要求,但看对方面色严肃,袖管下还带着钢笔的墨渍,倒像个读书人的模样,也不好直接赶人。
后院的杂役房里蹲着个胖乎乎的身影正在洗衣裳,脸上沾着黑灰也顾不得擦。
这人叫海棠,当年家破人亡流落至此,平时嫌她模样粗笨,平日里只叫她劈柴烧水,这会儿被拽到前厅时,单眼皮肿得像桃子,身上还裹着灰扑扑的粗布围裙。
郁达夫的眼睛却亮了,海棠这副模样活脱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苦菜花,脸颊的淤青还带着锅灰,粗布褂子裹着圆墩墩的身子。
他随手掏出一块银元拍在桌上,当夜就留在了海棠房里,第二日离开时,这穷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竟留话要赎她出去。
这事背后藏着段蹊跷,郁达夫那阵子正闹心病,报社催着约稿,手里的钢笔却像生了锈。
他在租来的小阁楼里枯坐三日,揉烂的稿纸把桌脚都埋了半截,直到有天路过青楼街,突生奇想要去寻些"人间真苦相"——这话是他后来在书里写透的。
那些惯会巧笑嫣然的年轻姑娘入不得他的眼,反倒是海棠那未施脂粉的脸蛋上,皱纹里都嵌着血泪故事。
海棠的命确实比黄连还苦,原本是山西富商家的独苗,十五岁那年土匪洗宅子,爹娘倒在了血泊里。
她裹着床单躲进牲口棚捱过一宿,第二天揣着两根金簪子去投奔亲戚,半道让胡子劫了,山匪头子掀开她的刘海就直咧嘴,转手把她卖给青楼当杂役。
老妈妈也看不上这姑娘:腰粗得赛磨盘,单眼皮耷拉着看人,倒被安排去后院管灶火。
郁达夫偏就看中了这份粗砺,他们在柴房后头絮絮叨叨说了整宿,弄堂里的蟋蟀都睡了两轮。
海棠把腌了十年的苦水一股脑往外倒,说到爹娘惨死时鼻涕眼泪糊了满襟,天亮时郁达夫的笔记本已经密密麻麻写满小字,临走前他摘下眼镜擦了擦,说明日再带稿费来。
三个月后沪上书局出了本新小说,主角是个命比纸薄的青楼苦役,书里描写得极细致:油灯照着她缺了口的门牙,鬓角的白发在夜风里打着卷儿。
文人圈里议论纷纷,有人说是照着八大胡同某位写的,茶楼酒肆开始传海棠的名号,不少闲人跑去青楼要看这位"活菩萨"。
老妈妈精得跟猴似的,把海棠从灶台边拖出来梳洗打扮,硬是炒成了头牌——虽说模样还是那个模样,但沾了文曲星的墨香,倒成了苦命人的象征。
郁达夫倒也没食言,来年开春河水化冻的时候,他当真把海棠接出了火坑。
巷子口晒太阳的老头瞧得真真儿的:海棠穿着八成新的蓝布衫,胳膊弯挎着碎花包袱,临走前还给门口的看门狗喂了半块烙饼。
据说她在城东菜市口盘了间小杂货铺,卖针头线脑兼帮人写书信,逢年过节郁达夫还会差人送点红糖糕,说是念着当年那段奇缘。
这事后来被收进民国奇谭录,说海棠这辈子算是被支钢笔救了的,不过据北平《晨报》民国十年的报道,郁达夫确实在当年创作低谷期频繁出入市井场所,其代表作《沉沦》中某些细节描写也印证了这段经历。
中央研究院近年整理的上世纪文人档案显示,郁达夫资助过数名底层妇女,虽未直接提及海棠姓名,但时间线与坊间传闻颇为吻合。
最后说句实在话,海棠的故事能传这么广,说到底还是沾了读书人的光。
如今东四胡同的老墙根下,偶尔还能听见晒太阳的老头咂着嘴念叨:当年要是没遇上那个戴眼镜的书呆子,海棠这苦命丫头怕是要在后厨洗一辈子碗碟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