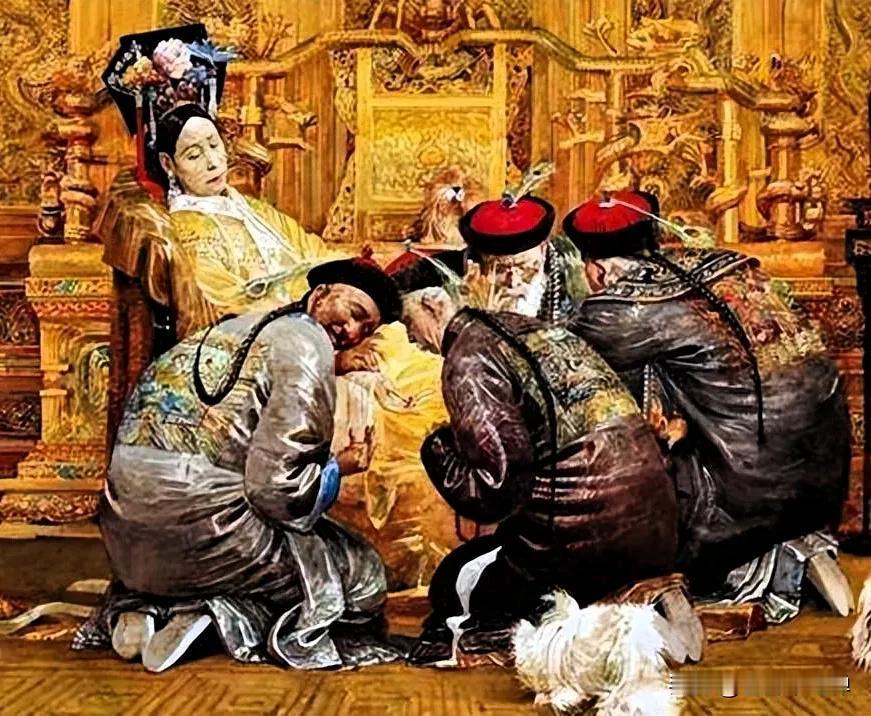1154年,23岁的俊美状元郎出任临江县令,看上了一个美貌尼姑,要与对方好,尼姑将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,却瞧上了状元的好友。数年后两人的丑事被告到了状元郎处,他该如何判?
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冬,淮西才子张孝祥踏着官道上的残雪赴任临江县令,这位二十三岁的新科状元本该春风得意,却在青石镇外的女贞庵里栽了跟头。
庵里那位抚琴的妙龄女尼陈妙常,不仅拒绝了他即兴所作的艳词,还赠了首《杨柳枝》让他碰了满鼻子灰。
要说这张孝祥可不是寻常人物,祖上是唐代诗人张籍,自己又是高宗皇帝钦点的状元,那年月能在殿试中压过秦桧的孙子夺魁,足见其才学胆识。
可偏偏这个在朝堂上敢为岳飞鸣冤的硬骨头,对着庵堂里抚琴的女尼竟乱了方寸。
他在月下听琴时写的艳词,什么"云锁洞房归去晚",什么"无计到巫山",活脱脱像个轻浮浪子,哪还有半点状元郎的体面。
这陈妙常也非等闲之辈,本是临江官宦千金,因自幼体弱被送入空门,倒养出副清冷性子。
她回赠的那阙《杨柳枝》,字字句句透着看破红尘的淡然:"独坐洞房谁是伴?一炉烟。"可谁能想到,这般冰清玉洁的女子,后来会为个落第书生破了戒?
后来,张孝祥的同窗潘必身上发生了件事情,这个屡试不第的书生听了状元郎的艳遇,反倒起了心思。
他收拾行囊住进女贞庵隔壁,每日不是讨教琴谱就是切磋诗文,有回暴雨突至,潘必正浑身湿透还陪着陈妙常抄经,手指相触的瞬间,小尼姑手里的毛笔"啪嗒"掉在了《金刚经》上。
要说潘必正的手段确实高明,他填了首《玉簪记》试探,词里藏着"曾许彩鸾同跨"的私心,偏又装作正经模样请陈妙常指教。
女尼翻开经卷时,突然飘落一纸艳词:"强将津唾咽凡心,怎奈凡心转盛。"潘必正当即逮住把柄:"出家人也动了凡心?"臊得陈妙常面红耳赤。
这层窗户纸捅破后,青灯古佛再困不住少女情怀,等到陈妙常珠胎暗结的消息传开,整个临江县都炸了锅。
按大宋律例,僧尼犯戒要受杖刑,可张孝祥接到诉状后,盯着案卷上"潘陈私通"四个字,想起自己当年在庵堂吃瘪的窘态,竟生出几分惺惺相惜。
要说这位状元郎确实有机智,他当堂判了个"指腹为婚,战乱失散",还亲自作证说两家早有婚约。
百姓们看着陈妙常还俗换上红妆,潘必正牵着新娘拜堂,倒把桩丑闻变成了佳话,后来有文人戏作打油诗:"短发蓬松缘未匀,袈裟脱却着红裙",说的就是这桩风流案。
这事看着荒唐,细究起来却透着南宋社会的机巧,彼时佛道盛行,官家女子带发修行蔚然成风,《宋史》里记载的"寄名"习俗,正是陈妙常这类故事的土壤。
而张孝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成全好友,恐怕也因自己吃过秦桧的亏,当年他为父鸣冤下狱,最知身不由己的苦处。
值得玩味的是陈妙常那首《西江月》,"遍身欲火难禁"这般露骨词句,竟被收录进《全宋词》,可见宋人对情欲的态度远比想象中开明。
而潘必正后来考中进士,带着妻儿赴任时,坊间又传这是"观音送子"的吉兆,百姓们早把清规戒律抛在脑后,只顾着给才子佳人的故事添油加醋。
说到底,这场风波里最亏的倒是张孝祥,他给好友做了嫁衣不说,后来在官场屡遭排挤,三十八岁便英年早逝。
反倒是潘陈夫妇隐居芜湖,活到儿孙满堂,如今青石镇外的女贞庵早成废墟,唯有陈妙常的艳词还在戏台上咿咿呀呀地唱,倒比正经史书记得真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