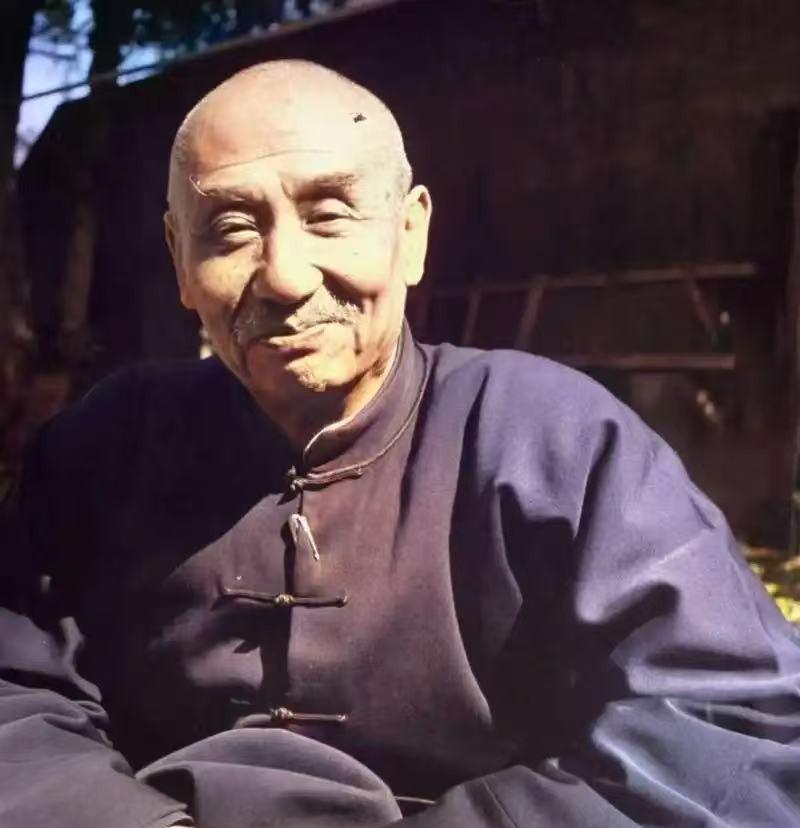1928年初,韩复榘花了1.7万银元和2000袋面粉收买巨匪刘黑七,刘黑七收了东西后毫无表示,韩复榘大怒,派人去捉住了刘黑七的老婆吴宗兰。
1925年春天的沂蒙山区,刘桂棠站在山坡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土屋茅舍,黝黑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。
这个后来被称作刘黑七的年轻人,此刻正指挥着上千名土匪将村庄团团围住,他抬手摸了摸腰间锃亮的驳壳枪,这是上个月从溃败的北洋军手里缴获的。
自从八年前带着七个拜把兄弟落草为寇,他的队伍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,如今连官府也要忌惮三分。
韩复榘坐在指挥部里,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檀木桌面,窗外春雨绵绵,却浇不灭他心头的焦躁。
刚接手山东防务的他急需扩充实力,盘踞鲁南的刘黑七匪帮成了他眼中的肥肉,副官递上最新情报:刘匪部众已逾万人,装备着从溃军处劫来的德式步枪,最近刚洗劫了临沂商会,劫得白银三十万两。
韩复榘眯起眼睛,抓起案头的青花茶碗又重重放下,溅出的茶水在作战地图上洇开一团墨迹。
1928年正月初八,济南城还飘着细雪,韩复榘的特使带着二十辆骡车,满载着银元和面粉,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三天三夜。
刘黑七蹲在碾盘上,抓起把白面在指间揉搓,突然放声大笑:"韩主席倒是大方,这白面够弟兄们包半年饺子了。"
前来劝降的陈席之刚要开口,就被他抬手打断:"回去告诉韩主席,我刘某人最讲义气,收了礼自然要办事。"
当夜,山寨里灯火通明,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,谁也没注意他们的头领悄悄派了亲信往南京方向送信。
吴宗兰蜷缩在柴房的草堆里,听着远处军营操练的号子声,这是她被韩复榘扣押的第七天,手腕上的麻绳勒出道道血痕。
她想起三个月前那个雨夜,刘黑七带着浑身酒气踹开房门,把偷情的她和张连长从被窝里拖出来。
要不是参谋长求情,那晚两人就该吃枪子了,柴房木门吱呀作响,韩复榘背光而立的身影在地面投下长长的阴影。
"你家男人真是铁石心肠。"新任省主席咬着后槽牙,手里的马鞭几乎要攥出水来,吴宗兰别过脸去,她知道那个男人巴不得借刀杀人。
南京总统府的会客厅里,何应钦接过刘黑七的亲笔信,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精光。
副官附耳低语:"这土匪头子要价可不低,开口就要个师长头衔。"
何应钦捻着八字胡轻笑:"给他!北伐正需要这样的地头蛇。"远在山东的韩复榘此时才接到密报,气得掀翻了整桌酒席,他精心准备的银元面粉,全成了刘黑七投奔何应钦的嫁妆。
这场闹剧般的招安暴露出军阀时代的荒诞逻辑,刘黑七带着新编第四师的番号招摇过市时,韩复榘正对着军事地图发狠:"早晚要扒了这孙子的皮!"
而蹲在莒县大牢里的吴宗兰,此刻反倒成了最轻松的人,当狱卒解开她脚镣时,这个被丈夫厌弃的女人竟笑出了声,她比谁都清楚,那个黑脸汉子最擅长的就是翻脸不认人。
1931年寒冬,当刘黑七的老娘被韩复榘从锅泉村带走时,这个土匪头子正在热河与日本人推杯换盏。
酒过三巡,关东军代表递上委任状:"第三路军总指挥,刘桑意下如何?"刘黑七蘸着酒水在桌面上画圈,突然想起七年前韩复榘送来的那车白面。
他咧嘴露出满口黄牙,伸手抓过委任状时,袖口露出的瑞士金表闪着冷光,这是上月洗劫沈阳富商时得的战利品。
时间来到1943年深秋,柱子村的打谷场上,八路军战士何荣贵屏住呼吸,月光下那个翻墙的黑影正是追剿多年的魔头,十八岁的农家少年手指扣上扳机。
枪声响起的刹那,刘黑七恍惚看见韩复榘在笑,看见何应钦在摇头,看见二十年前那七个拜把兄弟在山头歃血为盟。
这个辗转投靠过阎锡山、张学良、日本人、国民党,制造过白马峪惨案,发明过"放天花"酷刑的混世魔王,最终以最普通的方式结束了罪恶一生,像栽进粪堆一般,金牙在月光下闪着最后的微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