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一曼牺牲前有多凄惨?日军晚年回忆:她的惨叫像来自地狱的声音 日军的审讯室在珠河县城的关帝庙里,阴暗潮湿,墙角堆着沾血的刑具:烧红的烙铁、生锈的老虎凳、浸过盐水的皮鞭。赵一曼被抓时左腿中了枪,伤口还在流脓,日军没给她治伤,直接把她拖进了这里。第一个审讯她的是日军少尉山浦君,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:“她进门时抬着头,军装被血浸透,却像披着铠甲,眼神里的恨能烧死人。” 山浦君问她“抗联的粮仓在哪”,赵一曼只冷冷地说“不知道”。皮鞭抽在身上,血珠溅在青砖地上,她咬着牙不吭一声。山浦君急了,让人把烧红的烙铁按在她的胳膊上,“滋啦”一声,皮肉焦糊的味道弥漫开来,她猛地疼得弓起身子,额头的汗珠子砸在地上,却硬是没叫出声,只是盯着山浦君说:“你们烧的是我的肉,烧不掉中国人的骨头。” 这样的审讯持续了一个月。日军换了三拨人,用尽了酷刑:灌辣椒水灌到她肺里出血,绑在老虎凳上垫到三块砖让她腿骨咯吱作响,甚至用钢针戳她的指甲缝。有次审讯到半夜,看守偷偷听见她在牢房里哼歌,调子是东北的民谣,断断续续的,像在哄谁睡觉——后来才知道,她是在想儿子陈掖贤,小名叫宁儿,当时才7岁。 她给儿子的遗书,就是在这样的折磨中写的。日军见硬的不行,假意给她纸和笔,想让她写“悔过书”,她却写下:“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,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,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!”写的时候,她的右手被刑具夹得肿成了馒头,笔握不住,就用左手扶着,一笔一划,字迹歪歪扭扭,却每个字都像钉子,钉在纸上。 8月1日,日军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,决定处决她。行刑前,他们把她绑在马车上游街,想让老百姓看看“反抗者”的下场。可珠河的百姓们低着头,没人敢看,却有人偷偷往路上扔鸡蛋、窝头——那是给她的最后一点温暖。赵一曼看着熟悉的街道,突然对押解的日军说:“我要再唱首歌。”她唱的是《红旗歌》,声音沙哑,却字字清晰,马车上的日军愣住了,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人,都快死了,眼里还闪着光。 8月2日中午,刑场设在珠河县城南门外。赵一曼站在土坡上,阳光照在她脸上,她闭上眼,像是想起了宁儿的笑脸。枪声响起时,她倒在血泊里,手里还攥着那封没寄出的遗书。后来打扫刑场的老乡说,她的指甲全被拔掉了,胳膊上的皮肉焦黑一片,可嘴角却带着点笑意——像是终于能去见儿子了。 日军晚年回忆起那段日子,总说“她的惨叫不是因为疼,是因为恨”。他们不明白,为什么一个女人能扛住这么多酷刑,为什么宁愿死也不肯说一句软话。其实答案藏在她的遗书里:她不是不怕疼,是怕对不起那些跟着她打鬼子的弟兄,怕对不起还没长大的宁儿,更怕对不起这片被日军践踏的土地。 赵一曼的凄惨,不是肉体的痛苦,是一个母亲与儿子永别的不舍,是一个战士未能亲眼见胜利的遗憾。可她的坚贞,却像黑夜里的星,照亮了后来者的路。宁儿长大后,读到母亲的遗书,说“我懂了,妈妈是想让我活在一个没有鬼子的中国”——这,正是赵一曼用生命换来的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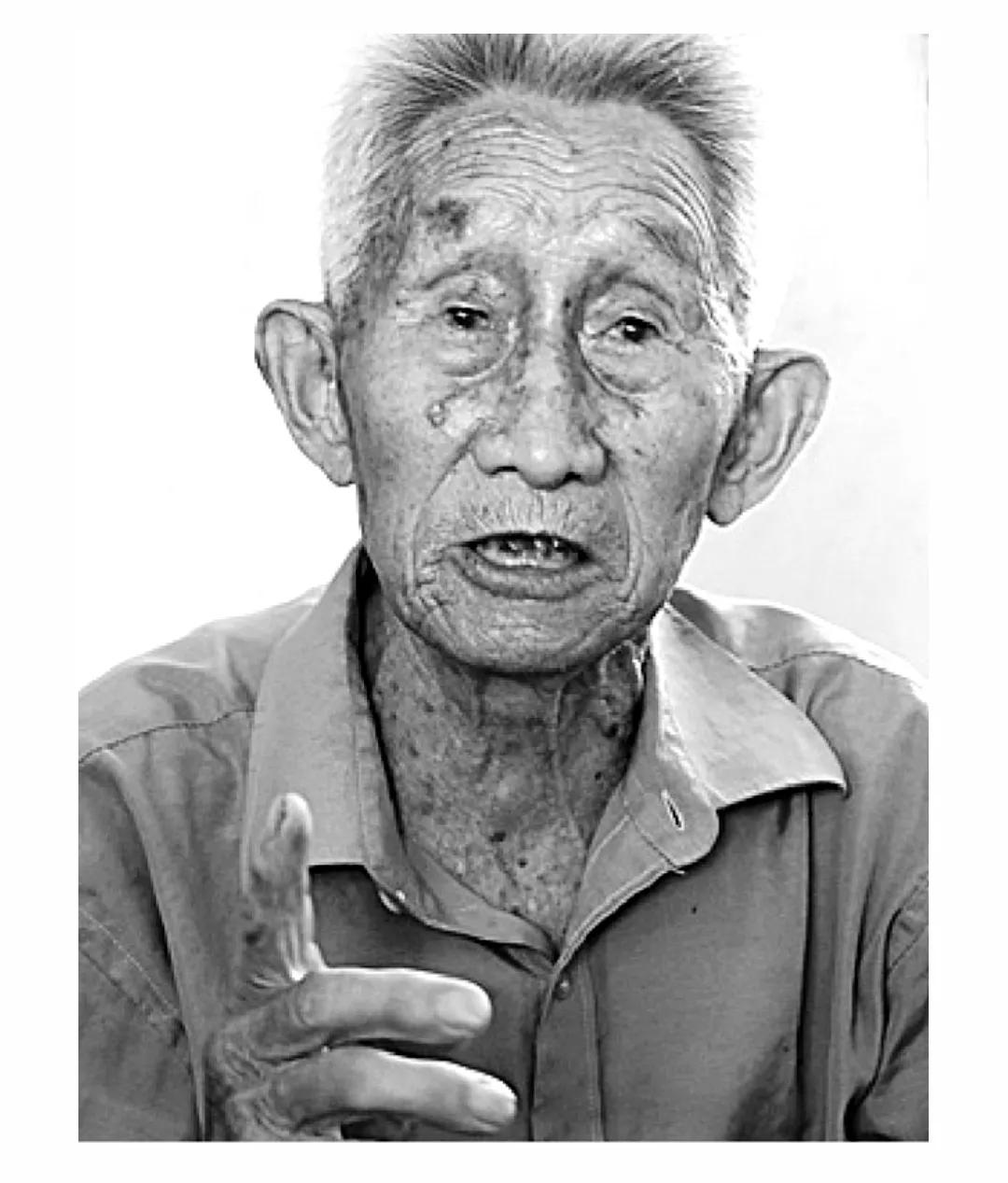







每天爱你多一些
勿忘国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