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,新疆妇人阿尼帕在街上发现一名衣衫破旧的11岁汉族女孩,只见这个女孩在垃圾桶里不停翻找,善良的阿尼帕最终将其带回了家,在那里,小女孩见到了其他十几个同样被阿尼帕收养的孩子,这些孩子甚至来自不同的民族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,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,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,感谢您的支持! 1977年,新疆青河县的寒风像刀子般割在脸上,街头行人稀少,昏黄的路灯下,菜市场拐角处的垃圾桶旁蹲着一个瘦小的身影,她不过十一岁左右,身上裹着一件棉絮外翻的破旧棉衣,袖口裂开,露出灰黑的棉花,脚趾从开裂的鞋面里探出来,冻得通红。 她双手不停在桶里翻找,似乎想找出一口能下肚的东西,头发纠结成硬块,黏着污垢和干涸的脓痂,远远便能闻到一股酸馊的气味。 阿尼帕从集市回家的路正好经过这里,她驻足片刻,心头一紧,这个女人出身在青河县,常年在食品厂做苦力,深知饥饿和寒冷的滋味,她走近,仔细看了看那双发紫的小手,犹豫了一瞬,便伸手将女孩拉起,寒风里,她的手掌粗糙却温热,紧紧握着那只冰凉的手,径直带着她向家走去。 推开院门,一股热气夹着饭香涌出来,屋里不大的土坯房被炉火照得通亮,炕上和地上坐满了孩子,有的五官深刻,有的圆脸细眼,说话时夹杂着不同的口音,炕角的大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几个年纪大的孩子忙着盛饭,另有几个在添柴。 这个热闹的场景让刚进门的女孩怔住,她没想到,在这间并不宽敞的屋子里,会聚着这么多不同面孔的孩子。 阿尼帕领着她到炕边坐下,又去屋后烧了两大锅热水,她先用温水将女孩头发上的硬痂一点点泡软,再用棉签蘸着药膏轻轻涂抹。 药膏是前几天她跑遍附近诊所才买到的,花掉了家里原本预备买煤的钱,屋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,屋里的动作却缓慢而细致,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兽,女孩低着头,第一次感到陌生却踏实的温暖。 这个家并非偶然形成,早在六十年代,阿尼帕的邻居,一对哈萨克族夫妇因病去世,留下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那时她自己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,丈夫阿比包在县里工作,收入不高,还要供养家中多个亲人,生活本已拮据。 夜里听到那几个孩子在屋外哭,她辗转反侧,天亮后便将他们接进了家,从那以后,被遗弃或无家可归的孩子陆续走进这个院子,家里的人数像滚雪球般增加。 为了养活这么多孩子,夫妻俩日夜忙碌,阿比包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工地打土坯,一块赚两分钱,一晚上能干上三百多块,常常磨破手掌。 阿尼帕生完小女儿不到十天就到河边给食品厂洗羊肠子,冬天的河面结着冰,她用石头凿开一个口,跪在岸边,把手伸进刺骨的水里反复搓洗,回家时双手像红萝卜一样肿胀,裂口渗着血。 家里日子虽苦,但规矩和温情并行,无论哪个民族的孩子,来了就是一家人,节日不分先后,古尔邦节要过,春节也要过,谁在学校进步了,就会有一顿特别的抓饭。 饭桌上,大的照顾小的,不会用筷子的学会用筷子,不会抓饭的也学会用手抓饭,阿尼帕常让孩子们结成对子,一个汉族孩子配一个少数民族孩子,互相学语言,久而久之,家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混合语言。 不时也会有小摩擦,一次,两个女孩为了同一条裙子闹得不愉快,阿尼帕没有偏袒,而是找来旧布料,让所有女孩子围在一起动手缝新裙子,缝到最后,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一件属于自己的花裙子,笑声盖过了之前的争执。 随着时间推移,当初瘦弱怯懦的汉族女孩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,几个月后,阿尼帕帮她找回了流落在外的三个兄妹,让他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团聚,饭桌上,四个孩子坐在一起,吃着热气腾腾的拉条子,神情久违地放松。 这些孩子慢慢长大,走向不同的人生,有人成了医生,在医院用三种语言安慰病人,有人当了老师,把所学传递给下一代,有人选择资助贫困学生,把温暖传递出去。 节日时,他们常带着家人回到青河县这个院子,那口大铁锅依旧架在灶上,锅底厚厚的烟垢像沉默的见证者,记录着几十年间的辛劳与团结。 多年后,记者来采访,正赶上院子里热闹的聚会,院子里摆满餐桌,哈萨克族女婿忙着烤全羊,汉族媳妇在擀饺子皮,回族的儿子炸油香。 孩子们用汉语、维语、哈语唱着歌,笑声和香气交织在一起,阿尼帕坐在炕沿,白发梳得整齐,眼神温和,仿佛在看一幅活生生的长卷。 这个家让人明白,亲情不仅限于血缘,跨越民族的善意和接纳可以把人紧紧连在一起,阿尼帕用几十年的时间,让十九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,在一口大铁锅升起的炊烟中,找到了同一个家。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说出您的想法! 信息来源:“传奇妈妈”阿尼帕——新华网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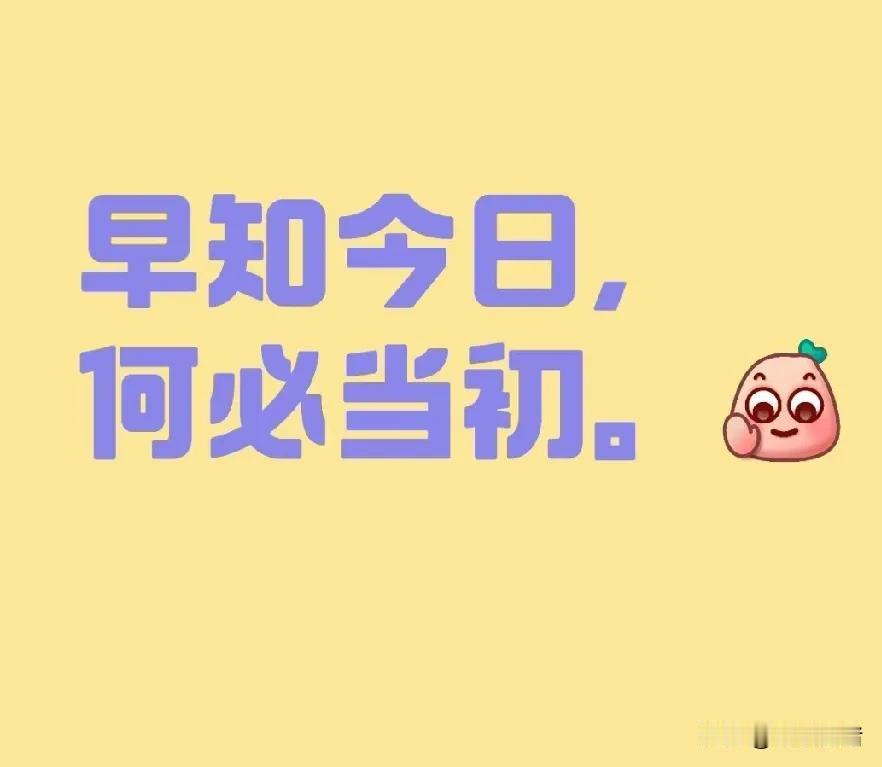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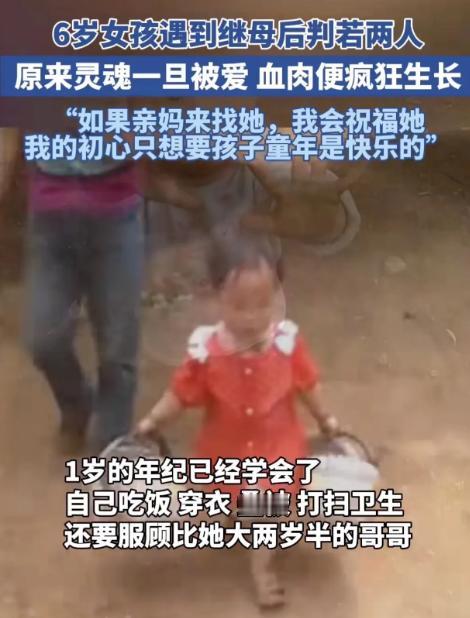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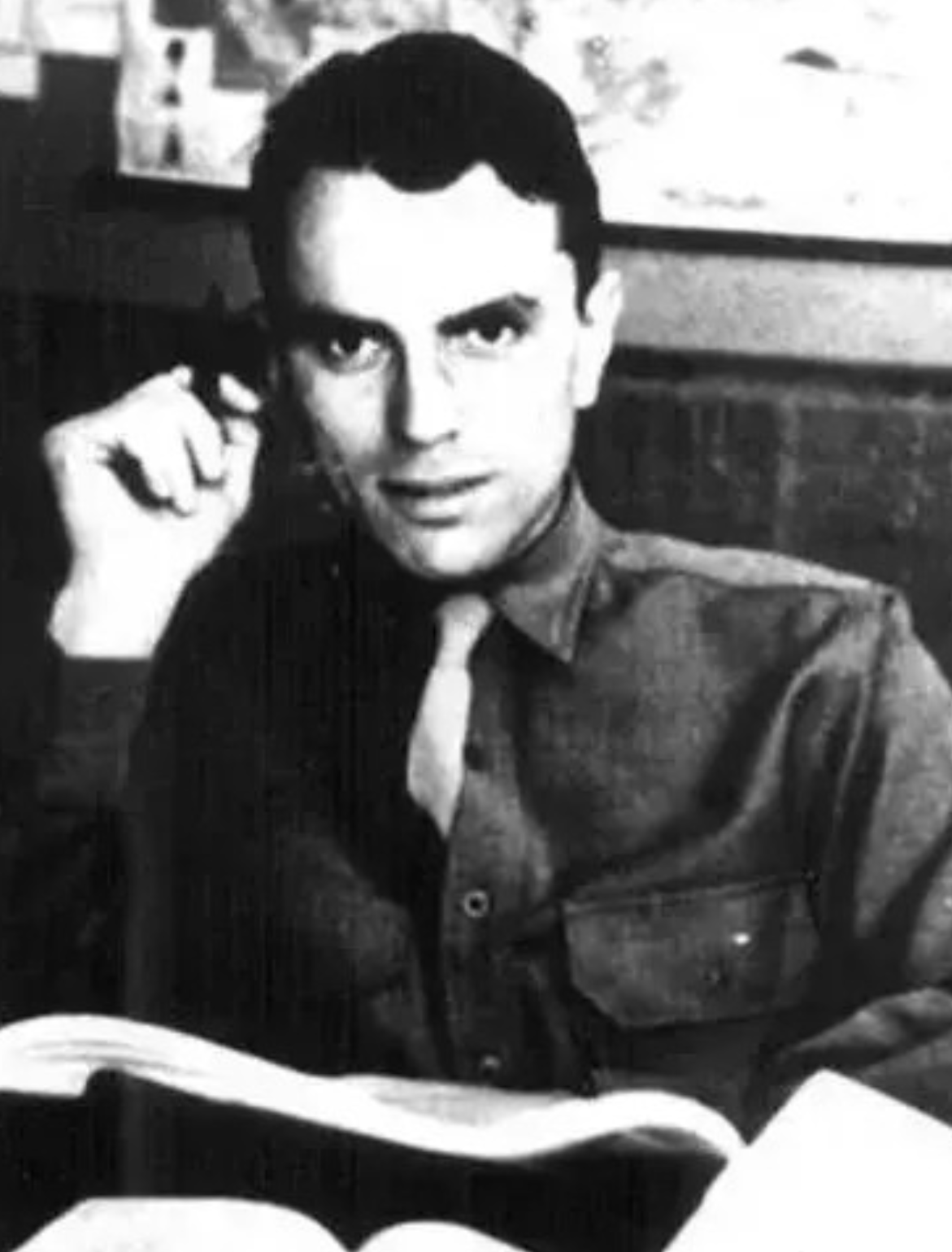





不良人
阿尼帕阿姨长得跟我妈妈好像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