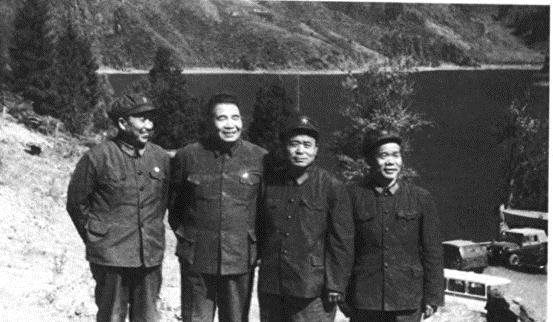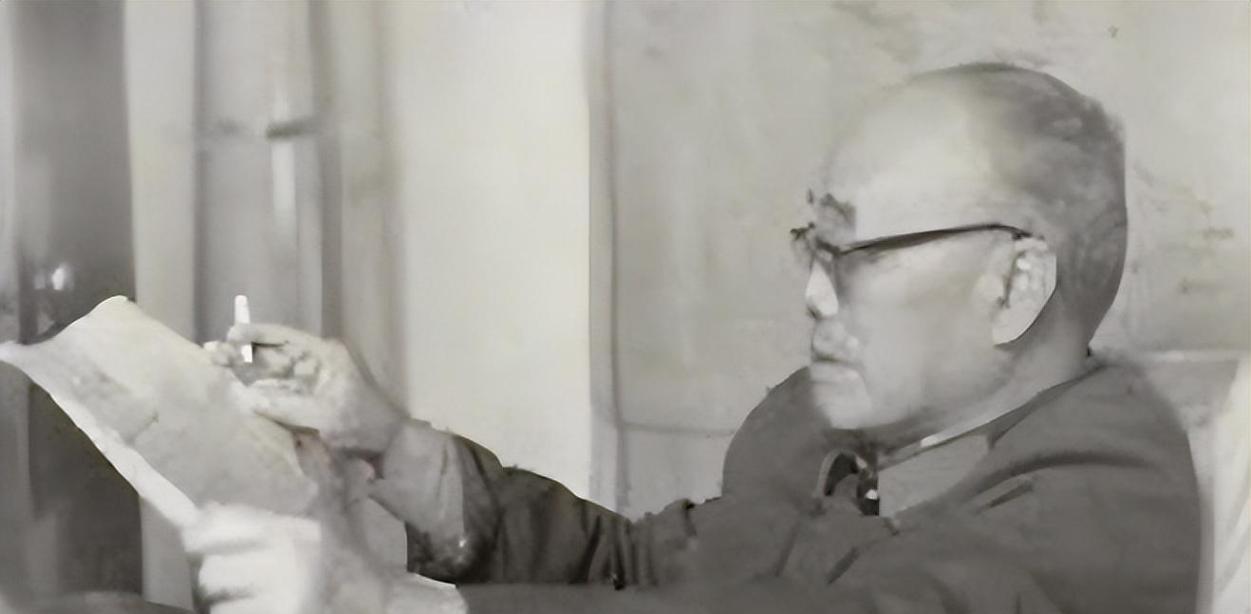他没当省委书记或军区司令,成工厂经理:和平了,让我搞经济建设 “1954年初春,你们别替我操心,和平了,让我到白银去开矿吧。”黄罗斌推开窗,兰州还带着冷冽的风,他语气却轻快得像刚打完一场胜仗。那天会上,中央决定撤销宁夏省、并入甘肃后的干部调整方案,摆在他面前的两条路,一条是进省里当书记处书记,一条是留部队升军区司令。出乎所有人预料,他把这两张“金名片”同时放下。 谈起黄罗斌,不少老兵会提到他当年在晋绥的硬气。陕北红军出身,枪林弹雨里一路爬升,解放战争时是四纵警三旅旅长。西府战役,他因“未按时发起攻击”被撤职,这段挫败在很多人眼里是污点,可他自己却常说:“撤职就撤职,战场上怕过子弹才丢人。”从那以后,他被调到地方军区接收起义部队,一边整编,一边跟进主力作战,对干部转行的难度也算早有体会。 1949年秋,他率部配合十九兵团解放银川。表面是副司令、副政委,实际司令是起义将领,具体事务全落在他头上。宁夏刚解放,青铜峡以南的土匪武装还在四处流窜;白天剿匪,夜里恢复电站、疏浚渠道。熬了几个月,总算把民生产业的账本捋顺。也正因为这段经历,他对“治理”二字有了另一层理解:枪口解决不了所有问题,只有工厂的烟囱冒起来,老百姓才真正松口气。 然而最令他头痛的,是刚接手那支由榆林守敌起义改编的独立二师。缺乏整训,缺乏组织,关键时刻跑得比谁都快。一次宁夏马家堡外线作战,连夜前推,半道上人就散了。师部连忙收拢队伍,他一边骂,一边追。最后这支部队干脆被撤编。他后来回忆时叹了口气:“战场和工厂不同,坏了可以返工,可人心散了,返工难。”这层体验形成了他对干部再教育的倔强,坚持“先做人、再干事”,影响了他此后的经济管理思路。 1954年机构调整,甘肃省委多次向中央打报告:老黄熟悉军队、懂地方,又是解放宁夏的功臣,当书记处书记顺理成章。总参谋部也递条子:“部队缺能打会管的老首长,请黄罗斌出任兰州军区副司令。”两封电报摆在桌上,他却觉得都“不太对劲”。和平建设已成大势,他不想再围着指挥图纸转,而是想握住炼炉,看看战火废墟能熔出多少铜铝。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选址在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坡,第一批地质队刚凿下去,便测出富铜富铅层。这个项目被列入“一五”重点,急需一位懂组织、敢拍板的“掌勺人”。黄罗斌看着工程方案,想到了老部队改造那段吃力不讨好的日子:同样需要整合,不同的是,矿山里没人逃兵,只有数据和石头。于是他的回信只有简短一句:“到白银,把矿挖好。” 到达白银的第一天,他踩着泥泞跑遍三十多个临时工棚。地质队员散住在山沟,伙食差得只能嚼馒头就咸菜。晚上开碰头会,他一句套话都没说,先把后勤处长点名:“人挖不动矿,先让人吃饱。”第二天凌晨,采矿队拉来两车菜叶子,“首长的命令”成了最硬通货。有人后来说起此事,直夸他懂基层,其实不过是一位老兵对体力极限的切身感受。 有意思的是,他把部队里的“班排建制”直接搬进了矿山:十人一组,组长负责安全、产量和思想动态;每晚收工写小结,第二天交调度室公示。今天看来像企业管理制度的雏形,那年却让不少专家皱眉——“搞经济不能用军事化那一套”。黄罗斌没多解释,只是笑——“好使,管用。”半年后,白银公司日产原矿提升了近三成,批评声默默消失。 1957年,一号竖井正式通风下矿,却赶上“反右”扩大化。省委内部一份材料指出:白银公司党委在执行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”口号时,存在冒进倾向。报告未明言,其实矛头直接指向黄罗斌。到1961年经济困难期,他顶着缺口拿贸易订单,换回大量救急钢材,厂子稳住了,他自己却被贴上“典型修正主义分子”标签。1965年文件下来,行政级别连降四级,搬出省委大院,去党校“反省”。那年他四十九岁,背包进宿舍时只说了句:“厂子没垮,人没散,就值。” 多年后,有同志问他当时恨不恨。黄罗斌摇头:“不恨,矿在那里,冶炼炉没冷却。”简单八个字,道破了一位老兵对“事业”二字的执念——职位高低不过过眼,机器转着才是正经。 1978年,拨乱反正。中央考虑边疆稳定,把他调到新疆自治区党委,先任常委,再任副书记、书记,兼管经济口子。上任第一周,他跑去新疆八一钢铁厂,看到高炉旁值班兵一身尘土,连说三声“像极了当年白银”。与军代表聊起改造计划,他提议引进甘肃那套“班排建制”管理,笑称“老方子还能治新病”。事实证明确实奏效,八钢当年产量突破设计指标百分之二十五。 1983年,他回甘肃主持政协工作。有人评价他从旅长到省长,再到厂长、书记,职务起落像过山车。可他自己更在意另一条曲线——产量。统计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白银公司1957年后的每一个季度数据,时隔数十年仍被他翻看。一次内参会上,他提到甘肃资源禀赋,说应让“铜、铅、锌这些深藏土里的家当”走上深度加工之路。讲话调子依旧不高,却让工业口干部直呼“落地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