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毛主席,就没有新西藏。毛主席是西藏的真活佛。 1951年,那个春天,北京的风不大,但西藏的事已经逼得所有人不敢喘粗气了。 昌都打完了,几万人马折在那里,电报一封封往中央飞,谁都知道,军队再往西推,几个月的事,拉萨就能收进来。 问题是毛主席不想这么快。他说要谈判,说要协议。 有人心里急,说解放都打到门口了,干嘛还陪他们耗?他摆摆手,说西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,信的是佛,敬的是活佛,几百年没大动过,不能一锅端。 结果,就是那纸《十七条协议》。 签字那天是五月二十三,地点选在中南海勤政殿。文件一页页摊开,铺在桌上。 说实话,协议内容现在一查就有,哪条哪款,写得不模糊。可真要说什么叫“历史的现场”,你得去看那天屋子里的沉默。西藏方面坐了阿沛·阿旺晋美,还有土丹旦达、桑颇·登增顿珠这些名字,说不上紧张,但脸色都很深。 他们知道签的是时代,可签的也是信仰、地位、世袭和一个可能被拆解的旧世界。 中央那边,张经武、李维汉都在,朱德副主席在场,陈云、郭沫若、聂荣臻全到齐了,那阵势,说是宣誓都不过分。 协议一共十七条。每条后面都有火药味,但包着棉。 比如说,西藏是中国一部分,这写死了;但又说,达赖的地位保留,原来的制度暂时不变,这留了口子。 两边你来我往,把一份兵临城下的战争结果,写成了一纸还能握手的契约。 这协议签完没几个小时,毛主席就在丰泽园见了李维汉和张国华。 他们刚回来,帽子都没摘,进屋就汇报。 毛主席一边听,一边抽烟,烟头蹭在烟灰缸上有一下没一下的响。 他听到协议成了,点点头,说好哇,你们干了件大事,但话锋一转:“这只是第一步。”他说西藏的事,别光看现在,要看十年、五十年。 他强调最多的不是军队,不是政治,而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。 这两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,像是一根绳子,捆着西藏的未来,也系着中央的谨慎。 送他们出门的时候,张国华敬礼。 毛主席没还礼,反而笑着伸手,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:“我的江西老表,你们此去,山高水远,要多保重。”说着又握住张国华的手,语气重了:“你们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。” 第二天的怀仁堂灯火通明,办宴会。 菜是好的,都是京城宫廷路子的手艺,但没人真在吃。 那天十世班禅的代表来了,献了哈达,还送了一面锦旗。那锦旗用藏文和汉文绣着:“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”。 毛主席看着那几个字没说什么,只是把旗展开看了好久。 他讲话那段被后人抄了无数遍,说清政府坏,说帝国主义坏,说汉族跟藏族过去总是闹,说现在终于能团结了。你要说那番话有多高妙,其实也没有。 语气很直,话很实:“现在团结起来了,这种团结不是一方压着一方,是兄弟般的团结。” 桌子那边,阿沛低头不语,嘴里嚼着茶叶末。有人说他那时候想的是拉萨的冬天,也有人说他是认命了。 我更愿意信,他在心里默念了一句:总算没动刀。 那几天毛主席像是特别爱说“团结”。 什么“团结—批评—团结”,什么“家里的事要摆在桌面上说”。 很多人听了,笔记本上抄得密密麻麻。其实这些道理,老百姓家里早就用惯了。吵一架,饭还得吃;说几句狠话,灯还得开。 毛主席把它升格了,说成民族政策,说成工作方法。 再往后几个月,拉萨来电了。 十四世达赖喇嘛亲自发的,说拥护协议,欢迎解放军,愿意共建统一中国。 毛主席亲自回了电,语气简练,言辞温和。可在历史这个老算盘上,每一封电报都不是孤零的点,它们拉出的是一条路线,是让西藏和北京之间,有了通话的线索。 而真正让这条线变得有温度的,是文化。 协议签完后不久,《北京的金山上》这首歌就开始在广播里放了。 歌词是从西藏民歌里来的,改编得不多,曲调一响,有种太阳刚爬上山的味道。歌里唱毛主席是“金色的太阳”,唱他给西藏带来温暖。还有一句,说毛主席是“真正的活佛”。 这句话传开后,不少人起先是愣的。 活佛是藏传佛教的核心信仰,说毛主席是活佛,怎么听都像冒犯。 但后来慢慢就接受了,尤其是藏族老百姓,他们没那么多政治词汇,好就是好,敬就是敬。毛主席让他们免了兵灾,粮食管了,庙还在,活佛的地位也还保着。 那在他们心里,他就是活佛。 有人说,这是不是一种神化?是不是一种宣传? 你可以这么理解,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草根的表达方式。在高原的语境里,“真活佛”不是对神的褒奖,而是对现实改变者的认同。 当然,历史不是一条线,它是一个麻团。 有人的记忆是宴会,有人的记忆是妥协。 西藏流亡者的叙述里,《十七条协议》是压力下签的,是不公的,是一种被迫。 他们不接受这段“和平解放”的说法,把它看作一种主权丧失的开端。这种记忆在海外延续,在新生代中被口述、被传播。 可不管怎样,在那年初夏的北京,纸是签了,手是握了,饭是吃了,电报是通了。 这些动作是真的,人是真的,气氛也是真的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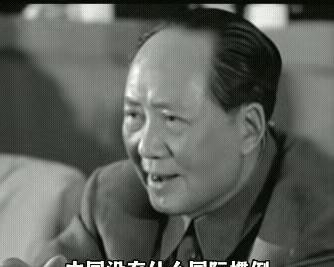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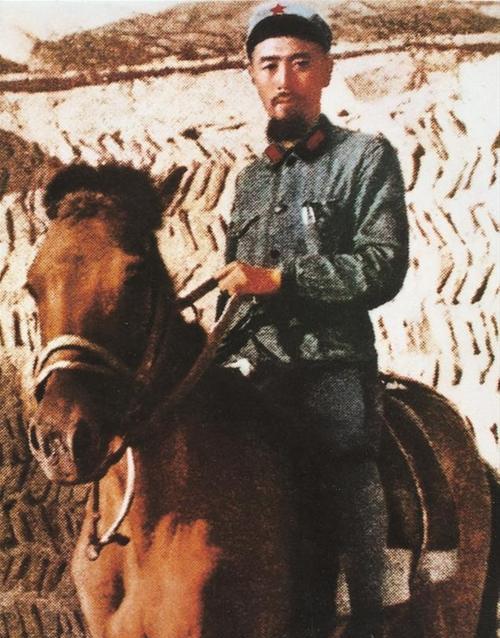
![感谢毛主席,为我们换了人间![赞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6590831489990443066.jpg?id=0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