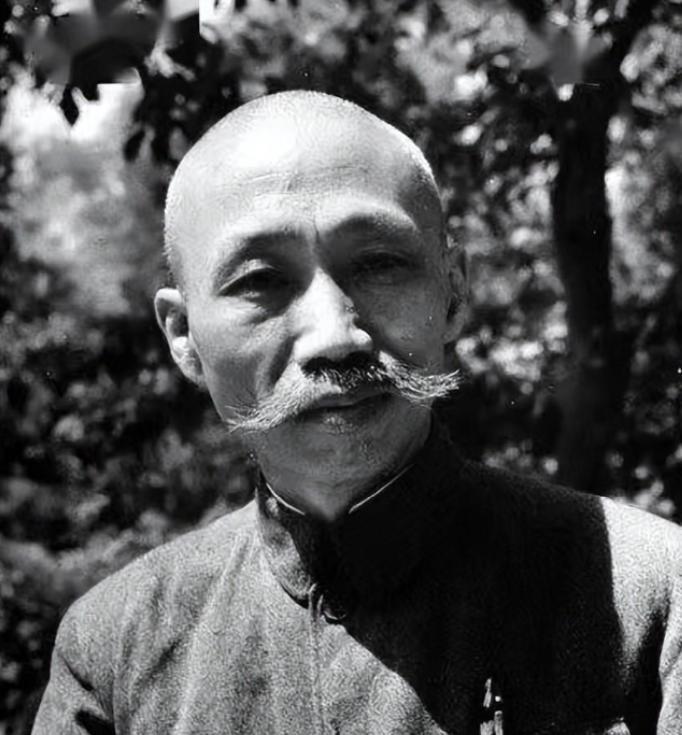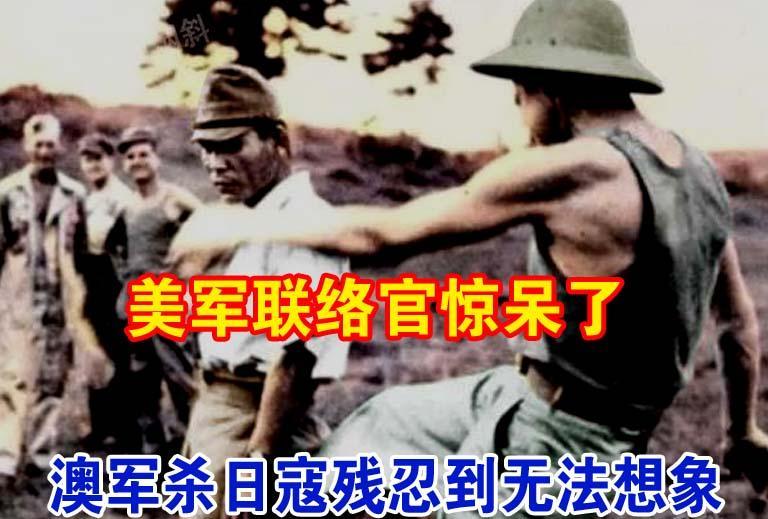1937年,地下党员张宗伟被捕,期间,妻子就在人群中,看到丈夫要被日军带走,妻子想走过来,丈夫一瞪眼,妻子又退回人群中! 张宗伟是东北早期的共产党员,这身份在当时就意味着,你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。他娶了个俄罗斯媳妇,叫阿格拉菲娜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一个东北汉子,一个俄罗斯姑娘,这组合在哈尔滨那个“东方莫斯科”虽然不稀奇,但背后的故事肯定不简单。阿格拉菲娜跟着他,就等于选择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路。 他们家,表面上看是哈尔滨炮队街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杂货铺。但实际上,这里是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站。前屋卖着面包和日用品,后屋的印刷机可能就在深夜里悄悄印着党的传单。张宗伟呢,就是这个站点的守护者。 搞地下工作,可不像咱们在谍战剧里看的那么神。没有那么多香车美女、灯红酒绿,更多的是每天提心吊胆,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。张宗伟得像个真正的商人一样,精打细算,迎来送往。他的任务之一,是负责哈尔滨和上海中央局的联络。他经常打扮成商人,提着一个藤条箱,坐上来来往往的火车。 有一次在火车上,鬼子搞突击检查,挨个儿翻行李。张宗伟的藤条箱夹层里就藏着绝密文件。眼看就要查到他了,怎么办?喊口号?掏枪火拼?那都是电视剧。张宗伟当时非常冷静,他蹲下来,假装整理箱子,迅速把文件抽出来,捏成一团,侧过身子,一口吞了下去。 然而,英雄最怕的,往往不是敌人的枪炮,而是来自内部的背叛。1937年春天,哈尔滨特委的一个叫傅景勋的家伙叛变了。这一下,整个东北的地下组织都暴露在危险之中。日军根据他提供的情报,策划了一场大清洗,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“四一五”大逮捕。 那天,张宗伟刚送走一位同志,日本宪兵就破门而入。 当时,他的妻子阿格拉菲娜碰巧出门了,正在回家的路上。她远远地就看到家门口不对劲,停满了日本人的汽车和摩托,杂货铺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什么都明白了。 阿格拉菲娜没有跑,而是强作镇定,走进店里,对一个日本兵说:“掌柜的,我要买面包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往后屋瞅。那个日本兵不耐烦地吼了一声:“不在!” 就在这一瞬间,阿爾格拉菲娜不顾一切地掀掀开门跑了过去。她看到了,她的丈夫已经戴上了手铐,正在被日本人推搡着往外走。 阿格拉菲娜下意识地就想冲过去,她想拉住他,想跟他说句话,哪怕只是最后一句。她朝他走过去。 就在这时,张宗伟看到了人群中的妻子。他没有喊,没有挣扎,甚至没有流露出悲伤。他只是用尽全身力气,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 就是这一瞪眼。 那眼神里有太多东西了。有命令:“别过来!快走!保护好自己和孩子!”有诀别:“忘了我,好好活下去!”更有如山一般沉重的爱:“我爱你,但为了你,我必须推开你。” 阿格拉菲娜瞬间就懂了。她所有的冲动,所有的悲痛,都被丈夫这最后一眼给钉在了原地。她咬着牙,含着泪,一步一步,退回了涌动的人群中,看着丈夫的身影消失在街角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夫妻二人近在咫尺,却必须靠一个眼神完成最后的告别。 张宗伟被捕后,受尽酷刑,坚贞不屈,同年7月就被日寇杀害了,年仅55岁。 一个英雄就这样牺牲了,他的家人怎么办?在那个乱世里,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俄罗斯女人,日子该有多难? 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人了,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,冯仲云。 抗战胜利后,冯仲云担任松江省主席。他心里始终惦记着那些牺牲的战友。他做的第一批事,就是登报寻找烈士的家属。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张宗伟的家人。当时,阿格拉菲娜正带着五个孩子,靠给白俄人洗衣服艰难为生。冯仲云二话不说,把他们一家全都接到了自己家里住。 一个省主席,自己家里住满了烈士的遗孤,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孩子,做饭都得用大铁桶。冯仲云自己的儿子冯松光回忆说,他那时候连固定的床都没有,有时候得跟警卫员挤一张床。冯仲云还亲自安排张宗伟的儿子进了烈士子弟学校读书。 这种情义,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的。它不是冰冷的命令,不是刻板的制度,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,滚烫的承诺:你为国捐躯,我为你养老育幼。 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,如今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。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,几十年来,一直在默默地关心、帮助那些抗联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