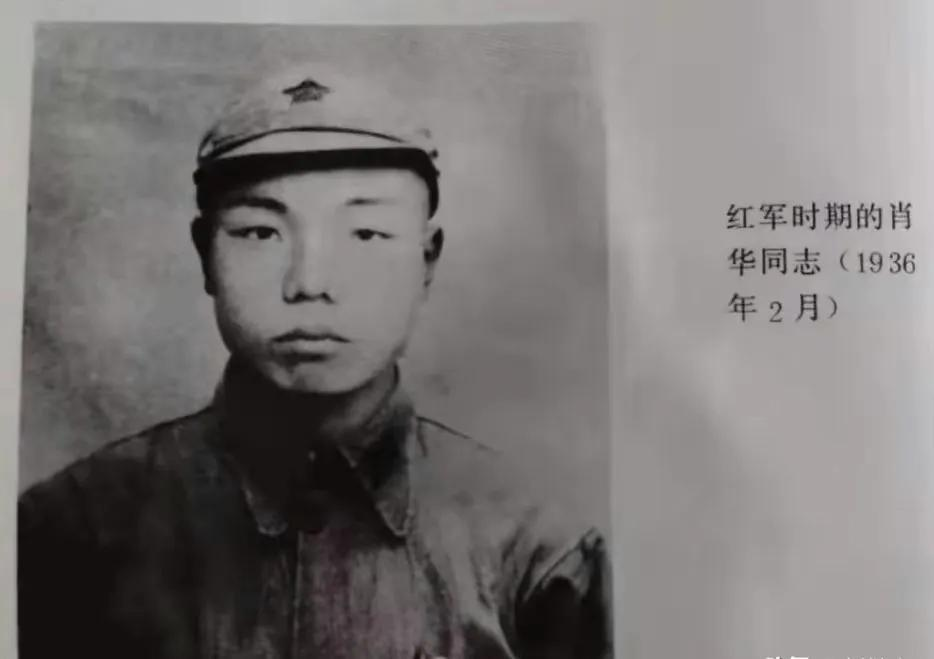1977年,安徽女知青于文娟在返城前夕,将身心托付给了那个痴情的农村青年:"你对我的情意,我今生难报,就让我们为这段岁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!"可谁曾想,她刚回城便杳无音信,命运从此天翻地覆。 【消息源自:安徽省档案馆《1977年知青返城安置登记表》、复旦大学"知青口述史"项目访谈录音、《XX县教育志》民办教师章节】 王胜利蹲在拖拉机旁抽烟时,村支书老张甩着两条沾满泥巴的裤腿走过来,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拍在发动机盖上:"上海来的加急电报,你那个知青姑娘要回来了。" 烟头猛地亮起红光。这个二十六岁的拖拉机手盯着电报上"怀孕"两个字,手指头把纸角捏出了汗印子。三天前于文娟返城时,他偷偷往她包袱里塞了半斤粮票和晒干的野菊花,没想到再见面的理由会是这样。 197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于文娟蜷在文具厂女工宿舍的木板床上,听着隔壁床老姑娘们讨论"的确良"衬衫的价钱。她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,想起三个月前离村那晚,王胜利家土墙上晃动的煤油灯影。当时这个憨厚的拖拉机手红着脸说:"俺给你留着搪瓷缸,啥时候想喝红糖水都管够。" "小于!医务室喊你复查!"车间主任的破锣嗓子吓得她打翻了颜料桶。在城郊卫生所,戴着白帽子的女医生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扔:"胎心都听到了,要留就赶紧开证明,要处理得趁早。"窗外的梧桐树上,最后一片枯叶正巧砸在计划生育宣传栏的"晚稀少"标语上。 当晚母亲掀了饭桌。这个在纺织厂干了半辈子的女人,把相亲对象的照片拍在搪瓷缸旁边:"李科长家里有抽水马桶!你非要回农村蹲茅坑?"于文娟盯着桌上并排摆着的两样东西——印着"广阔天地大有作为"的知青缸子和印着牡丹花的彩礼照片,突然发现自己的左手正在无意识地摸着腹部。 暴雪夜里的运煤列车像条冻僵的蛇。于文娟蜷在煤堆里,怀里揣着从母亲五斗橱偷来的两百块钱。这些印着大团结的纸币足够买台缝纫机,现在却要用来买通产科医生——或者买张回程票。当列车员的手电筒晃过来时,她突然想起插队第一年发高烧,王胜利连夜开拖拉机送她去县医院,车斗里垫的正是现在硌得她生疼的这种煤块。 黎明前的磨坊像个冰窟窿。于文娟摔倒在石碾旁时,听见熟悉的"突突"声由远及近。王胜利的破棉袄裹着机油味罩下来,她听见这个闷葫芦结结巴巴说了八年来的第一句情话:"孩、孩子别怕,俺拖拉机上有暖水壶..." 开春时村支书叼着烟锅来看新盖的耕读小学。土坯墙上,于文娟正用红粉笔写"拖拉机"的拼音,底下坐着二十多个流鼻涕的娃娃。老张眯眼望着屋檐下晃悠的两盏灯笼——左边挂着知青带来的马灯,右边是王胜利糊的竹骨纸灯,突然扭头对来视察的公社干部说:"这俩文化人搭伙过日子,比县里表彰的万元户还体面。" 1989年夏天,王胜利蹲在田埂上拆录取通知书时,手指甲里还沾着棉铃虫的尸体。儿子要去省城读大学的消息,比他拖拉机里的柴油机转得还快。于文娟擦着黑板笑,粉笔灰落在她早生的白发上,像是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飘着野菊香气的离别夜。 棉田里的墓碑很简单,没有歌功颂德的碑文。来看老师的孩子们总爱摸一摸那个"钢笔穿过麦穗"的浮雕,就像当年在耕读小学里传看那本被翻烂的《拖拉机维修手册》一样。风掠过棉铃时,新来的支教老师告诉学生:这是咱中国最特别的毕业证——半个知青和半个农民,给土地交的满分答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