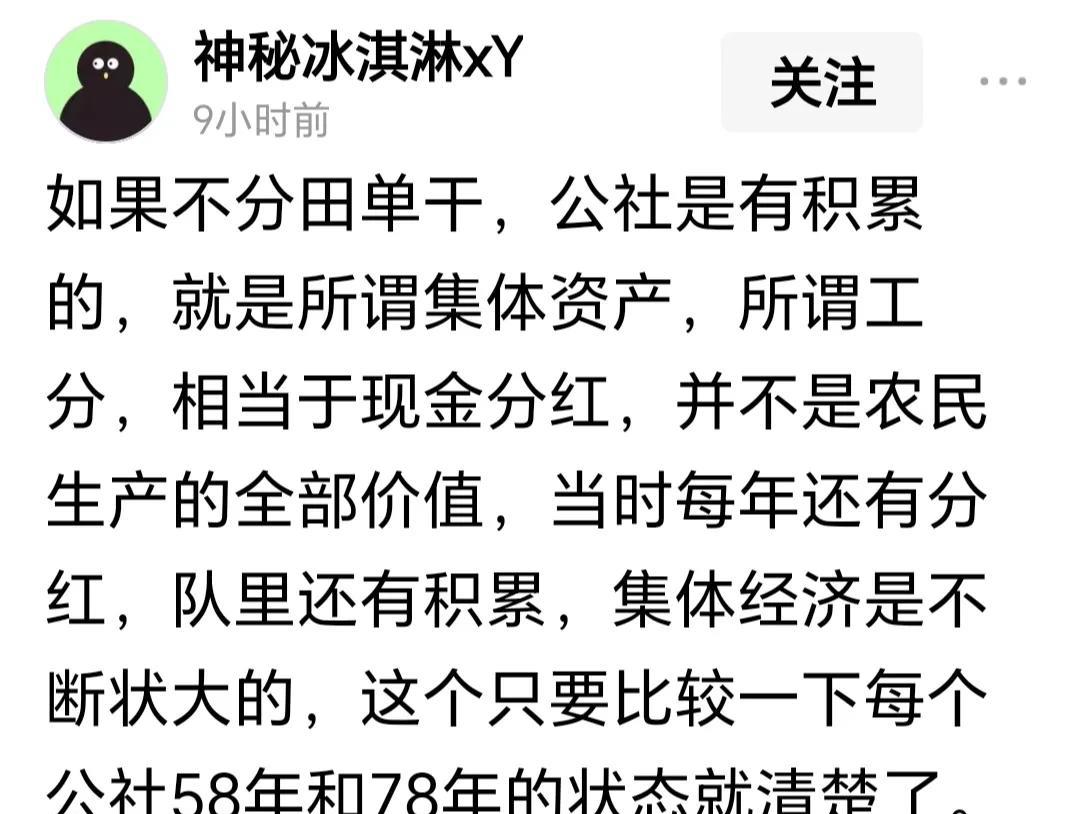1911年,李叔同回国后,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画,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。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,当场痛哭流涕。
1905年初春的天津卫,河面的冰碴在阳光下泛着冷光,码头上的苦力们呵出的白气与煤烟混在一起。
十八岁的俞蓉站在风里,怀里的幼子李端被裹得严严实实,只露出一双酷似父亲的眼睛。
她看着丈夫李叔同和族人将婆母的灵柩抬上马车,檀木棺材上那些繁复的雕花纹路,像极了婆婆生前常念叨的"李家迟早要飞走的鹰",此刻这预言正变成扎进她心口的针。
李叔同的留学梦早不是秘密,去年冬天婆婆病重时,他总在深夜对着东京美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呆,纸页边沿被拇指摩挲得卷了毛边。
那所学校课程表上刺目的"人体写生"四个字,让他既兴奋又惶恐。
此刻他接过妻子递来的暖手炉,指尖相触时发现她掌心全是冷汗。
"最多两年,学成即归。"这话他说得斩钉截铁,却不敢提已经托友人预交了学费,更不敢说黑田清辉教授的油画课需要女模特赤裸着站在画架前。
北归的客轮在黑浪里颠簸得像片枯叶,俞蓉蜷在二等舱的角落,听着孩子均匀的呼吸声。
八年前那个雪天突然闯进记忆,刚过门的她发现丈夫躲在书房临摹《秘戏图》,吓得打翻了茶盘。
婆婆当时拍着她的手说:"成蹊心里装着整个江湖,你得学着当个能装下江湖的碗。"
现在这碗终究要盛进东洋的樱花和那些她不敢细想的西洋画了,甲板上传来李叔同与同乡的谈笑,隐约飘来"春山淑子"几个音节,她下意识把脸埋进孩子襁褓,泪水在细棉布上晕出深色的圆。
1911年的秋天带着桂花香撞进天津老宅时,俞蓉在书房门口僵成了木头人。
墙上那幅裸体画里的日本女子斜倚在扶手椅上,皮肤白得像是会吸走屋里的光。
她手里的茶盘哐当砸在地上,惊飞了窗外槐树上的麻雀,李叔同从画架前抬头,眼神平静得像在讨论今天要不要加件衣裳:"雪子是我的模特,也是我在日本的妻子。"
这句话把俞蓉钉在原地,她突然想起丈夫留学前夜,自己偷偷在他箱底塞了尊白玉观音,现在那尊菩萨正被这幅画压着,在抽屉里碎成了三截。
李叔同的书房渐渐成了宅子里的禁地,有次幼子李端扒着门缝偷看,被俞蓉用戒尺抽得手心肿了三天。
她开始整夜失眠,耳边总回响着婆婆的预言,直到某个雪夜,她闯进书房扯下那幅画,却发现背面用铅笔写着"1910年2月17日,与雪子游上野,梅香如海"。
日期正是她生下第三个孩子难产那日,天津的稳婆说产妇血流得能淹了脚背,而东京的梅花开得正好。
1918年杭州虎跑寺的钟声传来时,俞蓉正在给李端的西装缝扣子,消息是卖豆腐的小贩捎来的,说老爷变和尚前把上海的房子和银元都留给了日本女人。
针尖扎进指腹的血珠像颗红珊瑚,她突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码头,当时李叔同说两年就回,结果五年后才踏进家门,带着满身油画颜料味和那幅要了她半条命的画。
现在他连"两年"都懒得说了,直接给了个永远。
天津的冬天还是那么冷,俞蓉偶尔经过"意园"洋书房,会看见那面空荡荡的墙,原先挂画的位置留下个比周围略浅的方印。
有次打扫的丫鬟说墙角堆着些发黄的画稿,她让人全烧了,火光里飘起的纸灰像极了当年客轮后消失的浪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