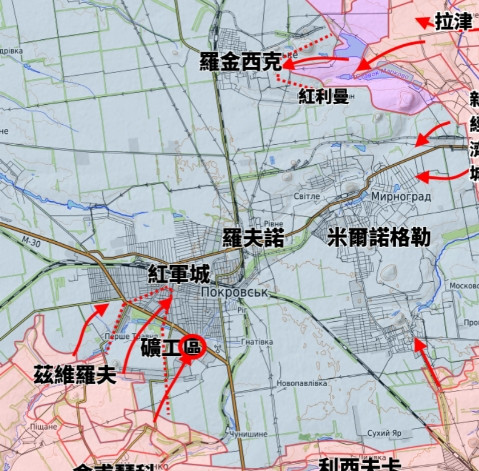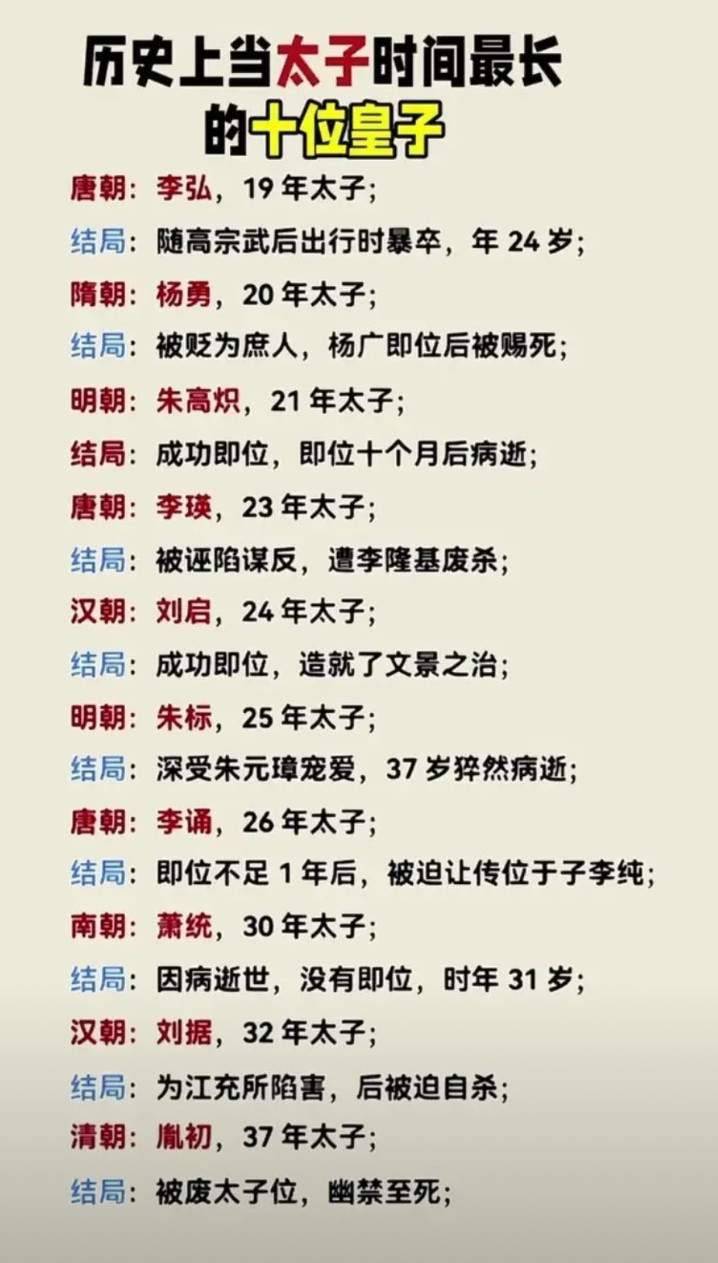1932年,一个地主老太为了支持儿子抗日,变卖全部财产。有人劝她,多少留点儿,她却说:“命都快没了,留钱有什么用!” 1937 年 4 月 5 日,青岛栈桥边,报童喊得正欢。一个裹着灰布头巾的老妇人站在那儿,正是王毕氏。 她手里攥着报纸。报纸头版有张照片,戴镣铐的男人被日军用铁钩穿透锁骨,脖子上的血痕一直延到衣领 —— 那是她的独子王凤阁。 报童嘴里嘟囔 “王司令全家殉国”,王毕氏听见,猛地把报纸按在胸口。指缝漏出的阳光里,能看到她手腕上根褪色的红绳,是二十年前儿子结婚时她亲手系的。 1919 年,奉天学堂里,校长 “中国不亡有我在” 的演讲让少年王凤阁铭记 “民族” 二字。此时三百里外,家境尚可的王毕氏正为凑他的学费犯愁。 1925 年冬,王凤阁要当兵,王毕氏想起他儿时耍木枪的模样,递出作为嫁妆的翡翠镯子:“当兵要保家卫国,不欺百姓。” 1932 年 4 月,通化县城里,王毕氏站在自家商铺前,看着伙计往马车上搬银元。 三个月前,儿子带了二十多个弟兄离开东北军,在大罗圈沟举起了抗日的大旗。 副官说:“司令想买捷克式轻机枪。” 王毕氏听了,下了决心:“把城南的粮栈卖了,后山的林场也抵押出去。” 王家的长工们私下里议论,说老太太疯了,把祖宗留下的家产都败光了。 王毕氏像没听见一样,在账房里一遍遍地核对卖地的契约,指甲都掐进了泛黄的纸里。 最后一担银元抬出大门时,她叫住管家:“把我陪嫁的紫檀木床拆了,木料能打三十个枪托。” 1932 年,王凤阁变卖家产起义,组建 “辽东民众义勇军”,任第十九路军司令,五年间在通化周边打游击,依托山区地形与敌伪周旋百余次,击溃伪军、围攻县城、捣毁日军据点,屡屡获胜。 1933 年春节,通化城飘着雪。王毕氏裹着件打了好几层补丁的棉袄,在义勇军驻地的伙房帮忙。 炊事员说:“老夫人,您歇着吧。” 要抢她手里的铁勺,看见她手腕上的冻伤 —— 是上个月冒雪给前线送弹药时冻的。 王凤阁的副官偷偷跟她说:“司令带弟兄们在果松川打伏击,缴了三挺歪把子机枪。” 她低下头接着搅锅里的高粱粥,眼角却笑开了。 日军的报复来得快。1934 年 3 月,关东军调了三个联队来围攻通化。 王凤阁在指挥部对着地图皱眉:“日军这次是来真的了。” 王毕氏听说后,带着十几个农妇闯进弹药库:“我教你们做土炸弹。” 她把硫磺和硝石按比例混在一起,火光照着她花白的鬓角。二十年前,她就是这么给王家的猎枪配火药的。 1935 年深秋,王毕氏跟着义勇军转移到临江山区。她的布鞋早就磨破了,脚底板结满了血痂。 副官想背她,被她推开:“我还走得动。” 路过一片苞米地,她突然蹲下,用冻僵的手指抠土里的土豆 —— 是她昨天偷偷埋的,想给伤员留着吃。 “娘,您去青岛吧。” 王凤阁在篝火边劝她。 老妇人拨了拨炭火:“当年你爹被胡子绑票,我带着你在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都没丢开你。现在让我扔下你?” 火星溅到她补丁多的裤脚上,她没在意。远处传来日军侦察机的声音,王凤阁握紧了腰间的驳壳枪。 1937 年 3 月 27 日,青岛汇泉路的小旅馆里,王毕氏对着镜子梳头。 她从包袱底下翻出个油纸包,里面是儿子小时候的胎发。 报纸上 “辽东剿匪大捷” 的标题看着刺眼,她却想起三年前在通化街头,儿子骑在马上对老百姓喊:“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站着,日本鬼子就别想安稳。” 刑场的枪声响起时,王毕氏正在菜市场买豆腐。 卖豆腐的老张头压低声音:“王司令一家……” 她的手抖得握不住秤杆,豆腐掉在青石板上,碎成了小块。 傍晚,她坐在栈桥边,看着海浪拍礁石,突然笑了:“凤阁啊,你小时候总说要当岳飞,现在真成了精忠报国的好汉。” 1937 年初,因叛徒出卖,王凤阁全家被捕。狱中他坚贞不屈,四岁的小金子也拒吃敌人物品。4 月 15 日刑场,王凤阁高呼 “中国不会亡” 后从容就义,妻儿一同殉国。 此前在青岛,王毕氏从报上看到儿子受刑的照片,又从卖豆腐的老张头处得知噩耗,手抖摔碎了豆腐。傍晚在栈桥边,她笑着感叹儿子成了精忠报国的好汉,如儿时所言成了岳飞式的人物。 王毕氏的故事,就是旧中国千万个母亲的样子。她们可能不识字,可能没去过远方。 但国家有难的时候,她们用最实在的办法,让人知道什么是家国情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