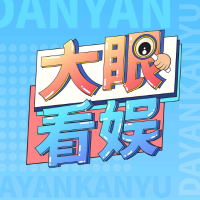1999年,李保田儿子李彧被人忽悠签了300万的合同,对方说:“只要让你爹来客串 20 集,你就是导演!” 李彧立刻把全部身家都压上,但李保田却拒绝:“我不演,剧本不行!”
李保田的拒绝像一盆冷水,浇得李彧从头凉到脚。
他攥着合同的手在发抖,不是因为害怕赔偿,而是想不通——父亲一辈子疼他,怎么偏偏在这件事上铁了心?
他不知道,李保田的办公桌上,正摆着一沓被红笔改得密密麻麻的剧本,那是他刚推掉的一个戏,对方开价是他半年的片酬。
“剧本是演员的根,根烂了,戏能好到哪去?” 这是李保田常挂在嘴边的话,只是以前,李彧没当回事。
投资方显然摸透了李彧的心思,第二天就带着更优厚的条件找上门:“你爹要是来,这戏的监制也给你做。”
李彧咬咬牙,回家跪在了李保田面前,把从小到大没说过的软话全说了一遍,末了带着哭腔:“爸,我知道剧本不好,可这是我唯一能证明自己的机会啊!”
李保田看着儿子通红的眼睛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。
他想起自己刚入行时,为了一个龙套角色,在剧团后台等了三天三夜,就因为老演员说 “这孩子眼里有戏”。那时的他,把 “戏比天大” 四个字刻在了骨子里。
最终,李保田还是妥协了,但提出了一个条件:“戏我演,但所有台词我要自己改,你要是敢糊弄,我当场就走。” 李彧喜出望外,没多想就答应了。
他不知道,这个决定让父亲在剧组里成了 “异类”。
拍摄时,李保田总是拿着小本子琢磨台词,一场简单的对话,他能想出三个不同的表达方式。
有次拍到深夜,李彧催着赶进度,李保田却突然站起来:“这句词不对,人物情绪到不了这儿,得改。” 李彧急了:“爸,差不多就行了,观众看不出来的!” 李保田把本子摔在桌上:“观众看不出来,我自己看得出来!”
更让李彧难堪的是,张丰毅的加入。
张丰毅是冲着李保田来的,进组第一天就拉着李保田说:“有你在,这戏错不了。”
可拿到剧本当晚,他就打电话质问:“保田,你怎么回事?这剧本简直没法看!” 李保田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,只说:“是我对不住你。” 张丰毅最终没走,但每次和李保田对戏,眼神里都带着惋惜。
李彧在一旁看着,心里第一次泛起一丝愧疚——他好像真的把父亲拖进了泥潭。
剧组的人很快发现,这对父子不对劲。
李保田从不跟李彧一起吃饭,休息时要么看书,要么一个人待着。有次李彧递过去一瓶水,李保田看都没看就摆摆手。
李彧委屈,却不敢问。直到杀青那天,李保田收拾东西时,突然说了句:“这戏播了,我就退休。”
李彧愣在原地,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,突然明白:父亲不是生他的气,是生自己的气 —— 气自己没能守住底线。
戏播出后,果然反响平平,甚至有人在报纸上写:“李保田晚节不保,竟演如此烂片。” 李保田把那份报纸剪下来,贴在日记本里,旁边写着:“警钟长鸣。”
那年春节,李彧提着年货回家,门是锁着的,邻居说:“你爸年初一就去乡下体验生活了,说要拍个农民的戏。” 李彧站在门口,手里的礼盒越来越沉。
这之后的四年,成了父子俩最漫长的冷战。李彧结婚时,给父亲发了条短信,没收到回复。
婚礼当天,他望着门口空荡荡的位置,突然想起小时候,父亲带他去看戏,散场后把他架在脖子上,边走边讲戏里的故事。那天的月光很亮,父亲的声音很暖。
转机出现在2007年的一个片场。李彧在一部戏里演个小配角,正好碰到李保田来探班老朋友。
两人在走廊里撞见,李彧下意识地想躲,李保田却先开了口:“听说你最近演的那个反派不错,我看了片段,眼神比以前准了。”
李彧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,哽咽着说:“爸,我错了,那时候我太想赢了。” 李保田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想赢没错,但得靠真本事。你看这走廊里的海报,哪个不是一部部戏磨出来的?”
从那以后,李彧像变了个人。
他不再提当导演的事,从龙套开始,踏踏实实地演。有次演一个乞丐,他在桥洞下住了三天,就为了找那种落魄的感觉。
李保田听说后,没打电话,却让朋友捎去一件厚外套。后来在一个颁奖礼后台,有人看到李保田拿着李彧的获奖照片,跟老演员说:“这小子,总算明白演戏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如今,李保田已经很少接戏,但每次有年轻演员来请教,他总会说起《生死两周半》:“那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观众的戏,但也是最对得起我儿子的戏。”
而李彧在采访里提到父亲,总会红着眼圈:“他用四年不说话的方式,教会了我比演技更重要的东西——敬畏。”
在这个拍戏越来越快的时代,李保田的 “轴” 显得格外珍贵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:演员可以老去,但对艺术的敬畏不能丢。
就像他改的最后一句台词:“戏可能会被忘记,但做事的良心,观众永远记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