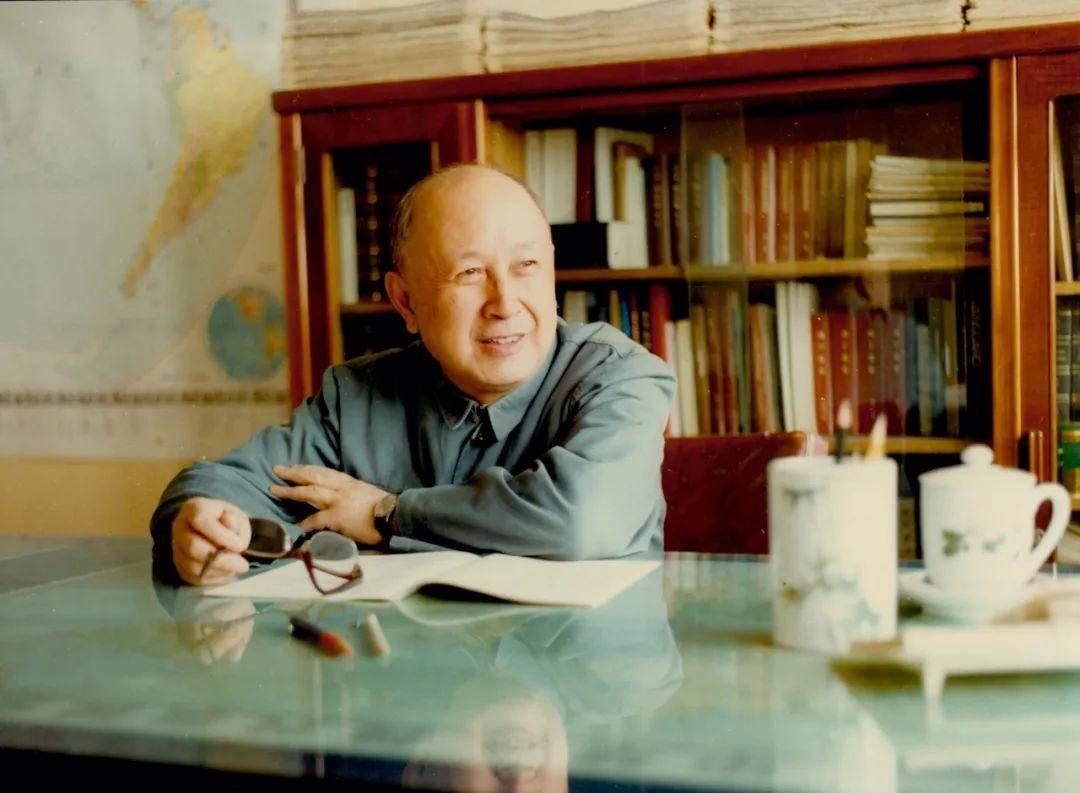1997年3月4日,86岁的杨绛看着病床上弥留之际的女儿,轻声低语道:“宝,安心睡觉,我和你爸爸都祝福你睡好。”话音落下,无儿无女的钱瑗缓缓闭上眼睛,没想到,最后一程只有母亲一人陪着她。 杨绛和钱钟书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对传奇夫妻。杨绛1911年出生于江苏无锡,原名杨季康,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,认识了才华横溢的钱钟书。钱钟书1910年出生,以《围城》闻名,学识渊博,精通多门外语。1935年两人结婚,携手赴英国留学,日子过得既充实又浪漫。1937年,他们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,皮肤白皙,像个瓷娃娃,夫妻俩把她当宝贝疙瘩疼爱。回国后,钱瑗跟着父母辗转上海、北京,1947年得了指骨节结核,休养了一年后康复,展现出惊人的韧性。1951年,她考入北京女十二中,高中时又因病休学一年,但凭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,1955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,1959年毕业后留校教书。钱瑗脑子活,精通英、俄双语,1966年改教英语,1986年当上教授,1993年还成了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。她在教学上特别用心,搞了个“实用外语文体学”,常跑图书馆挑英国文学的例句,让课堂生动有趣。学生们都喜欢她,觉得她讲课有种让人不想下课的魅力。钱瑗的婚姻却没那么顺。1968年,她和北师大校友王德一结婚,俩人同在美工队,住进历史系宿舍,日子甜蜜。可1970年,王德一因故去世,钱瑗成了寡妇。1974年,她再婚嫁给建筑师杨伟成,比她大十多岁,带着一儿一女。钱瑗心宽,和继子女处得像朋友,每周末从北师大骑车去灯市口,买牛肉馅饼和西式点心,陪孩子们吃吃聊聊,还会提前看电视报,聊节目拉近距离。可惜,她没自己的孩子,晚年又查出脊椎癌,病痛折磨得她苦不堪言。 1997年3月,钱瑗的脊椎癌已经到晚期,身体虚弱得不行。那段时间,钱钟书也在住院,父女俩都病着,杨绛86岁,奔波于两家医院,操碎了心。钱瑗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被病痛折磨的样子,总是推说别来医院,母女俩靠每天晚上的电话联系。有一天,钱瑗在电话里哽咽着说,过去那个乖巧的女儿已经没用了,杨绛听着心像被刀割。3月4日,钱瑗病情恶化,陷入昏迷。杨绛赶到医院,握着女儿的手,低声说让她安心睡,带着她和钱钟书的祝福。钱瑗嘴角微微上扬,像是听到了母亲的话,随后停止了呼吸。钱钟书因病没能赶到,钱瑗的最后一程,只有杨绛陪着。那一刻,三口之家开始走向分离,留给杨绛的,是无尽的孤单和思念。 钱瑗走后,学生把她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旁的一棵雪松下,那里是她教书的地方,常青的雪松像她对学生的关怀一样长久。杨绛常独自去雪松下,带着一束白菊,念叨着“从此老母肠断处,明月下,常青树”。1998年,钱钟书也因病去世,临终前他叮嘱杨绛好好活。杨绛把对丈夫和女儿的思念都写进《我们仨》,2003年出版,书里没有华丽的词藻,只有平实的回忆,记录了三口之家的点点滴滴。她还整理钱钟书的遗稿,翻译外国文学,把稿酬捐给清华大学,设了好读书奖学金,延续一家人对知识的热爱。2016年5月25日,杨绛在协和医院去世,105岁。她走前销毁了部分日记和书信,只留了些读者来信给清华档案馆。她走后,“我们仨”总算在另一个世界团圆。杨绛的一生,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,但她始终用文字和行动,守住了那份对家人的爱和对学问的坚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