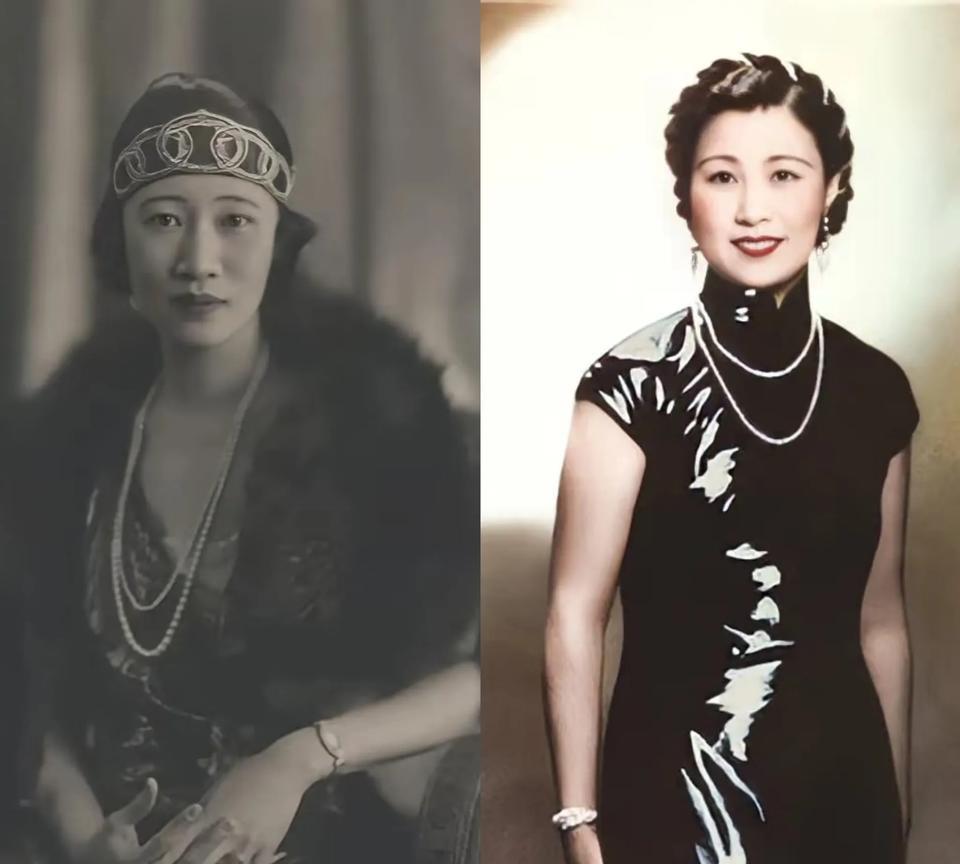1951年,老红军傅兴贵刚回乡务农,村里的一个寡妇就找到他,对他哭着说:“我曾参加过红25军,后来被俘,遭反动军官霸占。解放后回村,如今想要当小学教师,却无人敢用。”傅兴贵听了这番话,说:“老战友,我为你担保!”
1951年秋天,湖北麻城县的一个小村庄里,村民们惊讶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回来了。这个人叫傅兴贵,20年前跟着村里其他六个年轻人一起参军,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。
傅兴贵从省民政厅办完复员手续后,拒绝了在省城安排工作的机会,当年认出他的优抚处长肖逸山,正是他在红25军时的老部下,现在反倒成了他的上级。
老战友在武汉挽留了他整整九天,但傅兴贵心意已决。
回到村里没几天,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找到了他,这是个40多岁的女人,丈夫早年去世,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。
她告诉傅兴贵,自己也曾经是红25军的战士,在1934年的一次突围战中被俘,后来被迫嫁给了当地的国民党军官。
解放后,这个女人回到家乡,想找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养活孩子。但她的这段经历成了最大的障碍,没有学校敢要她。傅兴贵听完后,二话没说就答应为她作担保。在那个政治审查极其严格的年代,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。
傅兴贵的革命经历确实不简单。1931年,国民党军队袭击了他们村子付家榜,烧毁了十几户人家,杀死了村里几个积极分子。
当时只有15岁的傅兴贵跟着村里的成年男人拿起武器反抗,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在红25军的十几年里,傅兴贵从普通战士一步步升到了特务营营长。
1935年长征途中的一次激战,他头部中了三颗子弹,在野战医院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。军长徐海东亲自来看望他,给他记了一等功。
这三颗子弹改变了傅兴贵的一生。由于子弹位置特殊,军医不敢贸然手术取出。从此以后,每当天气变化,他就会头痛欲裂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,他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,胸前确实有七枚不同的军功章。
在省民政厅办手续那天,傅兴贵遇到了老部下肖逸山。当年这个小伙子是他手下的副排长,现在却成了处长。肖逸山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,坚持要给老营长安排一个省里的好工作。
但傅兴贵心里装着别的事情。他说:“当年我们村里一共走了七个人,现在就剩我一个了。
我得回去告诉乡亲们,其他六个兄弟都在哪里牺牲的,让他们的家人心里有个底。”
回到村里后,傅兴贵不但帮那个女战士解决了工作问题,还经常给村里的孩子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。但他从不夸大自己的功劳,总是重点讲那些牺牲的战友们。
村里人都说,这个当过营长的人一点架子都没有,干活时和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。
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待头痛的态度。村里的孩子们知道他头里有子弹后,总是好奇地问疼不疼。傅兴贵总是笑着说:“比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战友,这点疼算得了什么。”
那个年代像傅兴贵这样的老兵其实很多,他们在战场上九死一生,回到家乡后却选择默默无闻地生活。
没有特殊要求,没有居功自傲,就像普通农民一样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
更难得的是,傅兴贵还记得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。那个女战士的遭遇在当时绝不是个例,很多女红军因为各种原因,她们的经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。
傅兴贵愿意为她担保,实际上是在为一段被埋没的历史作证。
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,影响很大,一些原本对这个女人指指点点的村民,开始重新审视她的经历。毕竟,能让傅兴贵这样的老红军担保的人,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傅兴贵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,直到1980年代去世,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,每天早起锻炼,干活从不偷懒。头痛的毛病越来越严重,但他从不在人前表现出来。
村里人说,傅兴贵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“实在”。说话算数,答应的事情一定办到。他帮助过的人不只那个女战士一个,村里谁家有困难,他都会想办法帮忙。
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,却很少被记录下来,那些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老兵们,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什么叫做责任和担当。
他们不需要华丽的词藻,只是用行动证明,真正的英雄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来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