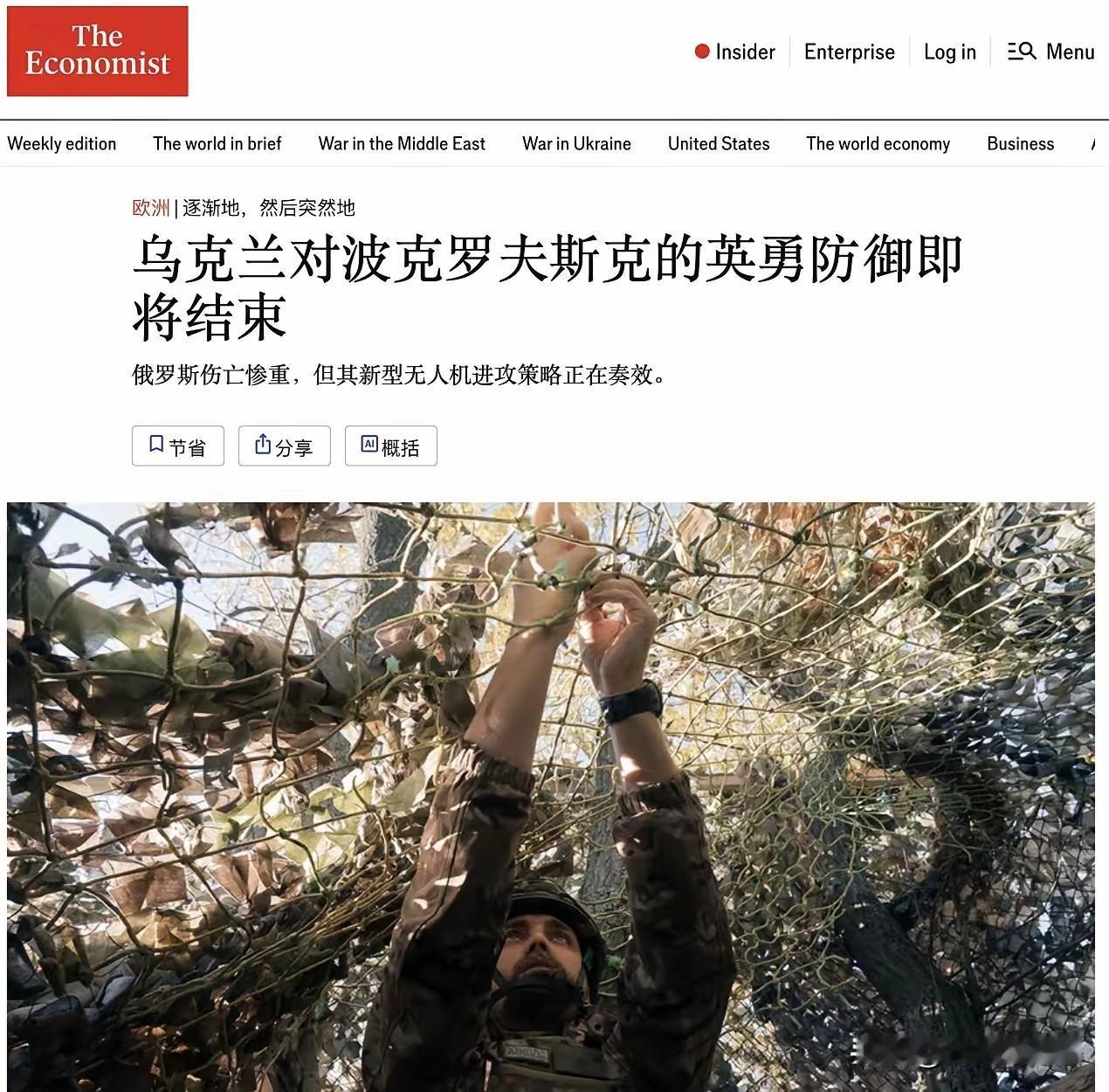英国学者马丁·雅克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台上,突然扔下一句话,全场炸了:“美国犯了一个致命错误——一个强大不过一百年的国家,居然敢“自称”成世界老大,而且是对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,起码在世界巅峰屹立二千年的伟大国家面前,何等狂妄和无知!” 麻烦看官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 关注”,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,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,感谢您的支持! 那场演讲结束后,剑桥大学的大礼堂安静得出奇,几百个西方面孔你望我,我望你,仿佛谁都没弄明白,刚才那位英国人到底说了句什么惊天动地的话。 马丁·雅克慢悠悠收起讲稿,脸上带着一点老派学者特有的淡定,他刚才那句——“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,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”,像一颗石子,扔进了长久平静的西方认知湖面。 这话出自一个英国人之口,让不少听众有点坐不住,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,这可不是哪个想红的政客放的嘴炮。 马丁·雅克今年已经快八十了,从剑桥博士毕业那天起,他就在学术圈打转,年轻时写过政治评论,后来在布里斯托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任教,是那种典型的“说话要有根据”的英国老派学者,可让他彻底变成“中国通”的,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中国之行。 那时的北京,街上全是叮铃作响的自行车,胡同深处飘着炸酱面的香味,马丁第一次看到一座古老城市和现代工地同时存在的画面,竟有点恍惚。 后来他回忆说,那趟旅行像掉进了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漩涡,一脚下去,就再也爬不上来。从那以后,他开始研究中国,写下《当中国统治世界》,在西方掀起不小的争论。 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不同,不在于政体,也不在于意识形态,而在于时间的尺度。西方国家的历史多以百年为单位计算,美国从建国到今天不过两百多年,正是青春躁动的年纪。 而中国的文明,用“五千年”来形容都显得克制,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的简单延续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套思想秩序、一种能从废墟里反复重生的文化体。 马丁经常拿这点打比方:西方人喜欢造王朝,中国人擅长造文明,前者靠征服维系,后者靠记忆传承。 就拿近代史来说,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,换成任何一个年轻国家,早该崩盘。但中国人就是能从断壁残垣里重新搭起秩序,三线建设的时候,工人住山洞、吃野菜,照样把钢铁厂修到了山腰里,这种“韧劲”,在他眼里,不是民族性格,而是一种文明的自愈能力。 他说美国真正的误判,就是把中国当成另一个苏联,冷战那一套,以为拉帮结派、搞封锁就能压制住,可中国不是靠军备吓人的,是靠技术、靠产业、靠对未来几十年的耐心布局。 封锁芯片?那就造自己的,禁5G?那就建自己的通信体系,马丁在报告里说得很直接:“他们以为封锁是绳索,没想到那是中国的磨刀石”这话听起来带点调侃,却切中要害。 他也没少批评自己所在的西方社会,美国的强大来自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红利,如今却沉迷在金融和话语霸权里,把短期利益当成长期战略。 相比之下,中国思考问题的时间单位不是“任期”,而是“世纪”,一个看十年,一个看一千年,怎么可能在一个频道上说话?马丁有一次接受采访时笑着说:“西方人永远在问‘明天怎么办’,中国人考虑的是‘下一代会怎样’。” 这番话在英国媒体上被炒得不轻,有人夸他“敢讲真话”,也有人骂他“向东方下跪”。可他一点不在意,反而越讲越透。他认为,理解中国,必须先放下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。 中国不是突然崛起,而是重新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,过去两百年不过是文明长河里的一个短暂弯路,现在它又回到了主航道上。 马丁说得更透彻的一点是,中国的强大,不是要挑战谁,而是要做自己,高铁、基建、科技创新,这些都不是炫耀,而是一种秩序的再建,西方社会的焦虑,其实来自一种失衡:他们习惯了自己制定规则的世界,却突然发现,游戏开始有了别的玩家。 如今,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,不再把它当作“威胁”,而是一个重新定义全球关系的文明体。 马丁常说:“中国的出现,不是西方的终结,而是世界多元的开始”他用半辈子研究一个他出生时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度,最后得出一个结论:这个国家强大不是因为幸运,而是因为五千年从未丢掉对自己的信念。 或许那天演讲结束后,掌声显得有些迟疑,不少听众还在消化那句刺耳的定义,但这场沉默,本身就是一种觉醒,因为当一个英国人终于看懂中国,也许意味着,世界开始重新看懂自己。 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