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给老妈换纸尿裤的时候,老公端了满满的一盆热水放到老妈卧室门口,并一再叮嘱我说: 换了纸尿裤,一定要用热毛巾挨着擦一遍,不能只用湿巾擦,那样不干净,也不舒服。 我觉得用湿巾擦擦就很好,老公非要让再用热毛巾多擦洗会儿,说是又干净又舒服,还能保证一点异味都没有。 老公怕我不听他的,他把热水盆放下后,不离远,在一边监视着我,嘴里还说着: 如果是我的亲妈,就不用你了,我自己做就行。当时我老妈卧床的时候,我就是这样做的,只要一换下纸尿裤来,我立马用热毛巾擦。 我听着老公的说教,用湿巾擦了以后,又换了热毛巾给老妈擦拭了一会儿。果然,老妈说: 热毛巾擦了太舒服了,比光用湿巾擦好受多了。 伺候老人,老公比我有经验,更有爱心。老公太细致入微了! 我端着那盆水,热气扑了一脸,心里其实有点不服气:湿巾多省事,撕开一抽,三两下完事,还自带香味。可老公站那儿,像棵门神,盯得我手抖,仿佛我一旦偷懒,道德分数就要被扣光。我小声嘟囔:“又不是给皇上沐浴。”他听见了,回一句:“皇上沐浴用花瓣,咱妈用热毛巾,已经打折了。”一句话把我逗笑,也把心里的刺按了下去。 毛巾浸进热水,我手指一烫,脑子却飘回小时候。那时我肚子疼,老妈把我搂在怀里,手里也攥着热毛巾,一圈圈给我焐肚子。她嘴里念着:“热气跑进去,痛气跑出来。”如今角色对调,我才尝到“跑”出来的何止痛气,还有时间——它把曾经无所不能的妈妈熬成了轻轻一句“太舒服了”,也把中年我推到了“给妈洗澡”的关卡。人生真会开玩笑,转着转着,就把你转到当年她的位置。 毛巾拧到半干,我学着老公的样子,掀开尿裤边,一点点擦。褶皱里藏着旧皮屑、藏着药味,也藏着她不肯说的尴尬。我动作尽量轻,像给大娃娃收拾残局。老妈眯着眼,嗓子眼里发出细微的“嘶——”,不是疼,是享受。那声音像根小羽毛,把我心尖挠了一下:原来“舒服”两个字,说出来只需一秒,做出来得有人肯弯腰十分钟。 老公看我动作慢下来,以为我要罢工,赶紧补刀:“记得大腿根也抹一圈,那里容易红。”我翻他一个白眼,手里却没停。擦到膝盖时,发现新添了两块淤青,想来是夜里翻身磕到床栏。我嘴里怪她:“妈,你又蹦迪了?”她嘿嘿笑,露出颗孤零零的门牙。那一瞬,湿巾广告里的“清爽”显得多苍白——它可不会给你开玩笑,也不会发现你膝盖上的青。 擦完一遍,我换水又折回来,第二遍只敢叫“扫尾”,老公却坚持“这叫巩固”。我腹诽:当年追我也没这么严格。可鼻尖凑近,确实没味儿了,只剩淡淡的肥皂香。我忽地明白,他争的不是干净,是尊严——让老人知道自己没被糊弄,让照顾她的人知道“糊弄”二字不该出现在家门。那一刻,我对这个平日木讷的男人有点刮目相看:他粗糙的手,原来藏着一把细密的尺。 晚上我算账:湿巾一包平均三毛一张,热毛巾得费水、费电、费洗衣液,成本翻几倍。可老妈睡前那句“今天真松快”,像给我账户里打了一大笔利息,怎么算都划算。我拍拍老公肩膀:“以后给妈洗澡的事,你挂帅,我跑腿。”他咧嘴笑,露出虎牙:“挂帅不敢当,我就一介弼马温,专治各种不服。”我踹他一脚,心里却踏实——知道往后无论多狼狈,都有人陪我一起把“老”字扛在肩上。 朋友听我吐槽“被监视”,回我一句:“你偷着乐吧,有人并肩作战,好过单打独斗。”我愣了愣,想起隔壁单元小李,一个人照顾痴呆父亲,半夜两点发朋友圈:“湿巾用光了,超市关门,谁能借我一包?”对比之下,我确实乐——乐的不是有人递热水,而是有人肯把“你妈”当成“咱妈”,把“老”当成两个人的考题,而不是一个人的深渊。 写到这儿,我低头闻了闻手,肥皂味早散了,却仿佛还留着那股温热。谁说热毛巾只是块布?它是一枚回形针,把今天和二十年前扣在一起;也是一张小纸条,写给未来的我:别怕脏、别怕累,别怕岁月把曾经挺拔的爸妈压成佝偻,因为你也终会被人小心翼翼地擦、被人轻声细语地哄——那是热毛巾的回声,叫“因果”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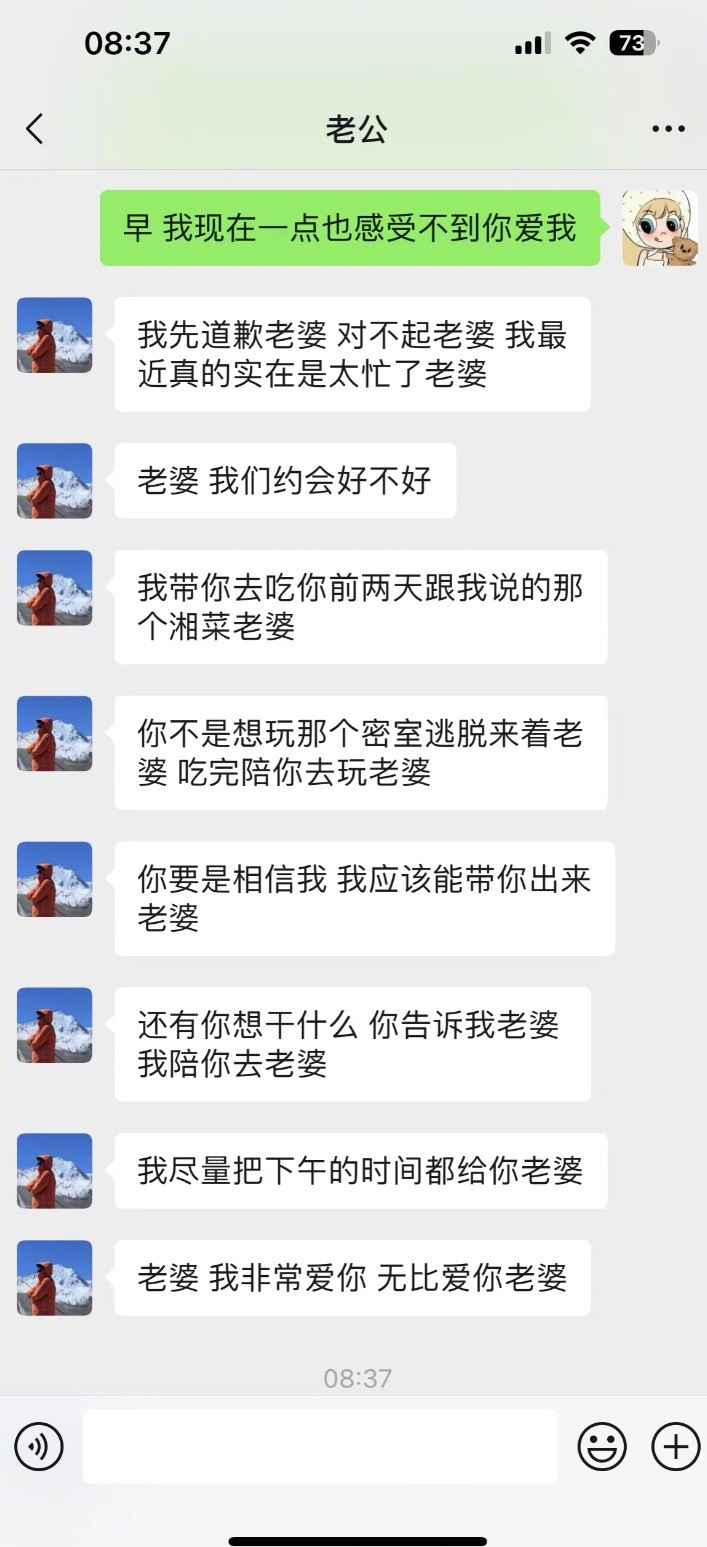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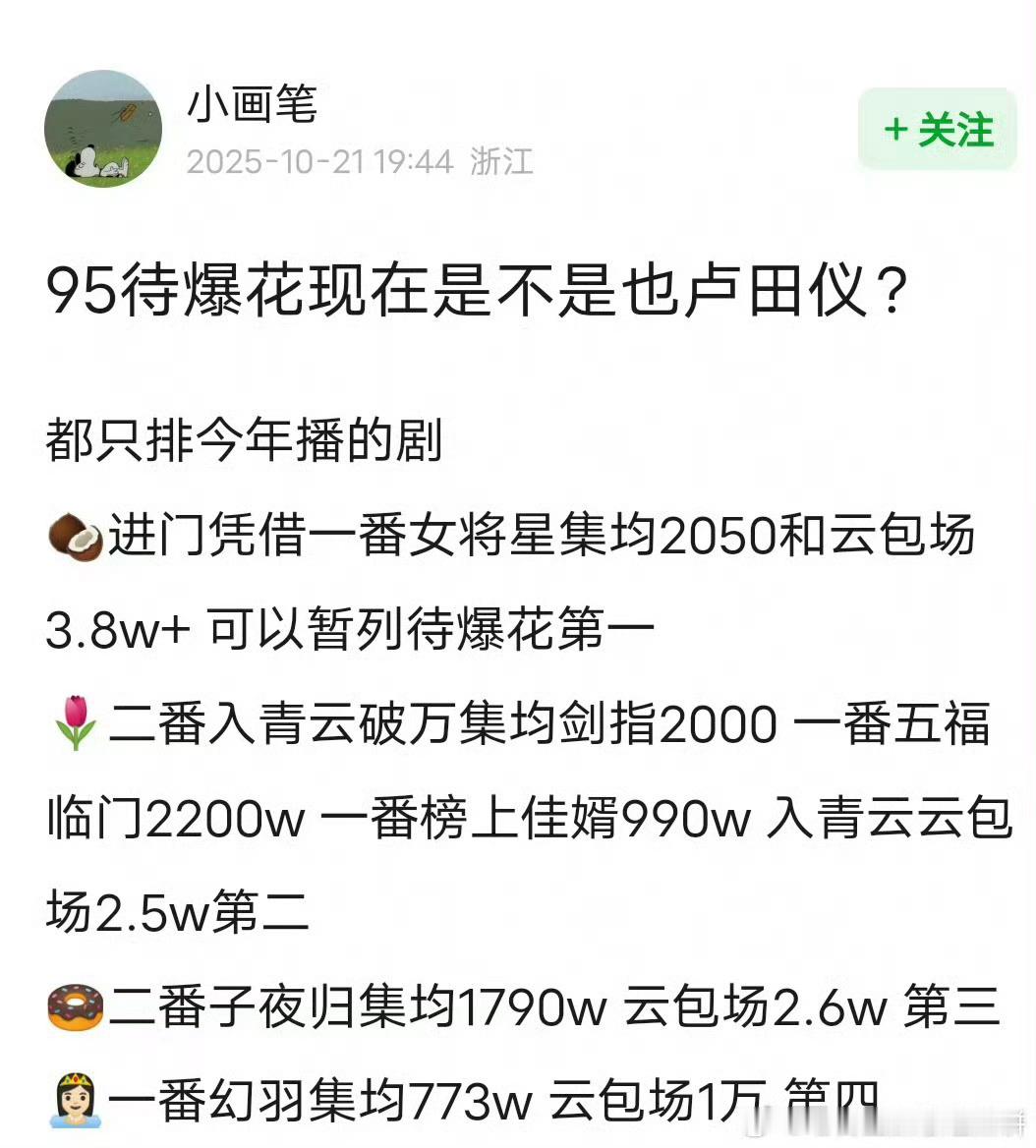

用户10xxx74
这个老公真是非常细心,这种男人值得拥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