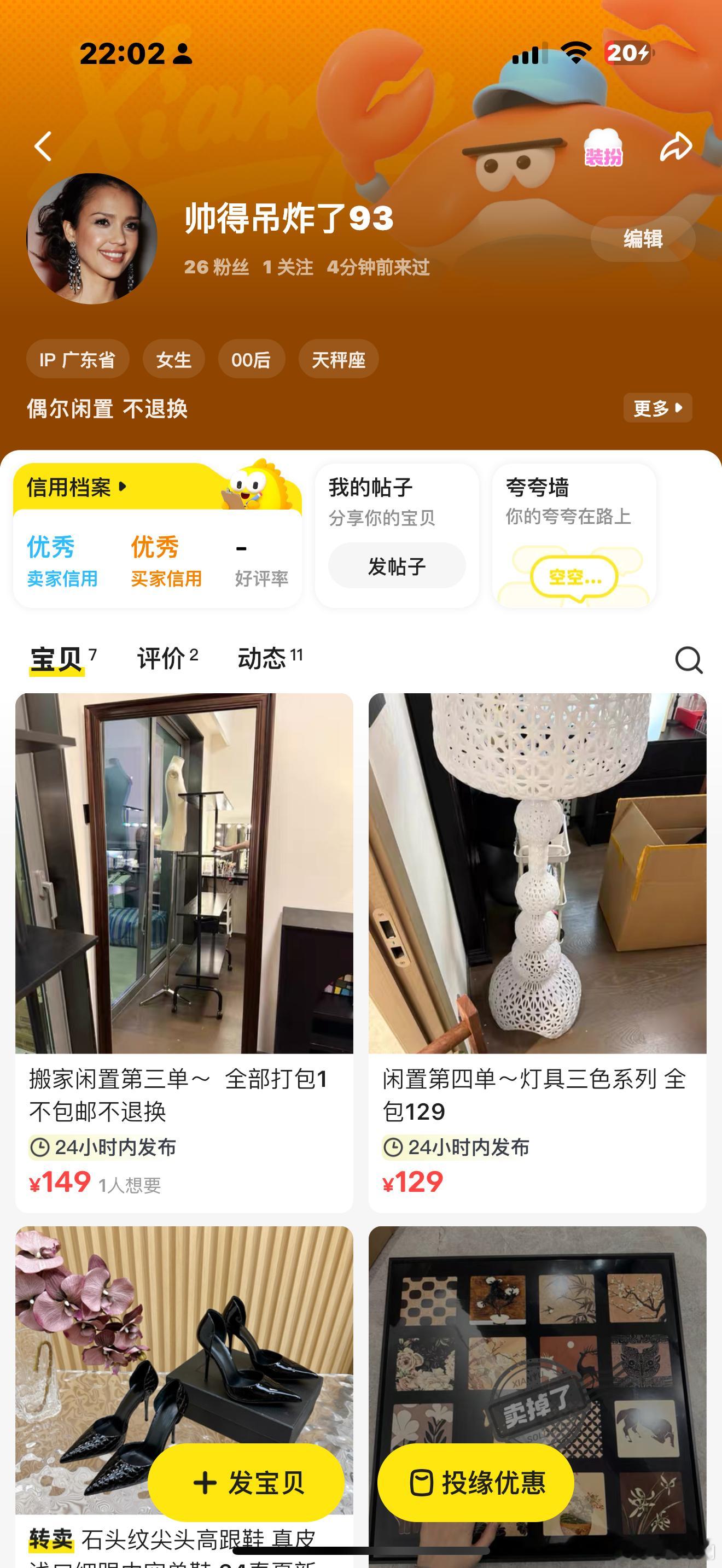民国第一美女胡蝶,一九三六年与丈夫潘有声在福州的珍贵合影,真是惊艳了时光! 那张照片……就福州那张,一九三六年拍的,胡蝶站在那儿,旁边是她丈夫潘有声。 她身上穿的衣服有点旧上海的味道,但你看得出那料子好,不光滑,是有点厚实的那种。她眼睛往右侧斜着,嘴角挂点笑。不是演给谁看的笑。 这张照片一直留着,说它“惊艳时光”也好,说它“命定一刻”也罢,说到底,就是一张老照片。 但你要说胡蝶的人生——真不是一张照片能收得下的。 她生得不早也不晚,1908年,清朝尾巴上那年,皇帝和老佛爷一个接一个地走了。 她家住上海,普通人家,洋行边上,父亲有个营生,母亲持家。她小时候不吵不闹,爱模仿,隔壁菜贩子吆喝什么,她能学一串。 有时候学得太像了,她妈拿勺子敲她,说“女孩子像什么话”。 她是怎么进的电影圈?说实话不太戏剧化。1924年,大中华电影学校招生,她去考了,也没谁拦着。她也不是一下子红的,早期在片场跑龙套、端茶倒水,演的角色也都边边角角,名字也不放在片头。 她演技好是后来的事,前几年就是肯干,能熬。 真开始有人记住她,是进了明星影片公司以后。 那几年,上海是电影的天下,她拍的片子一部接一部,名字爬上了海报,也爬上了小报的花边新闻。她的脸圆一点,不像那种削瘦的美,但就是好看,耐看。 有一次拍夜戏,风特别大,棚子用的是帆布和木架子,灯一亮,热得像蒸汽房。 她站在那儿不说话,导演喊停,她才擦一把汗,转头问:“刚刚那句,能不能重来一次?”不是做作,那是真觉得自己没演好。 她从来不急,别人抢角色,她让;别人拍完就走,她留下来陪摄影打灯。 有人问她图什么,她说:“镜头看得见。”她信这个。 《歌女红牡丹》那年,1931。第一部有声片。她跟不上节奏,说话要对口型,要站得离麦克风近一点。录音机老出问题,一遍一遍重录,她嗓子哑了,也不喊停。 拍完以后,导演瘫在椅子上说:“成了。”她低头笑一下,没说话。 然后是1933年,“电影皇后”选举。《明星日报》搞的,说是让观众来投票。 她拿了两万多票,阮玲玉才七千多。这事闹得不小,一边说她赢得干净,一边说她会做人。她本人倒不在意,媒体堵她,她只说:“演戏归演戏,别太当真。”她一直知道人情冷暖这回事。 感情上头,她不是没摔过。 最早那段,林雪怀,你知道的,就是那个戏子出身的。 两人是因戏结缘,但时间长了,问题也多了。她红了,他没红,他心里就憋着气。 拿她的钱去做生意,赔了,还被传和什么女人不清不楚。 她信了几年,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了。 写信求和好,他回得更绝,她咬咬牙,去法院告他,打了两年官司。钱拿回来了,人也凉透了。 那之后她沉了一阵,沉得住。再后来碰到潘有声,一个实在人,不风流也不多嘴。 做茶叶生意的,话不多,说句“今晚回家吃饭”,就算交代了全部。他们结婚没搞排场。胡蝶穿了一件白色旗袍,站在照相馆里拍婚纱照。潘站在她旁边,脸绷着,其实是紧张。 日子还可以,两人都不爱折腾,家里没那么多花样。 打网球她球技烂,他每次都故意打偏。她骂他“装样子”,他笑也不说话。福州那年,就是他们最稳当的一年。 那张照片也就是那时留下的。 战争一开,就不太平了。他们带着东西跑去重庆,三十几箱子,全没了,什么戏服、首饰、照片,全散了。她脸色都没变,说:“还在就好。”她说的“还在”,是人还在。 后来戴笠出现。军统那个。他盯上了她,说是保护,实则是软禁。 三年,她就那么过的,外界说什么她都不吭声。她不解释,不抗争,也不讨好。 戴笠死了,她就收拾行李,回到潘有声身边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更早些的事,还有那场乱传的绯闻。“九一八”那天,有人说她和张学良在跳舞。这话一出,舆论炸了,骂她是“红颜祸国”。她不吭声,只写了一封公开信,说“国难当前,不容虚言。”四个字顶十句。以后她再也没主动说过这事。 晚些时候她复出,拍了《后门》,1960年的片子,拿了奖。 那年她四十多岁,不年轻了,但站在镜头前还稳。领奖的时候,她穿了老旗袍,头发梳得紧,一句话:“谢谢大家。”没煽情,也没哭。 再之后,她去了温哥华。住在儿子那边,过得不声不响。每天去海边走一圈,看部老电影。还去报了英语班,八十几岁,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记单词。有人问她为什么学,她说:“电影里说什么我得懂。”就是这么回事。 她不爱提从前,照片也不挂。别人问她胡蝶的事,她笑笑,说:“翻篇了。”晚年,她用回了本名——潘宝娟。她说:“胡蝶飞累了。” 1989年,春天,她病了,躺在床上,窗外是阴天,风有点大。 她睁着眼看了一会儿天,说了一句:“胡蝶要飞走了。”声音轻,不像告别,更像一句话到了嘴边,不说不舒服。 人走了。她没留什么话,也没写回忆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