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6月20日,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第一次见面。首次见面,冯玉祥对蒋介石印象极佳,后来他在自传中这样回忆:“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,无不使我敬慕,大有相见恨晚之情!” 徐州那会儿正是闷热,空气不动,天像铁盖子扣着。 1927年6月,蒋介石和冯玉祥见了面。地方不讲究,气氛也不隆重。简单一场会谈,却在往后的二十年里反复被提起。 蒋那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正当红。 冯玉祥守着豫陕甘,兵多,地盘也大,可地方苦,军粮紧,一年到头愁的就是供给。 这人平常说话带火气,动不动就拍桌子,可那天在徐州,神色不见多紧,反倒挺客气。 他看蒋介石的眼神,有几分欣赏。 后来在自传里提过,觉得蒋的人很有劲头,说话利落,是干事的样子。 那一年的政局,挺乱。国民党分了家,南京这边是蒋,武汉那头是汪精卫。 再往北,张作霖盘着,三头对峙。 冯玉祥正卡在中间,被两边拉扯。兵力上,他说了算;可粮草供应,靠南方。 蒋介石看得清楚,先送了一批军械物资过去,算是“意思”到了。冯知道那不是白送的,可人都这样,谁雪中送炭,心里自然记着。 他没答应蒋立刻打武汉,但在清党和继续北伐的问题上,态度就软了。 过了几个月,北伐进展快,眼看着就要拿下北京。 1928年二月,郑州一聚,两人交换了兰谱。 冯做兄,蒋为弟。形式上算是结拜,实则是表明态度:以后是一个路数的人。 场面没多隆重,就几张桌子,几个随行的人看着。兰谱上写着“三民主义”几个字,气氛不紧张,也没人多说什么。 这之后没多久,关系起了变化。1929年,蒋介石把桂系打了下去,底气更足了,不太看得上冯这边。 冯原以为自己要接收济南、武汉,结果南京先下手,派兵占了地方。 冯气得够呛,部下火气也大,几个人凑在一块,给蒋发通电,说要他下野,还给冯戴了顶“护党救国”的帽子。这一来,台面上的兄弟关系就算彻底撕破了。 到1930年,冯、阎锡山和李宗仁凑成一伙,准备一块儿干蒋介石。 中原大战就这么开了。河南一带成了主战场,炮火声连着几个星期没停。冯的西北军过去纪律不错,可一打起仗,问题就冒出来了。将领倒戈的倒戈,兵士跑的跑。 韩复榘、石友三带着兵马转头投了蒋介石,把冯这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冯一开始还撑着,觉得能扛过去。可战局明摆着,越打越不利,自己人先散了。 最后没办法,通了电,说自己下野,不再参与政务。退了之后,他搬到农村,日子一下清闲了下来。 没兵、没地、没实权,外头风声大,他屋里却静得很。 日子过了一段,冯没闲着。 1933年,他又折腾了一下,在张家口组了个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。 打着抗日的旗号,人还真不少,行动也快,一下子拿回了不少地方。 可这事儿没让南京高兴,反倒觉得他是借抗日之名起事。后来军队被打散,他也只好再一次辞职。 到了抗战全面爆发,蒋介石又把冯叫回来,给了他个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”的职务。 这名字听起来响,但说白了就是挂名。开会他是去了,发言也有,可真要定事儿,没他份。那段时间里,冯在南京住得清冷,不怎么见人,开完会就回家,身边就两三个旧部陪着。 战争快结束时,他提出想出国走一走。 蒋也没拦,给他安排了个“水利特使”的名头,说是考察用水问题。 人出了国,消息也少了。有人说这是蒋在边缘他,也有人说冯本来也没打算回来。 1947年,冯发了话,公开批评蒋介石,说了一些不中听的。 这回是真的撕破脸了,国民党那边也火大,马上把他开了党籍,连过去的头衔一并收了。 一年后,冯玉祥死在苏联的海边。 1948年9月,坐的船叫“胜利号”,起了火,烧得快,人没能逃出来。据说在那之前,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,想说点话。但这封信没收到回信,最后也没人再提起过。 那一年,冯六十多岁,在异国他乡,死于一场突发的火灾。 没有仪式,也没告别。兰谱上的兄弟,最后成了陌路人。 那个夏天徐州的见面,外人看着像是握手言欢,背地里其实各有算盘。从相识、相助,到反目、对打,再到合作、疏远,最后连话都不说了。 这些年变来变去,谁也没站稳过,谁也没彻底赢过。 人前称兄道弟,人后提防着彼此,政治就是这么个东西。 冯玉祥那封没人回的信,烧没烧成灰不知道。但那张兰谱,那顿酒桌,那一声“老弟”,多半是早就没了意义。 黑海的风一直吹着,火光一闪一灭,夜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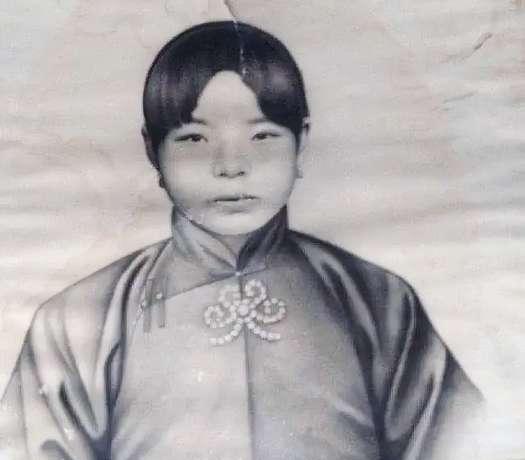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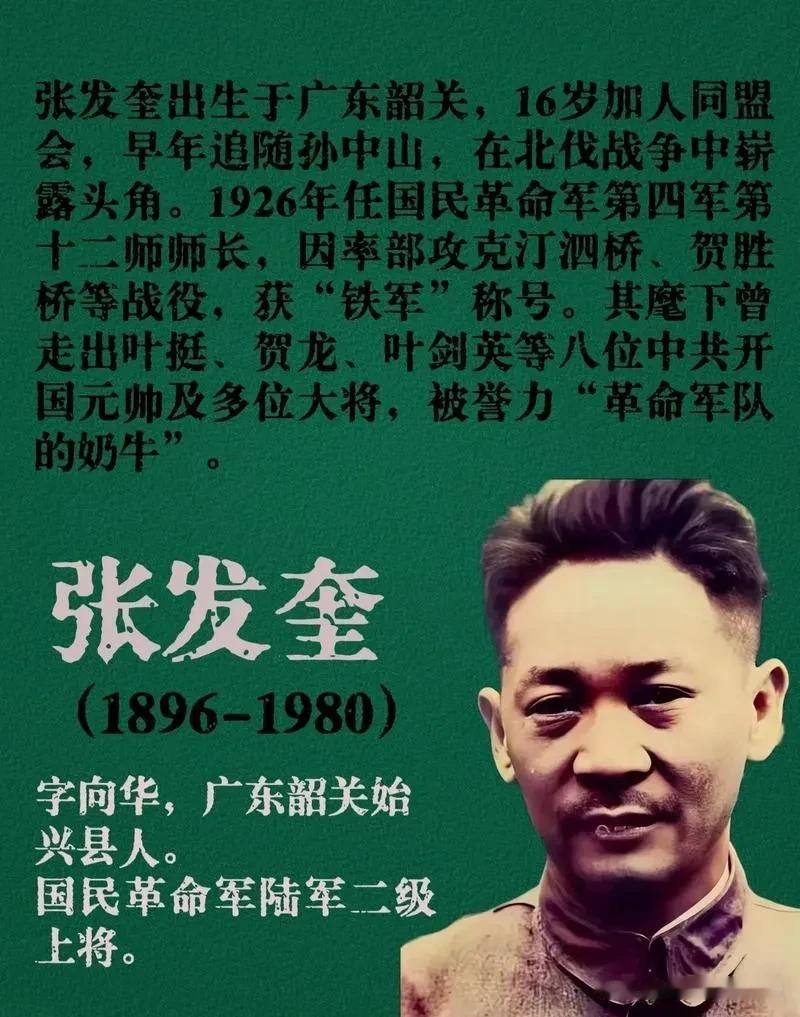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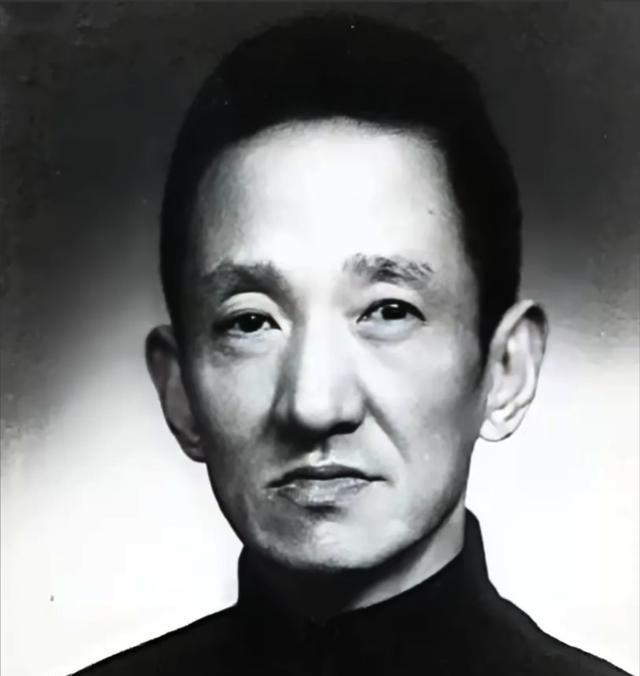

江渐月
要是没有新旧军阀的火拼,日寇也不敢蹬鼻子上脸搞侵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