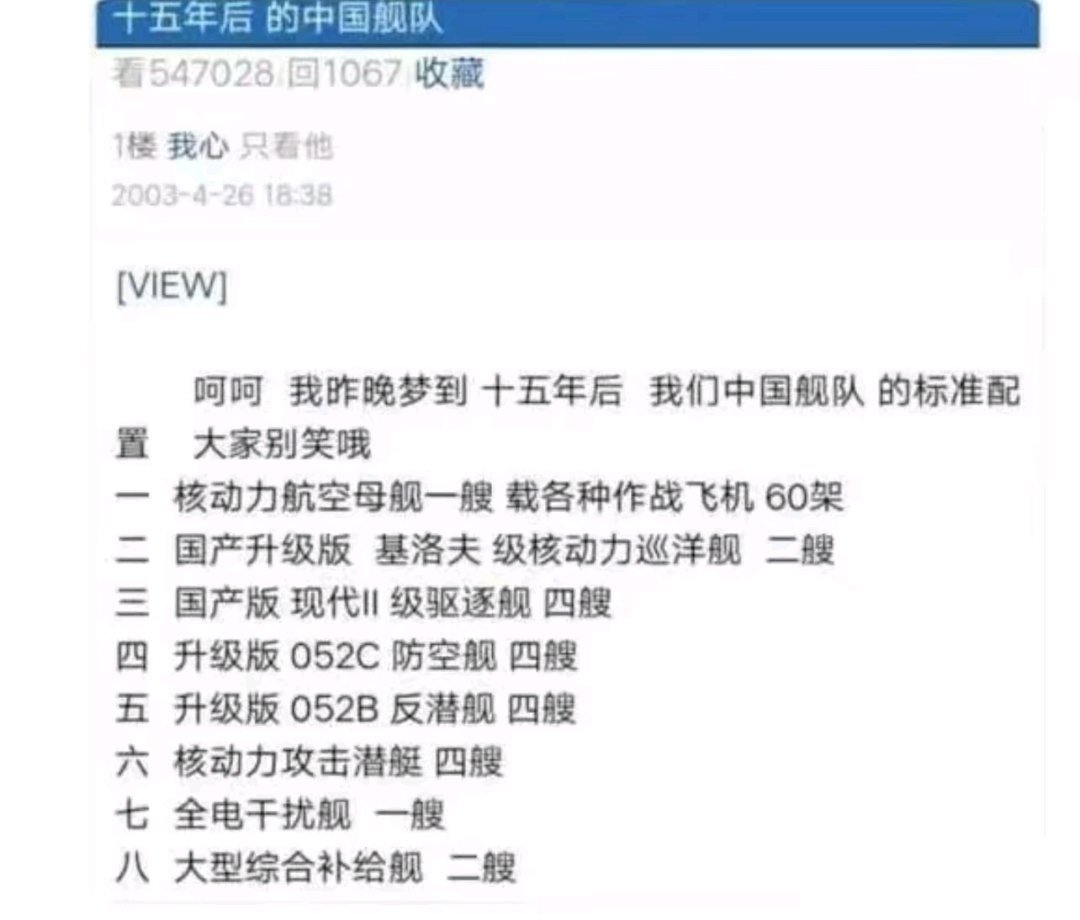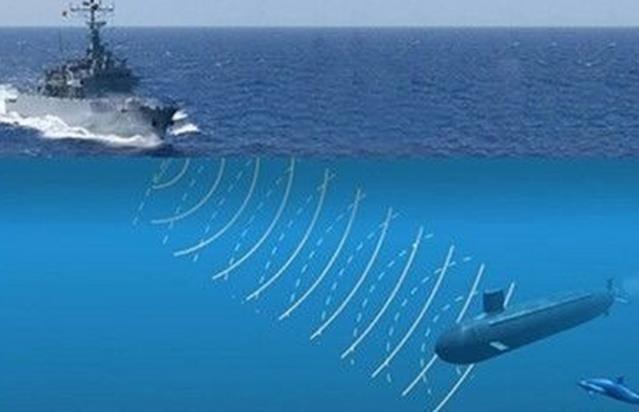1988年,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,顺道回了趟家看望母亲,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,望着30年未见的儿子,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......当那扇隔绝了三十年岁月的大门打开时,黄旭华看见了门后那个满头银丝的母亲,再也绷不住了,双膝一软,长跪在地,哭得像个孩子。 黄旭华出生于1924年,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普通乡医家庭,是家中第三个孩子,原名黄绍强。 父母行医多年,悬壶济世、深受乡邻尊敬,这种环境让他自小心怀敬意,也立志将来继承家业,为人解除病痛。 1938年,日军入侵沿海,许多学校停办。 年仅十四岁的黄绍强,随兄长前往揭西山区求学。 沿途崎岖山路,他与兄长走了整整四天,才找到所谓的中学,却发现学校早已被轰炸摧毁,原有建筑所剩无几,只留下一座弯曲扭曲的小楼,其余地方临时用稻草和竹竿搭建了简陋的教室。 尽管条件艰苦,学生们仍尽力学习,但日军轰炸机不时飞过,师生们不得不随时躲避。最终,中学不得不再次停办。 为继续求学,黄氏兄弟辗转桂林、重庆等地,沿途满目疮痍,老百姓流离失所、痛苦不堪。 少年黄绍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,他心中升起愤怒与疑问:“为什么敌机可以随意轰炸?国家如此脆弱,百姓如此受苦。” 从那一刻起,他决定放弃学医的初衷,立志学习科学,以求将来能为国家强大、抵御外敌贡献力量。 1958年,三十出头的黄旭华接到了一项绝密任务——为当时几乎一穷二白的中国,研制核潜艇。 彼时,美苏早已在深海中拥有先进潜艇,掌控战略制高点。 黄旭华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,但在整理行李的那一刻,他的心里满是对家人的牵挂。他明白,这一去,就意味着从亲人的生活里彻底“消失”。 从此,他不再只是父母的孩子、妻子的丈夫,而成了国家机密的守护者,一个隐形人。 家里的联系只剩下模糊的信件,信中反复写着:“在南方从事技术工作。”妻子独自承担起家中重担,却不能追问他的具体行踪;父母每日盼归,却只能面对无法兑现的归期。 与此同时,他肩上的责任沉重如山。 黄旭华和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,要在技术封锁和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,建造一艘核潜艇。 他们没有计算机,全靠算盘日夜计算复杂的数据;没有现成的设计图纸,就翻阅国外杂志,将零散的潜艇照片剪下,像拼图一样分析、推演。 在海边简陋的棚屋里,这群年轻人用最原始的方法,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。 为获得潜艇最关键的重心数据,他们甚至把成千上万的零件逐一称重、记录。 正是靠这种咬紧牙关的坚持,中国的核潜艇才从无到有。 而最沉的,是情感的重量。 三十年间,每一次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,都像石头压在他心头。 母亲在信里问:“什么时候能回家吃顿红烧肉?”他只能回答:“快了。”可这声“快了”,跨越了近三十年。父亲病重时,他仍在实验场上攻坚,未能见到最后一面。 二哥临终,他也未能陪伴,亲人的离去成了心中永远的痛。忠于国家、孝顺至亲,他只能把悲伤深埋心底。 直到1987年,母亲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儿子的报道,才明白,这个三十年未归的孩子,竟是在为国家研制核潜艇。 这迟来的理解,让黄旭华多年的愧疚终于有了出口,也让他肩上的那份沉重,得以被家人理解和尊重。 1988年进行的极限深潜试验中,黄旭华把肩上的全部重担——国家机密、技术难题以及深藏心底的亲情——带进了深海。在几百米深、足以压碎钢铁的海水中,他坚持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亲自下潜。他说:“我是总设计师,艇上每一个人的安全都由我负责。” 当核潜艇顺利浮出水面,船舱内响起一片欢呼,黄旭华却悄悄走到角落,从怀里拿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,用袖子轻轻擦拭。那一刻,他所有的付出和牺牲仿佛都有了答案。 黄旭华和他的团队,就是靠着这种坚韧与责任,将个人的牺牲化作国家的力量,打造出一件坚不可摧的“隐形铠甲”。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,有一种深沉的孝顺,不只是对家庭的守护,更是在国家需要时,将对亲人的爱转化为对国家最真切的忠诚。 参考资料: 北京日报 《他三十年未与父母团聚,为国“深潜”造出大国重器!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