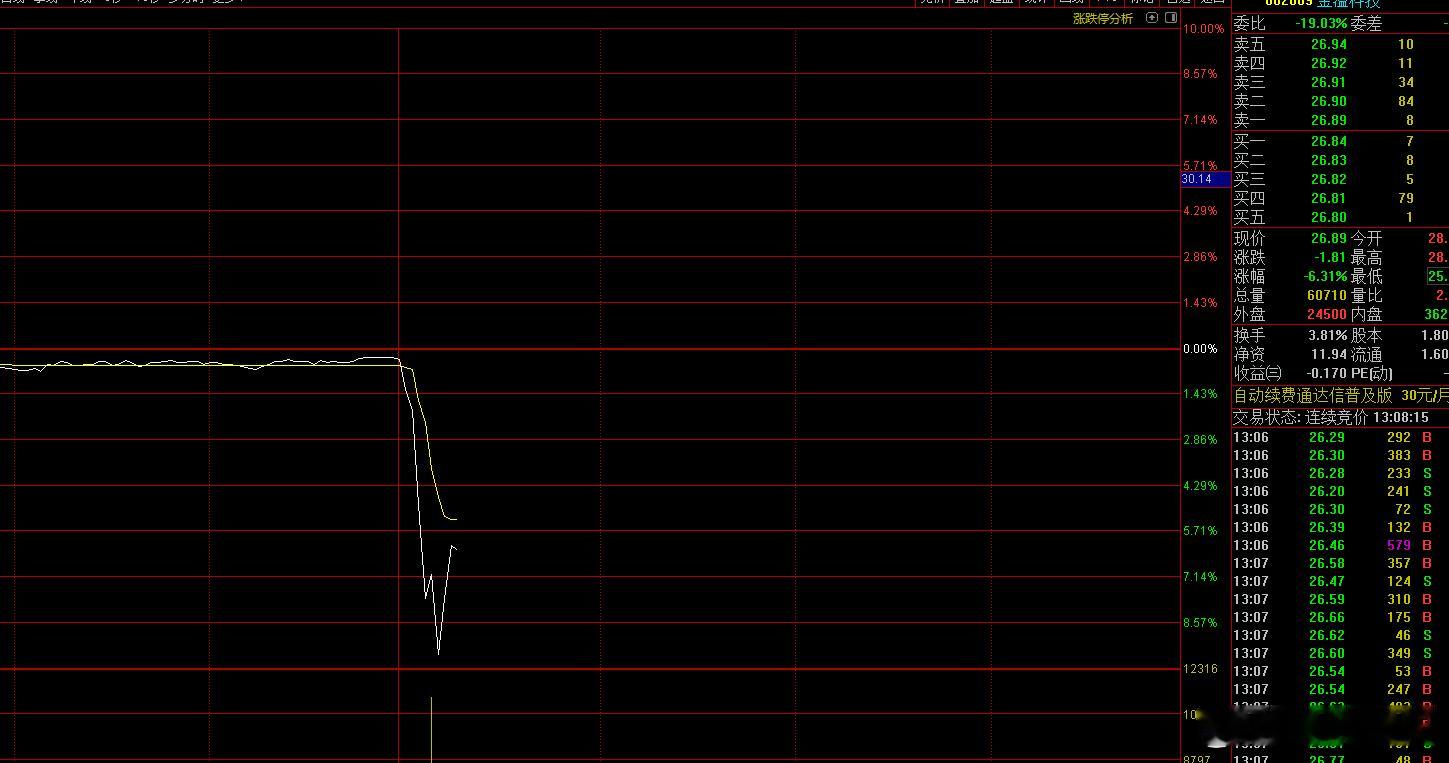多年以后,风烛残年的黄维双眼朦胧,内心悲恸,凝神看着那个身覆红旗的、已经是传奇的人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,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,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,感谢您的支持! 1986年,邓稼先的追悼会现场,黄维站在人群中,神情凝重,他已经八十多岁,身体略显佝偻,但站得笔直,他望着灵柩上覆盖的红旗,眼中是压不住的悲意,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送别,对黄维来说,那一刻,像是自己一生的历史在眼前缓缓展开。 邓稼先是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,他的名字在很多年里都鲜有人知,但国家的强大,离不开他那样的人,他的选择,是放弃国外的安逸生活,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,钻进戈壁滩里的实验室,那些年,条件艰苦到连最基础的设备都要自己动手造,他和同事们靠着一股劲儿,硬是在极限环境下,完成了核武器的突破,邓稼先的身体在那样高强度、带有辐射风险的工作下,一步步垮了,他默默承受,从不张扬,直到生命最后一刻,仍然没有离开岗位。 而黄维的故事,走过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,他是黄埔军校出身,曾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将领,参加过北伐,也参加过抗战,在抗战时期,他带兵打日本,立过不少战功,后来,随着内战爆发,他站到了国共对立的那一边,1948年,战局突变,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,从巅峰跌落谷底,一步之间。 被俘之后,黄维被关押、接受改造,他曾经不肯低头,不愿认错,甚至执拗得让人头疼,他坚持自己的立场,始终觉得自己为国家尽过力,不该被否定,但在漫长的岁月中,他开始思考,也开始观察,他看到了新中国在一步步建设,看到了百废待兴中涌现出的新气象,那些年,他被带去参观工厂、堤坝、铁路、桥梁,一路走、一路看,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反抗,而是慢慢沉默下来,开始接受现实,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。 1959年,第一批战犯被特赦,黄维的名字不在其中,这个消息对他和家人来说,是一次沉重的打击,他的妻子,一直在等待丈夫出狱的那一天,熬过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,最终精神也几近崩溃,后来,黄维被转移到抚顺,继续接受改造,在那个阶段,他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国家新的方向,他写信关心家人,寄钱为女儿治病,生活简单而节制。 1975年,黄维终于被特赦,身份不再是战犯,而是文史资料专员,他回到社会,开始参与政协的工作,积极参政议政,他不再是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将军,也不再是牢狱中的囚徒,他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,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国家的新篇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他常常说,过去的事不能抹去,但人总要向前看。 邓稼先的离世对全国来说是一种沉痛的损失,黄维站在追悼会现场,脸上没有过多表情,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,他知道,眼前这位科学家,为国家做了他永远无法企及的贡献,那一刻,他没有说话,也没有流泪,只是静静地站着,他并不熟识邓稼先,但他明白,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,是因为有像邓稼先这样的人,愿意默默无闻地奉献一切。 黄维这一生,走过了太多曲折,他曾是将军,是俘虏,是囚犯,是政协委员,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,也在改造中沉思悔悟,他的妻子,曾经是那个挺着大肚子站在庐山山脚望着他远去的女人,最终却在漫长的等待中耗尽了所有力气,她的离开,是黄维心中永远的痛,他为她写的挽联中,亲手落下“难妻”两个字,有人劝他改,他没有接受,他知道,这两个字写尽了她这辈子的委屈和苦难。 晚年的黄维,生活变得平静,他开始频繁参加政协会议,参与对台事务,还多次向台湾方面表达希望探访老同学的愿望,他说得很清楚,蒋介石是他的校长,陈诚对他有恩,而共产党也给了他新的开始,这种说法或许让人觉得不够“彻底”,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,有恩不忘,有错愿改,他不愿对任何一方虚伪,也不愿对历史撒谎。 1989年,黄维在搬家和“两会”准备之间突发疾病,被紧急送往医院,他没有留下遗言,也没有做任何交代,他的一生,在那个春天悄然画上了句号,他没有再穿上军装,也没有再回到战场,但他用自己的方式,走完了这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