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作曲家赵季平的夫人去世后,朋友第二年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,这个女人长的和他的夫人一模一样,大家都以为是他夫人的妹妹。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,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,感谢您的强烈支持! 西安音乐学院的老琴房里,阳光透过积尘的窗棂,在黑白琴键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 1962年那个闷热的午后,19岁的赵季平循着肖邦的夜曲推开门,看见一袭白裙的孙玲正在弹琴。 少女纤细的手指在琴键上起舞,发梢随着节拍轻轻晃动,这个画面从此烙印在赵季平心底。 琴房角落的节拍器滴答作响,空气中飘散着松香与旧乐谱特有的霉味,窗外梧桐树的影子在磨石地板上轻轻摇曳。 他们的爱情如同乐章般悠扬却曲折。 毕业后孙玲被分配到陕南小城,她怕耽误恋人的前程,默默切断了所有联系。 直到1972年深秋,赵季平在采风途中偶然走进一家县城供销社,发现柜台后的售货员正是失踪十年的恋人。 重逢时,孙玲正在整理货架,转身看见风尘仆仆的赵季平,手中的搪瓷缸"咣当"落地。 货架上堆着的红糖罐子被震得微微发颤,一缕阳光正好照在孙玲突然泛红的眼眶上。 婚后的孙玲毅然收起自己的音乐梦想。 1973年冬天,她挺着孕肚,用脸盆一趟趟从楼下搬运煤块。 冰碴子混着煤灰沾满棉鞋,她却始终抿着嘴微笑——丈夫正在屋里创作《陕南民歌三首》。 每当赵季平推开窗想帮忙,总被她用眼神制止: "你的手是用来谱曲的。" 煤块在脸盆里碰撞出清脆的声响,与屋内传来的钢琴声奇异地交织在一起。 1983年陈凯歌登门邀约时,赵季平正在为难。 孙玲却已默默打包好行李: "陕北风大,我给你织了新的毛线围巾。" 在黄沙漫天的安塞县,赵季平住在窑洞里记录民歌时,总会摸一摸围巾上细密的针脚。 后来《黄土地》的配乐里,那些苍凉婉转的女声吟唱,藏着他对妻子最深的思念。 围巾的蓝色毛线在黄土高原的风沙中渐渐褪色,却始终温暖如初。 2001年秋天,孙玲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完丈夫的演出后突然咯血。 诊断书上的"肺癌晚期"让赵季平彻夜未眠。 病床前,孙玲总是笑着安慰他: "可惜不能再听你写的新曲子啦。" 她离世前最后的要求,是让儿子学会做赵季平最爱吃的臊子面。 医院窗台上的茉莉花静静绽放,药水味中隐约飘着淡淡的清香。 失去妻子的日子,赵季平常常对着钢琴发呆。 乐谱上沾着泪渍,冰箱里放着发霉的饭菜。 直到2003年清明,好友张坚领着个眉眼酷似孙玲的女子出现。 张宁佳什么也没说,只是挽起袖子收拾满屋狼藉。 当她在厨房娴熟地抻开面条时,赵季平恍惚看见了亡妻的身影。 面条在沸水中翻滚,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窗玻璃,也模糊了他的视线。 更奇妙的是,张宁佳不仅与孙玲容貌相似,连很多生活习惯都如出一辙——都爱把钢笔别在衣领上,都会用同样的指法弹奏《黄河谣》。 她笑着告诉赵季平: "说不定是孙玲姐派我来照顾你的。" 书架上那本泛黄的《乐理教程》,两个女人都曾在同一页留下过批注。 再婚后的清晨,总能看到张宁佳为赵季平整理乐谱的身影。 书桌旁永远温着枸杞茶,就像孙玲在世时那样。 2016年赵季平创作大型交响乐《长安》时,张宁佳每天陪着他在工作室熬夜,在他揉太阳穴时适时递上眼药水。 作品首演成功后,赵季平在谢幕时突然转身,对着观众席上的妻子深深鞠躬。 舞台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掌声如潮水般涌来。 如今在赵季平的书房里,并排放着两张照片。 一张是孙玲在钢琴前回眸浅笑,一张是张宁佳在敦煌采风时为他撑伞。 照片下方压着发黄的五线谱,上面写着: "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" 两个女人用各自的方式,谱写了同一首关于爱与奉献的永恒乐章。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,琴房里的音符永远在流淌。 主要信源:(人民文摘——音乐大师的灵感女神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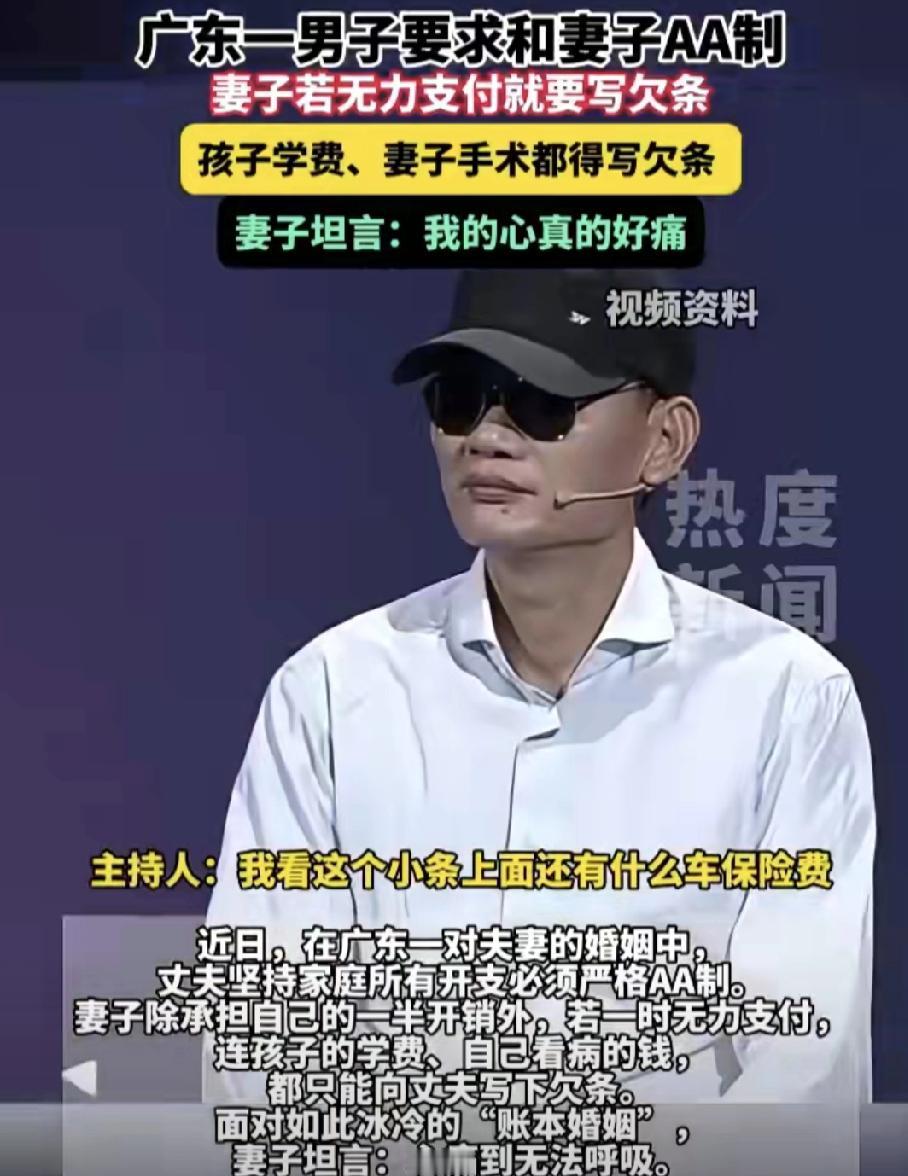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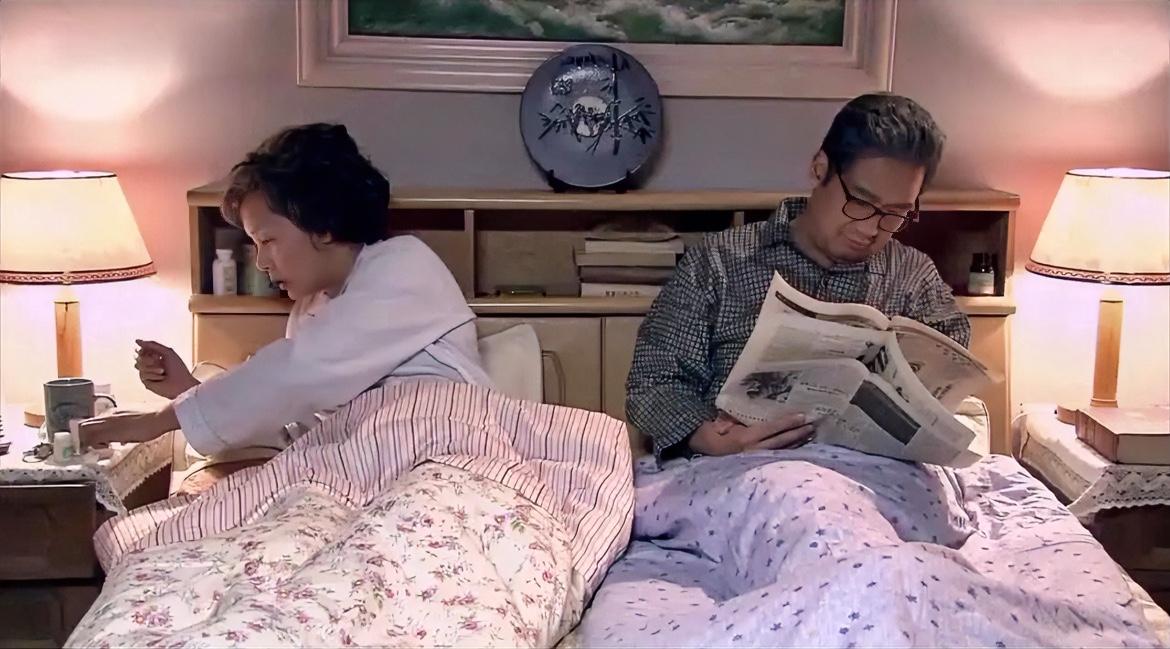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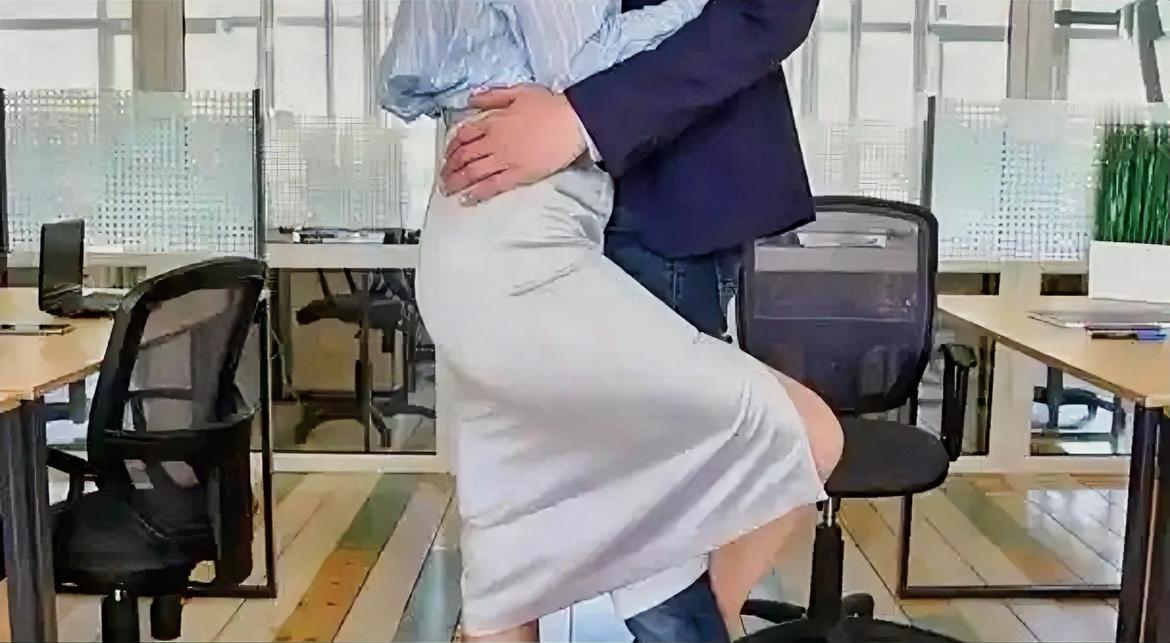

![闺蜜团,能一眼看出谁结婚了吗?[捂脸哭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1781014935424926314.jpg?id=0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