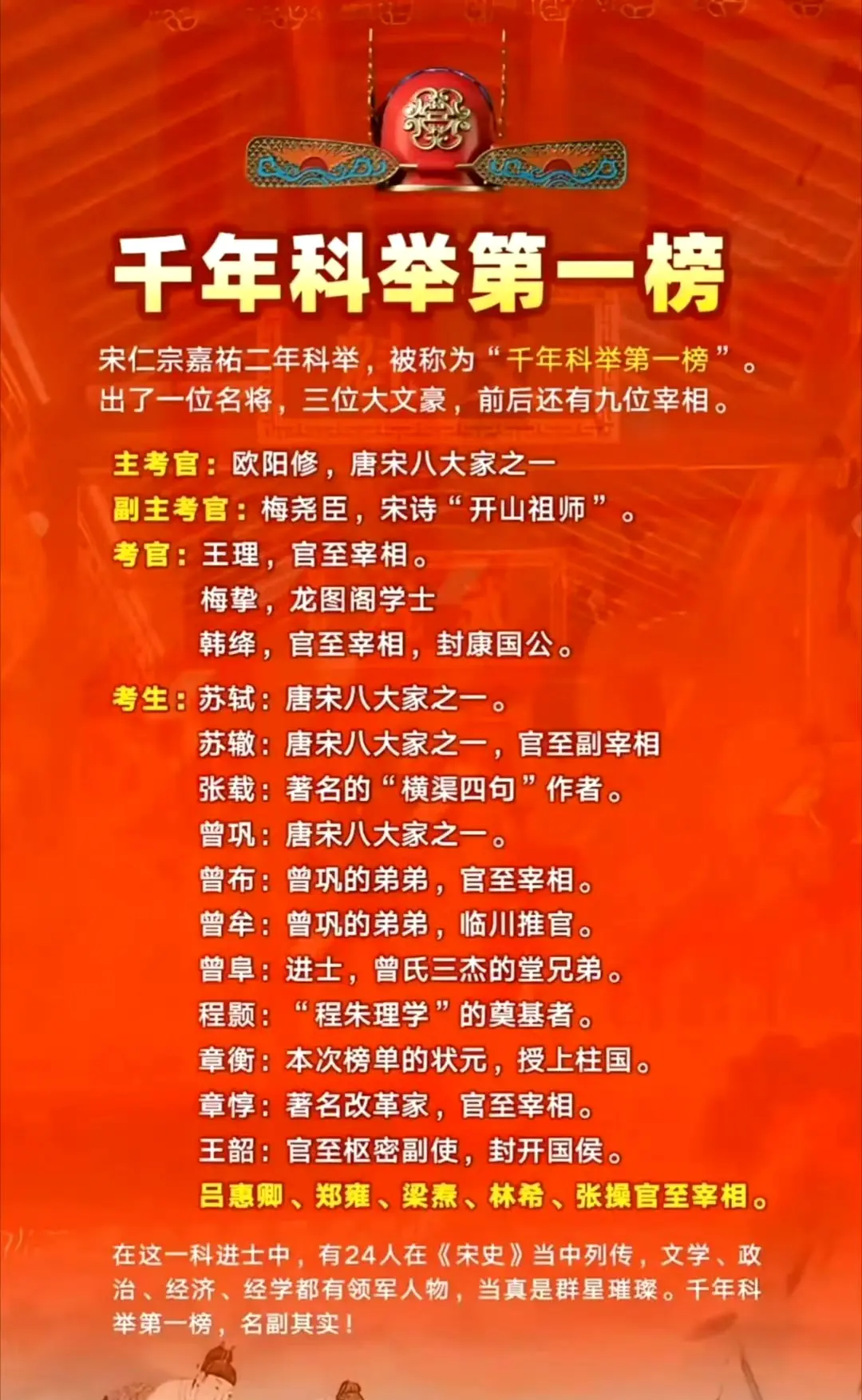北宋年间,江南一个财主的小妾月儿,因腰伤走路一拐一拐,财主将她赶出家门,两年后,财主再见月儿,发现她恢复了人也娇俏了,财主想再续前缘,但他却有一点想不通,当初花了不少钱都没治好,她怎么就自己好了呢? 北宋那会儿,江南有个大地主李家,大少爷李承乾娶了个跳舞顶呱呱的舞姬月儿当小老婆,疼得跟眼珠子似的。结果大房孙氏和其他小老婆们眼红了,合计着给月儿下个套,让她把腰给摔坏了。请来的名医王琚直摇头,说这腰伤没法治。李承乾一看,心凉了半截,干脆把月儿给打发走了。 月儿被赶出门那天,江南正下着梅雨季的冷雨。 她裹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袍,腰里缠着李承乾最后赏的半匹麻布,一步一挪地往城外走。孙氏站在门楼上啐了口,说她是“占着茅坑不下蛋的废物”,声音尖得能划破雨幕。月儿没回头,她知道,这深宅大院里的“疼惜”,从来都挂在钱串子上——她能旋出惊鸿舞时,是李承乾掌心里的珍珠;腰一坏,就成了沾不上手的烂泥。 出城三里地,她在破庙里遇见个拾柴的老婆婆。老婆婆看她疼得直冒冷汗,从竹篓里摸出个油布包,里面是晒干的艾草和几块黑乎乎的药膏。“丫头别怕,”老婆婆的手糙得像老树皮,却捂得她后腰暖烘烘的,“我那口子年轻时扛木头伤了腰,就是靠这野草片子熬好的。” 月儿就在山脚下租了间茅屋住下。 每天天不亮,她就跟着老婆婆去采草药。晨露打湿裤脚,山路硌得脚底生疼,可弯腰、伸展、用热草药熏腰时,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松开——不只是腰上的筋,还有心里那团拧了许久的气。她不再是那个踮着脚尖盼着李承乾来的小妾,不用再看孙氏的脸色,不用再强撑着伤痛练舞讨好人。 夜里没事,她就坐在灯下绣帕子。针脚从歪歪扭扭到细密匀整,绣的不是李家喜欢的牡丹,是山间常见的野菊,黄灿灿的,带着股子野劲儿。腰还是会疼,但疼得实在,不像在李家时,总掺着慌和怕,疼得人直打颤。 两年后的清明,李承乾去城外上香,在渡口撞见个挑着绣品担子的姑娘。 那姑娘回眸一笑,眼尾的痣亮得像点了胭脂,走路时裙摆扫过青石板,轻快得像风拂柳。李承乾看直了眼,直到姑娘开口问“客官要绣帕子吗”,他才惊觉——这不是月儿吗? “你……你的腰?”李承乾指着她的腿,话都说不利索。 月儿把绣帕往竹筐里一收,笑意淡了些:“早好了。” “怎么可能?”李承乾急了,“王神医都说没法治!我当初请了多少大夫,砸了多少银子……” “李公子怕是忘了,”月儿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线头,动作自然得很,“您请的大夫,都是孙氏夫人找的。” 这话像根针,扎得李承乾哑了火。 他这才想起,月儿刚受伤时,王琚开的药总带着股怪味,月儿喝了就吐;后来换的大夫,每次来都先去孙氏院里问半天话。那时他只当是月儿娇气,如今想来,那些药汤,怕是治不好病,也断不了根,就吊着她,让她永远是个走不了路的废人。 “那你是怎么好的?”李承乾还不死心,从怀里摸出个金镯子,“跟我回去,以前的事……” “不必了。”月儿往后退了半步,避开他递镯子的手,“山里的老婆婆说,我这腰不是骨头断了,是筋扭了,又郁了气,才僵得动不了。离开李家,气顺了,再用草药慢慢熏,自然就好了。” 她顿了顿,看李承乾的眼神,像看块没捂热的石头:“其实治腰不难,难的是心里不堵得慌。李公子府里太挤,我的腰,舒展不开。” 风卷着桃花瓣落在李承乾的官靴上,他忽然明白,自己当初砸的那些银子,治的哪是腰伤?不过是想把月儿钉在“有用”的位置上。一旦没用了,便弃如敝履。倒是这两年清苦日子,没花什么钱,却让她把心里的结、腰上的僵,全舒展开了。 月儿挑着担子往镇上走,背影轻快得很。 李承乾捏着那只金镯子,站在渡口,看着她的身影融进赶集的人群里,像滴墨落进清水,再也找不着了。他到最后也没彻底想通,但心里某个地方,空落落的,比当年月儿拐着腿离开时,还要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