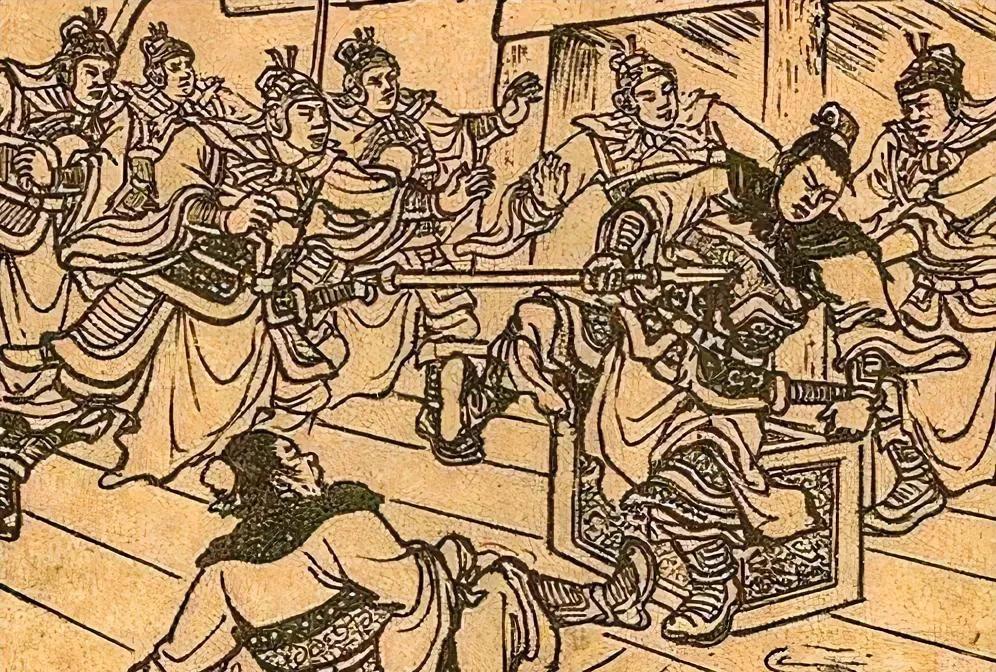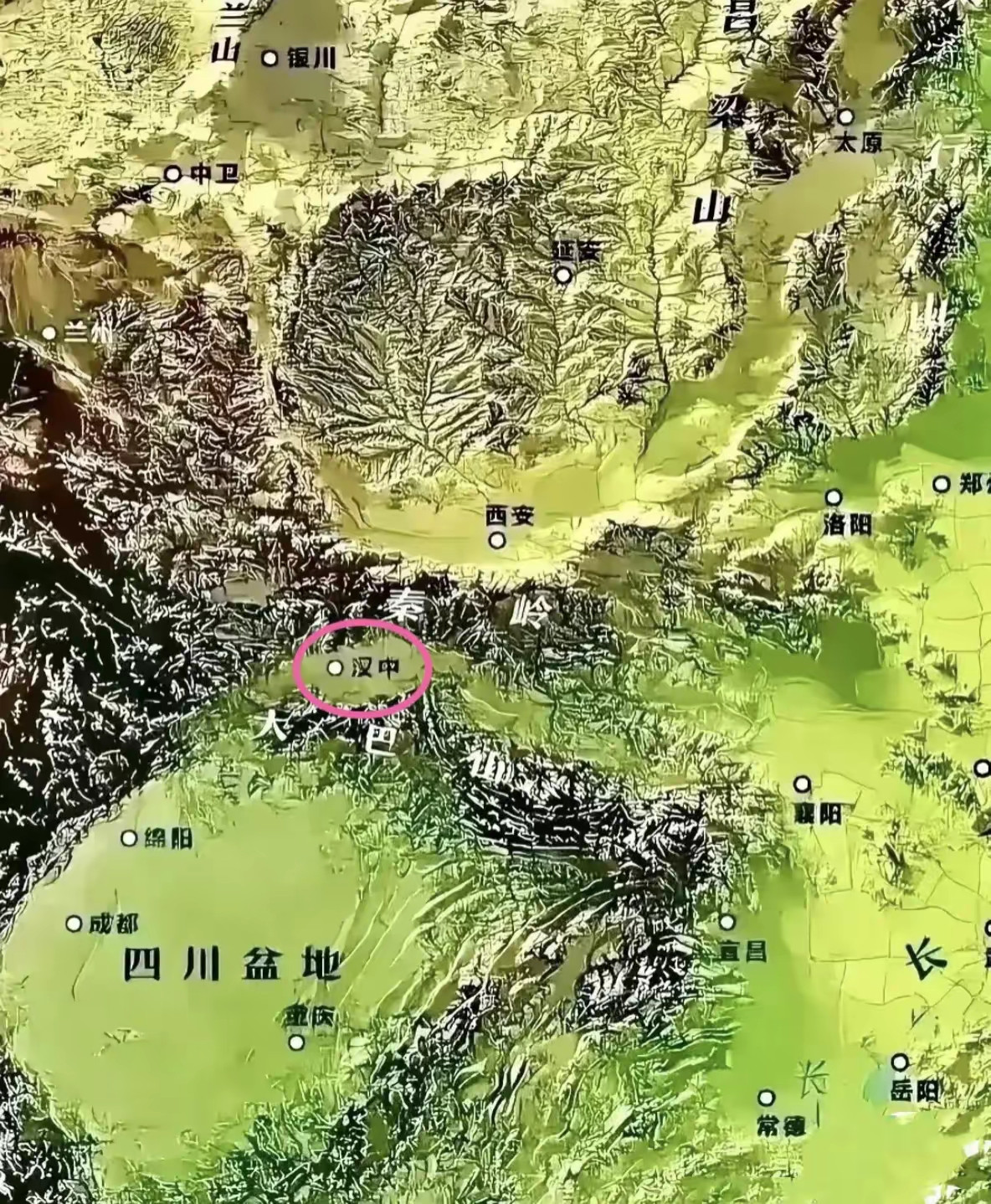公元445年,范晔因为参与谋反,被关在了死牢里,等着被处决。有个狱吏跟他开玩笑说:“范大人呐,听说您的死罪免了,改成长期关着啦。”范晔居然就信了,松了口气说道:“那可太好了,总算是保住一条命。” 元嘉二十二年的腊月,廷尉诏狱深处,范晔裹着单薄的囚衣,蜷在铺着烂草的角落。寒气顺着石墙缝钻进来,冻得他牙齿打颤。范晔闭着眼,脑子里却像开了锅的粥,翻腾着过去几个月的事,转念一想那狱吏的话像根救命稻草,一下子把他从绝望的泥潭里捞出来一点。 保住命了!范晔心里那点死灰,仿佛又腾起点火星子。长期关着?那有啥!活着就有希望,活着就能等来转机。他范晔是谁?是写出煌煌《后汉书》的大才子,是曾经皇帝身边说得上话的近臣!只要命还在,凭他的才华、人脉,将来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。他开始盘算,出去了要如何如何,甚至觉得这牢房里的寒气也没那么刺骨了。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。 范晔,这位在史册里纵横捭阖、臧否千古人物的史学家,此刻却像个天真的孩童,轻易相信了一个狱卒毫无根据的戏言。他笔下那些因轻信谗言而身死族灭的帝王将相,那些在权力旋涡中迷失心智最终陨落的豪杰,那些血淋淋的教训,此刻仿佛都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背景板。历史这面镜子,照别人时纤毫毕现,轮到自己,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、名为“求生欲”和“侥幸”的尘埃。 问题出在哪?是范晔不够聪明吗?显然不是。是他不懂得历史的教训吗?更不可能,《后汉书》字里行间都是他的洞察。说到底,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彻底扭曲了他的判断力。当死亡的黑影紧紧扼住喉咙,任何一点微光都会被无限放大,变成足以遮蔽理智的太阳。他太渴望活下去了,以至于本能地抓住任何一丝可能的生机,哪怕它荒谬得像水中的月亮。那份对生的贪婪渴望,瞬间击溃了史学家应有的清醒和警惕,让他变成了自己笔下最该怜悯、也最该警醒的那类人——在命运无常的刀刃下,因一念之差而堕入深渊的聪明人。 他参与谋反,本就是一场豪赌,赌注是自己的身家性命。赌输了,被押上刑场,这结局本不意外。但狱吏一句玩笑,竟让他重燃希望,这份希望本身,恰恰暴露了他骨子里对权力、对重回舞台中心那份难以割舍的执念。他幻想的“将来”,依然是依托于那个他曾试图颠覆(或参与)的权力结构。他念念不忘的“才华”与“人脉”,本质上还是他赖以攀爬权力阶梯的工具。这份深入骨髓的、对权力地位的眷恋,在死亡的绝对恐惧面前,扭曲变形,成了他接受谎言的心理基础。他不仅输掉了政治赌局,甚至在面对最终审判时,连那份洞察世事的清醒也输掉了。 腊月里的寒风似乎更猛烈了,卷着细碎的雪沫,从牢房高窗的缝隙里灌进来。范晔裹紧了那件破旧的囚衣,试图汲取一丝暖意,脑子里却开始不受控制地描绘出狱后的景象:温暖的炉火、新酿的酒、朋友们劫后余生的唏嘘、或许还有机会重新拿起笔,修订他那部引以为傲的史书……生的诱惑如此巨大,淹没了所有理性的声音。 突然,沉重的铁链撞击声由远及近,在死寂的牢狱甬道里显得格外刺耳。脚步声停在门外,锁孔传来冰冷的转动声。几个面无表情的狱卒走了进来,手里拿着的不是饭食,而是沉重的枷锁和绳索。范晔的心猛地一沉,像块石头直坠冰窟。他抬起头,对上狱卒毫无波澜的眼睛,那里面只有执行命令的漠然。 “时辰到了。”为首的那个声音平板,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。 刹那间,那狱吏带着戏谑眼神说“保住命了”的画面,在范晔脑中轰然破碎。假的!全都是假的!巨大的恐惧和荒谬感瞬间攫住了他,比腊月的寒气更刺骨。他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,不是冷的,是绝望的痉挛。他想喊,喉咙却像被堵住;他想质问,嘴唇哆嗦着发不出一个清晰的音节。狱卒上前,毫不费力地架起他瘫软的身体,沉重的木枷压上肩头,粗糙的绳索勒进皮肉。他被半拖半架地弄出了牢房。 就在即将踏上刑台的那一刻,一股强烈的悲怆和一种奇异的清醒,如同冰冷的洪流,猛地冲垮了他心中最后一点侥幸和幻想。他忽然仰起头,对着灰蒙蒙、飘着雪的天空,用一种近乎嘶吼、又带着巨大讽刺的语调,喊出了那句注定被史书记载的话: “可惜!可惜!白落了这么个好脑袋!”(注:史载范晔临刑前感叹:“可惜!满腹经纶,葬送此地。”或类似表述,此处理解为对自身结局的悲愤与自嘲。) 话音未落,也或许是被风声吞没。雪,下得更急了,洁白的雪花无声地飘落,覆盖着肮脏的刑场,也即将覆盖一切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