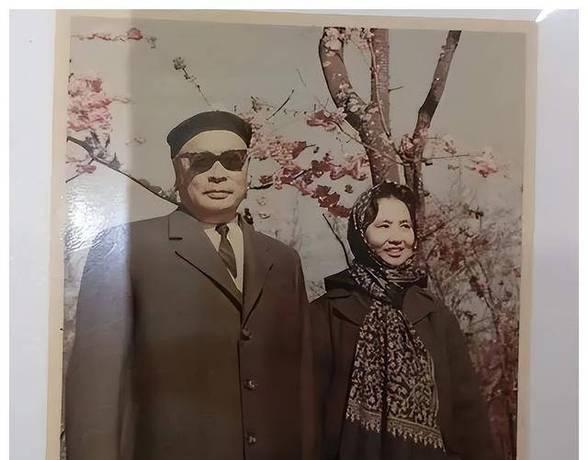1938年皖南的清晨,浓雾像掺了水的米浆,死死黏在茂林镇的青石板上。陈毅裹着灰布长衫,毡帽檐压到眉毛,鞋底沾着碎草,踩着湿滑的石板路往街角烟店走。这地方看着普通,却是十字路口的"消息枢纽",南来北往的商贩、挑夫都爱在这儿歇脚,正是打探情报的好位置。
掀开门帘时,煤油灯晃出的光晕里飘着股怪味——烟丝混着煤油,还有股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。柜台后的老头驼着背擦玻璃罐,手腕突然翻过来,陈毅眼尖,瞅见一圈发黑的环状伤疤,像铁链勒进肉里留下的印记。
"来包老刀牌。"陈毅摸出银元,声音压得粗哑。老头转身拿烟时,柜台角落的日文账簿露了出来,横平竖直的字符在磨破的封皮上格外扎眼。陈毅心里"咯噔"一下——上月培训时,教官特意展示过特高课间谍的特征,手腕的环状疤就是他们的"身份证"。
"掌柜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啊?"陈毅划着火柴点烟,眼角瞥见老头手指往柜台底下伸。门外闪过黑影,老头眼仁猛地一缩,陈毅假装没看见,摸出火柴又问:"再给盒洋火。"
这一拖延,街对面的动静全收眼底:几个穿短打的汉子端着茶杯,眼睛直往烟店里瞟。陈毅心里有数了——这是放哨的。他假装看布料,实际盯着烟店后门,果然没一会儿,黑褂子男人低着头往镇外跑。
傍晚,陈毅带着战士抄近路堵后门。老头正趴在柜台记账,听到动静猛地抬头,笔"啪嗒"掉在账本上,墨汁晕开大片。
"客官又来啦。"老头转身拿烟,手抖得抓了好几次。陈毅盯着他后腰鼓囊囊的轮廓,突然掀翻柜台——两把黑枪"咔嗒"对准他,老头扯着嗓子喊"八嘎",陈毅动作更快,"砰"一声,子弹正中眉心。
战士扯开老头袖子,那圈黑疤在灯光下清晰可见。脱下裤子,里头竟是日军制式兜裆布,白布上印着小太阳。鞋后跟磨损得厉害,边缘起毛,陈毅蹲下身说:"这是长期骑马磨的,普通老百姓谁天天骑战马?"
搜出的密码本更惊人:"三营运输队""军部粮仓"等字样密密麻麻,全是新四军的机密。小李押来的黑褂子男人招了:老头真名山本龟次郎,特高课行动组,潜伏三年,靠烟店传递情报,前两次运输队遇袭就是他报的信。
军部连夜开会,陈毅把带血的密码本拍在桌上:"这就是特高课的阴招!他们不跟咱们拼刺刀,就躲在老百姓里当眼线。一个疤、一句话,都能要咱们弟兄的命!"
后来,密码本被破译,新四军端掉三个情报点。茂林镇的烟店贴了封条,风一吹"哗啦啦"响,像在提醒路人:这里曾藏着吃人的阴谋。
如今,那本密码本躺在纪念馆里,血迹变成深褐色。讲解员总指着它说:"情报战没硝烟,却比枪炮更狠。一个细节,能保千百条命。"
茂林镇的老人常给孩子讲:"当年有个将军,就瞅了眼手腕的疤,一枪打断了鬼子的情报网。"和平年代,咱们更得睁大眼——那些暗处的"疤",可能换了模样,但只要多留个心眼,就不怕它们作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