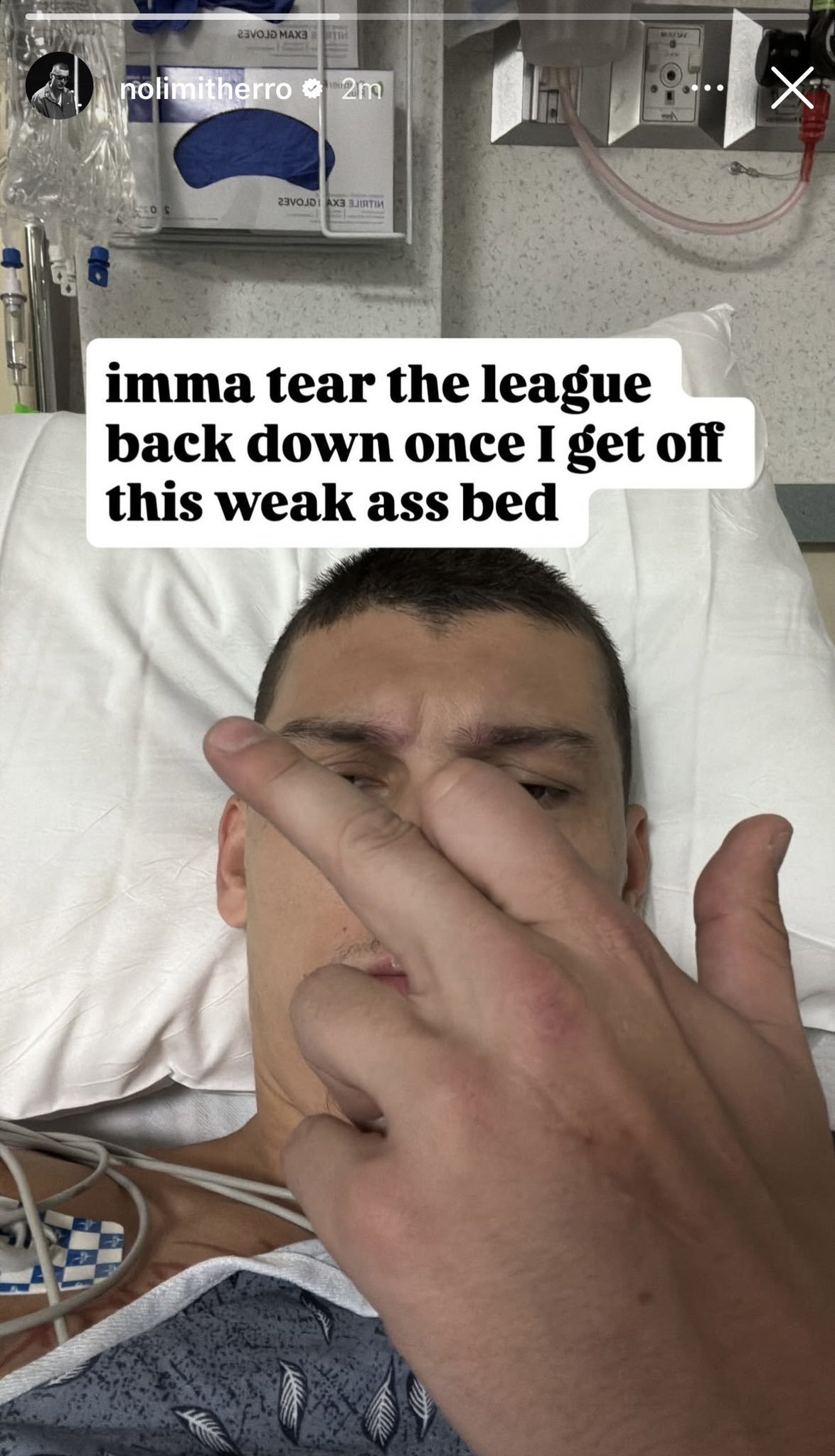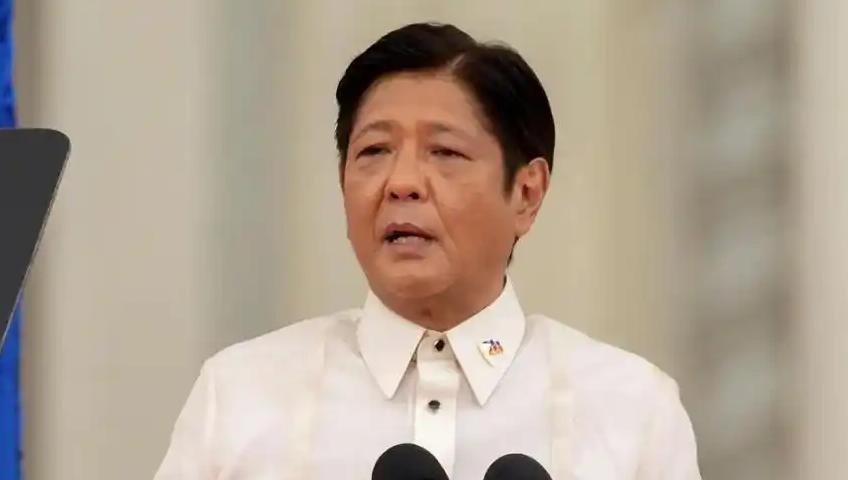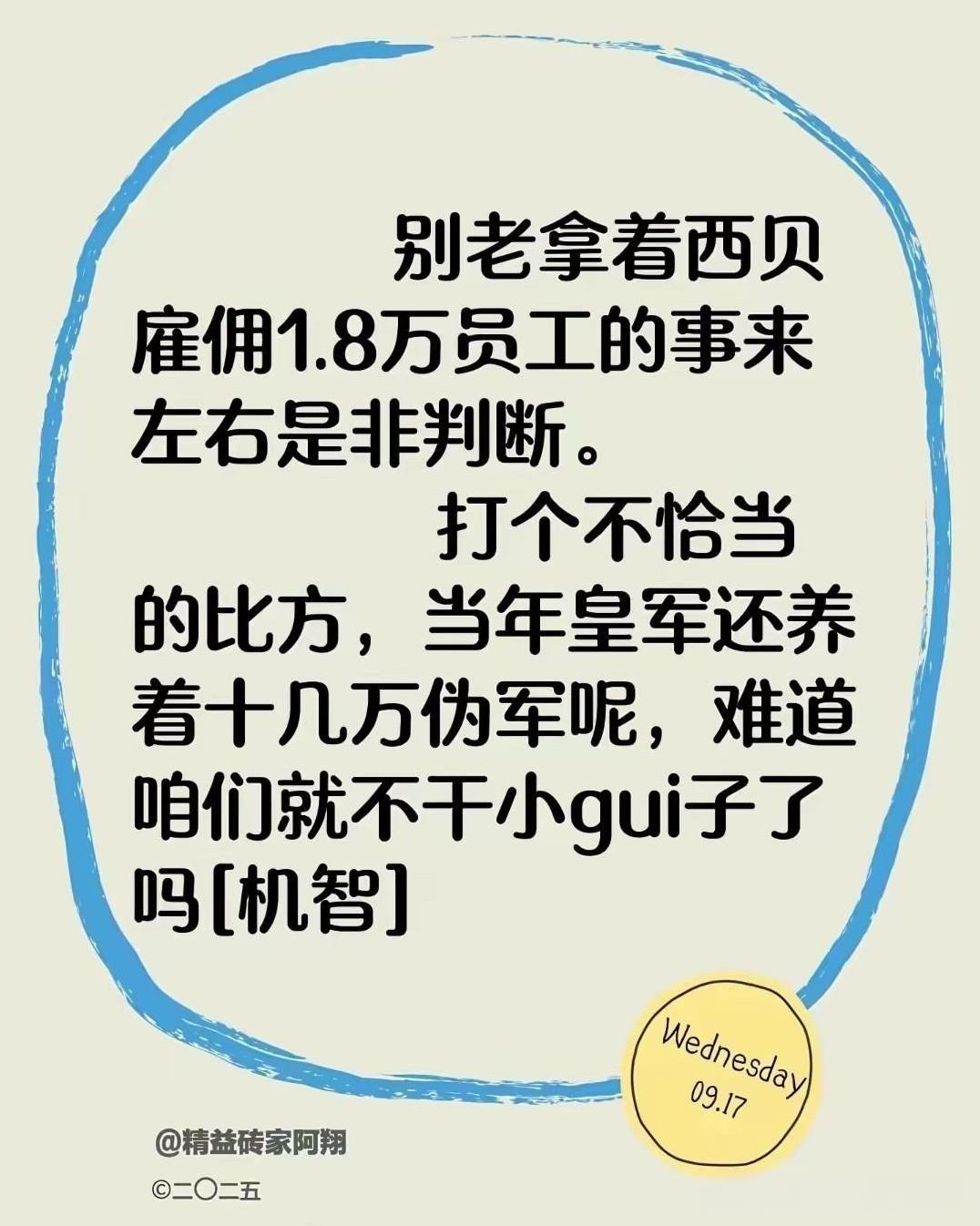1911年,林徽因叔叔林觉民牺牲后,遗书由友人带回老家,途中遇到土匪,土匪看完遗书后,扑通一声跪倒在地,乞求原谅,最后将行李如数奉还,并一路护送友人离开。 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的一个书香家庭,家中藏书成堆,祖辈都是读书人,父亲林孝觊是廪生,清贫却讲究格局,从小,林觉民就被要求读四书五经,写小楷,练诗文,可这个孩子总不安分,十三岁那年,他第一次参加童试,别人都在考场里奋笔疾书,他却只写了一句“少年不望万户侯”,便起身离席,那句话不是诗词,也不是策论,而是他对现实科举制度的反抗,他不想做官,他想改变这个国家。 后来,他进入了全闽大学堂,那是福建最早的新式学堂,课程中加入了西方的科学、政治和历史,他在那里接触到了许多思想激进的著作,比如《天演论》和《革命军》,这些书像火种一样点燃了他心里的革命热情,他开始频繁演讲,内容多谈国家危机与民族觉醒,甚至连当时的学监都说:“亡大清者,必此辈也,”他的理想逐渐清晰,他要为国家寻找出路。 1905年,他被迫接受了家中的婚姻安排,娶了陈意映,这场婚姻本是长辈定下的,出乎意料地成了一段深情的结合,陈意映出身官宦之家,却识大体、明大义,在家中,她和林觉民一同设女学、办读书会,还劝说家族中的女子放足,她不只支持丈夫的思想,还亲自参与,他们的家,成了一个小型的思想实验场。 1907年,林觉民东渡日本留学,在那里,他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哲学,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他的朋友圈里,有黄兴、宋教仁这样日后名动天下的革命者,他们在夜里开会,白天印传单,密谋如何推翻清朝统治,林觉民在东京拍了一张西装照,寄回家,背后写着“愿以吾辈之青春,守护盛世之中华”,那一年,他二十岁,眼里只有理想。 1911年春天,他突然从日本回到福州,他告诉家人,说是日本学校放了樱花假,顺道回家看看,其实,他是接到起义的密令,要赶赴广州,那时,陈意映已经怀孕八个月,他在家中一边筹备,一边强作镇定,他知道这次离开,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 起义前夜,他在香港的滨江楼写下了两封信,给父亲的只有三十几个字,言辞简短,语气沉稳,给妻子的那封信却写了三张纸,整整一千多字,他写下两人的过往,写下他对未出生孩子的期望,也写下他为何要舍弃家庭走上这条路,他说,正因为爱她,才愿意为天下人争取爱的权利,他用“吾充吾爱汝之心,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来解释自己的选择,那封信没有宣言,却比任何宣言都坚定。 三天后,广州起义爆发,林觉民作为“选锋队”成员冲入两广总督署,带着炸药和武器,他和同志们连续作战数小时,终因寡不敌众被捕,他身中多弹,血流不止,却仍昂首挺立,审讯时,他言辞激昂,毫无悔意,总督张鸣岐听完他说话,感叹这是个“面貌如玉,肝肠如铁”的奇男子,那年,他24岁。 他被关押在广州天字码头的牢房里,五天后,行刑之日,他不肯跪地,不肯蒙眼,从容赴死,他的遗体被草草掩埋,家人无法见他最后一面。 那封信成为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,信由友人力钧保管,夹在棉袄中,准备送回福州,途中在闽粤交界险些遭袭,土匪将他们的行李洗劫一空,唯独留下那封血迹未干的信,据传,土匪首领读完信后沉默良久,竟下令归还全部财物,并派人护送力钧离开,这段故事后人多有演绎,但信件最终确实安全送达福州。 陈意映在光禄坊的亲戚家避难,那天夜里,友人叩门送来信件,她读到“汝腹中之物,吾疑其女也……”时,悲痛过度,当场昏厥,数日后早产,生下遗腹子林仲新,这个孩子由祖父抚养长大,后来成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,但他的母亲,在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中渐渐沉默,两年后郁郁而终,年仅22岁。 林觉民的信被林家保存多年,1937年抗战爆发,为防信件遗失,林仲新委托堂兄林性奎将其送回福州,当时正值动荡,途中再一次遇险,林性奎死死护住那封信,最终将其送达安全之地,1959年,林仲新将信件捐赠国家,现收藏于福建省博物院。 林觉民的故居仍在,位于福州杨桥东路17号,白墙素瓦,门前石阶早已磨平,门楣上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七个字,是他一生的写照,1991年,福州市委现场办公时,决定原址保护此宅,作为历史的见证,后人常在此朗诵那封信,那些字句,穿越百年,依然震撼人心。 林觉民没有活过二十四岁,却留下了一封穿透时代的信,他用最平实的文字,写下最深的情感与最坚定的信仰,这封信不是文人的抒情诗,也不是战士的决绝书,而是一个普通人在国家生死关头做出的抉择,那是对妻子的告别,也是对民族的承诺,如今再读,依旧让人热泪盈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