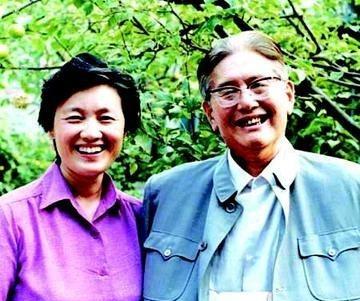公元前535年,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去世。曲阜的秋天来得早,颜徵在咽气时,院子里的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。十七岁的孔子跪在榻前,握着母亲枯瘦的手,那双手曾无数次为他缝制衣裳,为他在油灯下抄录竹简。他想起三天前母亲还强撑着坐起来,指着窗外的杏树说:“等你父亲的坟找到了,就把我葬在他身边。” 这话像根刺扎在孔子心上。他是父亲叔梁纥与颜徵在野合而生,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。母亲带着他离开陬邑大夫府,在曲阜阙里的陋巷里安家。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从未断过,孩子们追着他喊“野种”,颜徵在总是把他护在身后,用木棍赶走那些顽童,回家后却抹着泪教他认字:“阿丘要好好读书,将来做个体面人。” 母亲说的“体面”,是让他成为士阶层。那时的鲁国,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官学。颜徵变卖了陪嫁的唯一一支玉簪,托人把孔子送进私学。他还记得第一次领到《诗经》竹简时,母亲在灶台边熬着野菜汤,火光映着她眼角的细纹,那是他见过最美的模样。 如今母亲走了,连父亲的坟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按照周礼,父母合葬才算尽孝,可叔梁纥的墓地早被主母藏了起来——那个女人恨颜徵在夺走丈夫的宠爱,更恨这个“孽种”可能分走家产。孔子穿着麻衣在曲阜城外奔波,逢人就问陬邑大夫的旧坟址,脚下的草鞋磨破了底,脚后跟渗出血珠,混着尘土结成硬痂。 有个放羊的老汉指着一片荒草坡说:“前几年见过有人来这里烧纸,说是纥大夫的坟。”孔子扑在齐腰深的草丛里,用手扒开泥土,果然摸到一块半截的石碑,上面模糊的“纥”字被风雨侵蚀得只剩轮廓。他趴在碑上哭得撕心裂肺,像是要把十七年的委屈全倒出来——那些母亲夜里的叹息,那些他装作听不懂的嘲讽,原来都藏在这不知名的孤坟里。 安葬母亲那天,孔子按照周礼守在墓前。他堆起土丘,在旁边种了棵柏树,早晚祭奠时都要背诵母亲教他的《孝经》片段。有个姓孟的老人路过,看着这个瘦高的少年在寒风里瑟缩,却依旧行礼如仪,忍不住感叹:“这孩子,懂礼啊。” 守孝三年里,孔子把自己关在屋里,把母亲留下的竹简读了一遍又一遍。颜徵在生前总说,她没见过叔梁纥的模样,只听人说他是个能举起城门的勇士。孔子对着父亲的画像,在竹简上写下“孝悌”二字,笔尖划破竹片,像是划破了那些年母亲隐忍的时光。 三年期满那天,孔子脱下麻衣,换上母亲生前为他缝制的儒服。他站在阙里的路口,看着往来的行人,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苦心。那些年教他的礼仪,不是为了“体面”,而是为了让他在混乱的世道里守住本心。他开始在巷口设坛讲学,不管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少年,只要愿意学,他都倾囊相授。有人嘲笑他“一个野种还敢教书”,他只是笑笑,继续在杏树下讲解《周礼》。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,每次路过陬邑,都会绕道去父母合葬的墓地。他带着弟子们在墓前行礼,指着那棵已经枝繁叶茂的柏树说:“我少年时不知父亲何在,是母亲用孱弱的身子为我撑起一片天。她教我的,不只是认字,是如何做人。” 世人都知孔子强调“孝道”,却少有人知道这背后藏着一个少年对母亲的亏欠。他说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或许是想起自己年轻时为求学离开母亲的愧疚;他说“入则孝,出则悌”,或许是想让天下的孩子都能体面地为父母尽孝,不用像他那样,连父亲的坟都要找遍荒坡。 《礼记》里记载,孔子为母亲守孝三年,期间不歌不乐,连肉的味道都尝不出来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他“少孤,贫且贱”,却没细说颜徵在如何在陋巷里为他筑起精神的城墙。 你看,那些影响后世的思想,往往源于最朴素的情感。母亲的坚韧,成了孔子一生的底色;少年时的困顿,让他懂得了礼的真正意义。若没有颜徵在在陋巷里的坚守,还会有后来的孔夫子吗? 信息来源:《礼记·檀弓》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