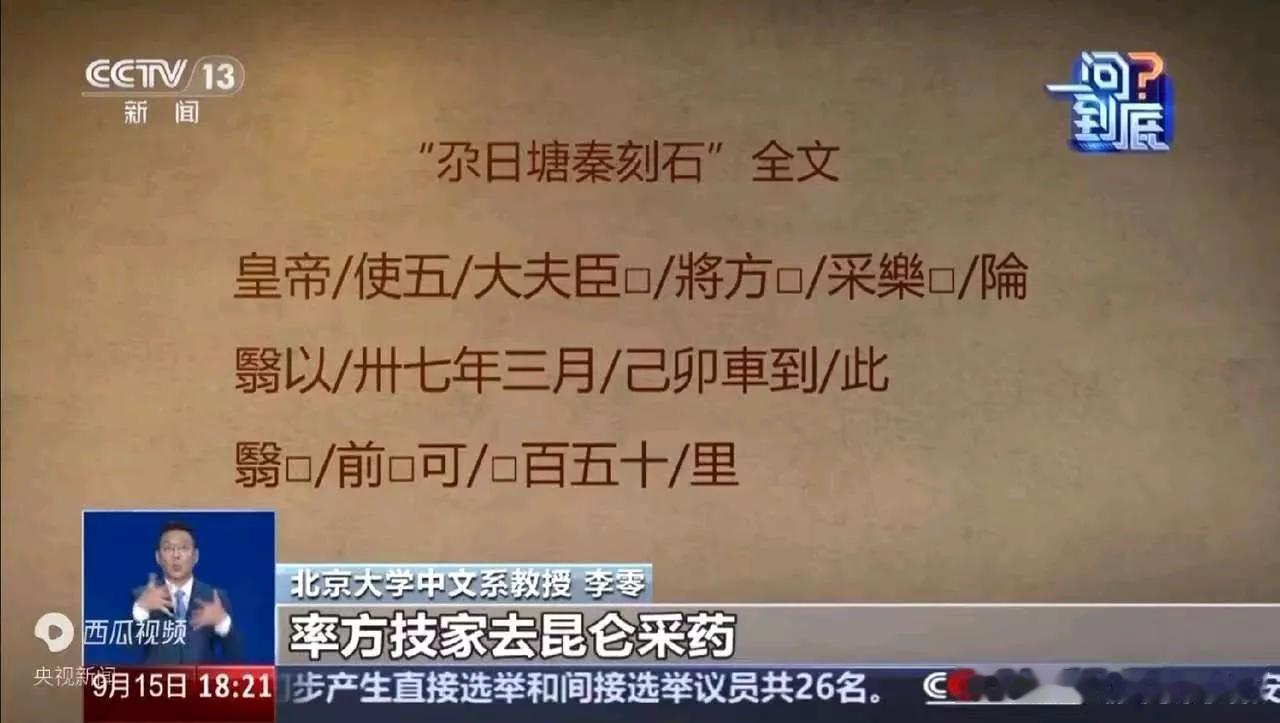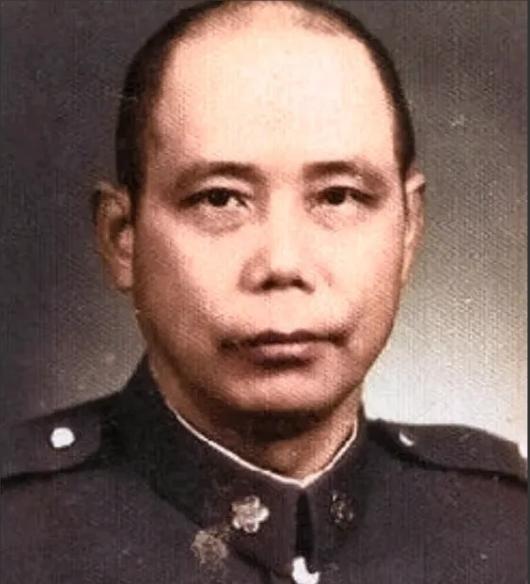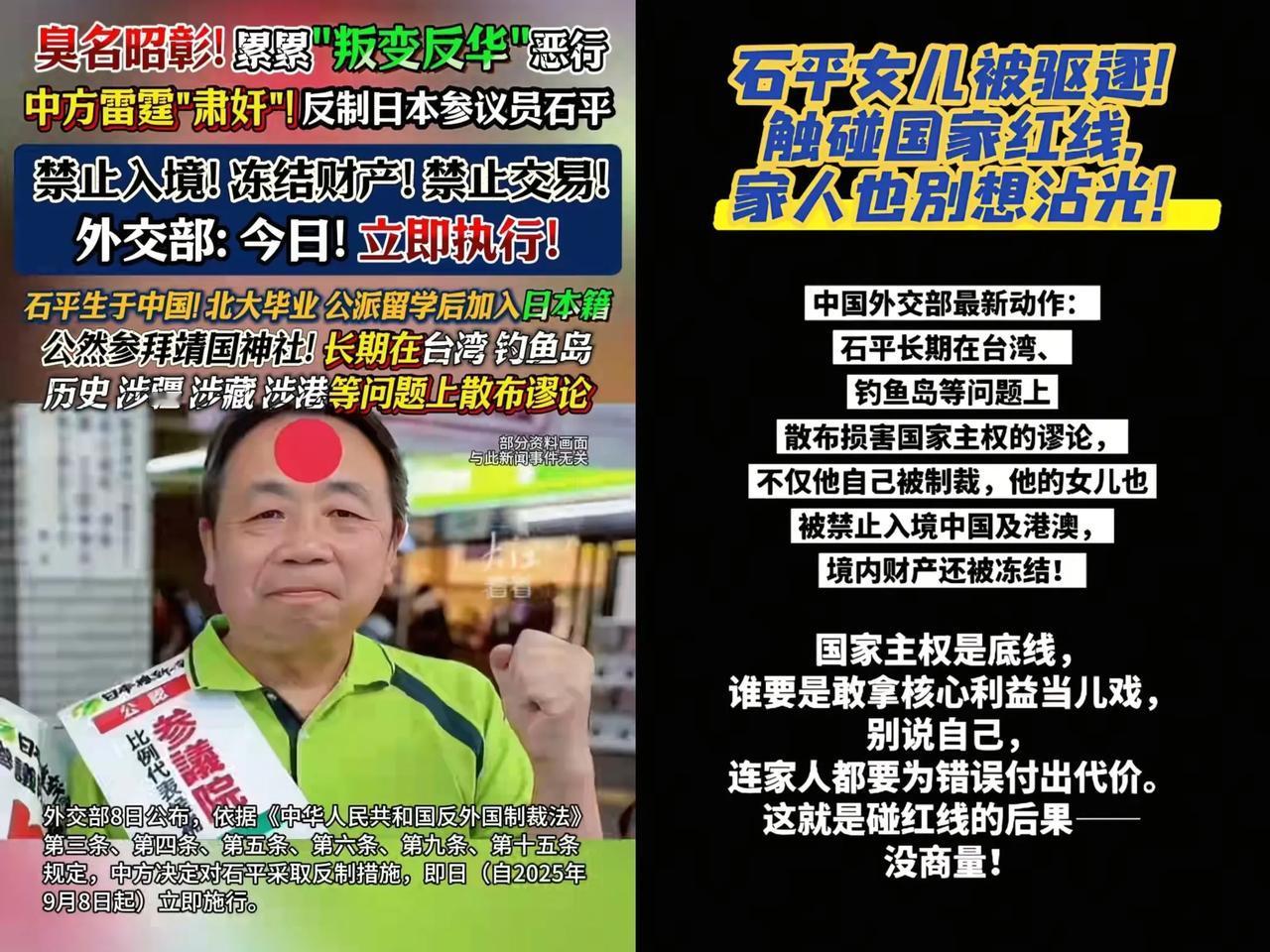清道光六年,陕甘总督杨遇春新得了一个绝色美女。由于连日忙于军务,还没来得及同床共寝,美人居然患了一种奇怪的病。 杨遇春那会儿正忙着对付西北的回部叛乱,军营里的事堆成山,白天勘察地形,晚上跟将领们研究战术,脚不沾地地忙了快半个月。听说美人病了,他才暂时从军务里抽出身,快步赶回总督府。 进了美人住的西跨院,就见丫头们正围着床边唉声叹气。美人躺在绣床上,脸色白得像宣纸,原本顾盼生辉的眼睛闭着,睫毛上还挂着泪珠,呼吸又轻又急。杨遇春皱着眉问:“请大夫来看过了?” 杨遇春可不是一般的总督。他打四川农家子一路拼上来,从乾隆年间跟着福康安平叛,到嘉庆朝平定白莲教,再到道光年间坐镇西北,手里的刀砍翻过多少叛军,身上的伤疤比军功章还多。军中都叫他“杨无敌”,说他眼里只有战局,没有儿女情长。可他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硬汉子也有软肋——去年夫人去世后,身边总缺个知冷知热的人。这次这美人,是甘肃本地乡绅献上来的,说是江南逃难来的,名叫苏婉,不仅貌若天仙,一手琵琶弹得能让黄莺闭嘴。杨遇春见了第一眼,心里就动了,只是军务紧急,才把人安置在府里,没顾上细处。 苏婉呢,年方十六,眉眼间带着江南女子的柔媚,可那双眼睛里总藏着点怯生生的东西。她原是苏州书香门第的小姐,家里遭了水灾才流落西北,被乡绅撞见,当成“奇货”献给了总督。对她来说,杨遇春是权倾一方的大官,更是传闻中杀人如麻的武将,住进这深宅大院,跟关进金笼子里没两样。 丫头们七嘴八舌地回话:“回大人,城里最好的三个大夫都来过了。” “李大夫说像是中了邪,王大夫说脉象乱得很,找不出根由。” “小姐这三天水米没沾,就躺着哭,问她哪不舒服,也说不出来。” 杨遇春走到床边,伸手想探她的额头,指尖刚要碰到,苏婉忽然像受惊的兔子似的抖了一下,睫毛颤得更厉害了。他的手停在半空,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姑娘不是病了,是怕了。 他从军半辈子,见惯了生死,可没跟娇弱女子打过交道。这会儿看着苏婉苍白的脸,忽然想起自己刚从军时,第一次上战场吓得尿了裤子的模样。那会儿他怕的是刀枪,这姑娘怕的,大概是他这个“杨无敌”吧。 “都下去吧。”杨遇春挥挥手,丫头们如蒙大赦,悄没声地退了出去。 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,粗哑的嗓子放轻了些:“我知道你怕。我杨遇春在外面杀人,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好好活着。在这府里,没人敢欺负你。” 苏婉还是没睁眼,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,顺着眼角往下滚,浸湿了枕巾。 杨遇春没再说话,就那么坐着。他想起夫人在世时,总说他是“铁打的石头”,不懂心疼人。那会儿他还犟嘴,说军人哪有功夫儿女情长。可看着眼前这姑娘,他忽然觉得,再硬的石头,也该有块软地方。 过了约莫一个时辰,苏婉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些。她悄悄睁开眼,见杨遇春正盯着帐顶发呆,那背影看着竟有点孤单,不像传闻中那么吓人。她嗫嚅着开口,声音细得像蚊子哼:“大人……我想回家。” 杨遇春猛地回头,眼里闪过一丝诧异,随即沉了沉脸。换了别人敢提这要求,他早发作了,可看着苏婉那双含着泪的眼睛,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,江南对这姑娘来说,是家;对他来说,不过是地图上的一块地方。 “你的家没了,去年那场大水,苏州淹了半城。”杨遇春的声音低了些,“我让人查过你的底细。” 苏婉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,哭得浑身发抖:“那我也不想待在这儿……这里的墙太高了,我怕。” 杨遇春沉默了。他忽然明白这怪病的来头——不是风寒,不是邪祟,是这姑娘的心被关得太苦了。他总以为给她锦衣玉食就是恩宠,却忘了她要的不是金笼子,是能喘气的地方。 那天下午,杨遇春让人把西跨院的角门打开了,允许苏婉在府里随意走动。他还让人去街上买了把新琵琶,送到苏婉房里。自己则回了军营,只是那晚研究战术时,眉头舒展了不少。 过了几天,杨遇春再回府,老远就听见西跨院传来琵琶声。调子有点哀伤,却不像前几天那么绝望。他走进去,见苏婉坐在廊下,抱着琵琶,阳光落在她脸上,气色好了许多。见他进来,她站起身,虽还有点怯,却没再躲。 “大人。”她轻声唤了句。 杨遇春点点头,从怀里掏出个东西递给她——是块玉佩,上面刻着江南的小桥流水。“我让人打听了,你家里还有个表哥在西安做生意,我已经让人去接了。” 苏婉愣住了,捧着玉佩的手微微发抖,眼泪又下来了,这次却带着点暖意。 后来苏婉的病渐渐好了。她没走,也没成杨遇春的妾,就住在西跨院,每天弹弹琵琶,偶尔帮着府里管管账目。杨遇春还是忙军务,只是回府的次数勤了些,有时会站在廊下听她弹会儿琵琶,不说什么,就那么站着。 有人说杨遇春傻,放着绝色美人不动心。他听了只是笑笑。经了这档子事,他才算明白,这世上比军功更重的,是人心。强抢来的服从,不如心甘情愿的停留。 信息来源:基于《清史稿·杨遇春传》及清代西北地方志野史记载综合创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