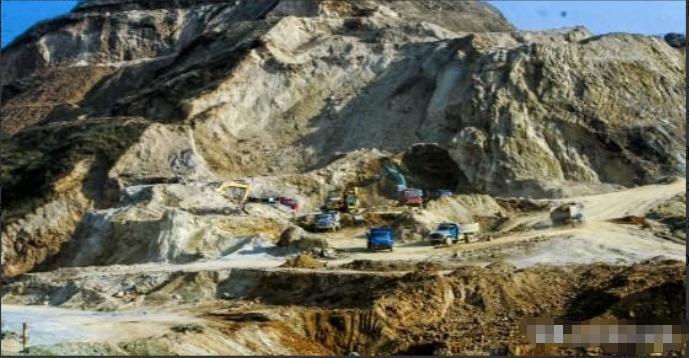2018年,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,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,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,他却突然开口说话,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...... 大卫·古德尔,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生态学家,80岁的时候还出版了厚厚的《世界生态系统》,退休后被大学聘为荣誉教授,没薪水也天天准时上班,坐一趟火车两趟巴士,花一个半小时赶路都不觉得累。 直到102岁,还因为学校不让他去办公室闹过脾气,女儿说他的脑子比年轻人还灵光。 可衰老这事儿,谁都躲不过,后来他眼睛看不清了,腿也走不动了,不能开车,不能打网球,连最喜欢的话剧也演不了,学校怕他出事让他在家待着,他的日子就变成了“等早餐、等午餐、等晚餐”的循环。 这种落差有多难受?就像把一个一辈子忙惯了的人突然关进空房子,活着却没了盼头。 压垮他的是一次摔倒。104岁的老人独自在家,摔在地上喊了两天没人听见,等被发现时身体没大碍,心却凉透了。 他后来在生日会上说“我后悔活到这个年纪”,不是矫情,是真的熬不下去了。他想要的不是苟活,是尊严。 可在2018年的澳大利亚,这事儿根本没选择,当时维多利亚州虽然通过了安乐死法案,但要2019年才生效,而且只给那些预计活不过半年的绝症病人,他身体没大病,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。 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早年倒有过安乐死法律,1996年就生效了,可后来又没了下文,全澳洲当时就没个地方能让他有尊严地离开。 没办法,他只能盯上瑞士,那儿是当时少数允许外籍人士安乐死的地方,只要本人自愿、头脑清醒就行。 为了这趟“死亡之旅”,朋友帮他在网上筹了两万多美金,带着护理人员跨洋飞去瑞士,落地时记者围着问他怕不怕,他笑着说“我来这儿只为一死”,穿的毛衣上还印着“毫无尊严地老去”,字字戳心。 出发前他跟家人道别,说“只对他们有点抱歉”,可孩子们都懂他,纷纷从各国赶过来陪他最后几天,没人拦着,这得多大的理解和勇气啊。 执行安乐死那天,场景挺特别的,他躺在小床上,窗外是绿树,身边围着家人、医生,还有记者,现场放着他选的《欢乐颂》,歌词里唱“欢乐女神圣洁美丽”,谁能想到这是送一个老人离开的曲子。 医生先问了他四个问题:你是谁?生日哪天?为什么来这儿?知道后果吗?他都答得清清楚楚,一点不含糊,然后自己滑动了输液管的开关。所有人都屏着气,孩子们开始掉眼泪,屋里静得只能听见音乐声。 就在大家以为他要平静离开的时候,注射药物30秒后,他突然睁开眼喊了一句:“这也花太长时间了吧!”一屋子人先是愣了,接着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。 我特能理解这种心情,难过是因为老人马上要走了,可这句抱怨里的直白和幽默,又让人觉得他根本没怕过,还是那个犟脾气的老科学家。 没过多久,医生确认他走了,带着他最后的那点“不耐烦”,安安静静地离开了。 有人说他太偏激,长寿多好啊,可这些人根本没站在他的角度想。对大卫来说,活着不是数日子,是要能做事、能交流、能自己做主。 他说从五六年前就没真正快乐过,三次自杀都没成功,那种求死不能的滋味,比死还难受。 他一辈子研究生态,讲究万物平衡,连自己的生命都想做到“善始善终”,这不是消极,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。 这事儿当时闹得挺大,全世界都在讨论安乐死到底是“夺命”还是“给尊严”。 后来澳大利亚不少地方都加快了安乐死立法,2023年新南威尔士州也生效了相关法律,虽然条件还挺严,要绝症、要住满一年、要两个医生审批,但总比以前强了。 要是大卫能多等几年,说不定就能在自己的国家离开,不用折腾那一趟。可他等不起,衰老不等人,对尊严的渴望更等不起。 我一直觉得,生命的质量从来不是用长度衡量的,咱们身边也有不少老人,躺在床上动不了,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,眼神里全是无奈,他们可能不像大卫那样能主动选择,但心里说不定也盼着能有尊严地走。 大卫的勇敢,不光是敢自己选死法,更是敢戳破“长寿就一定幸福”的假象。他最后那句话,笑着吐槽药效慢,其实是在告诉所有人:死亡不可怕,可怕的是活得没尊严、没盼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