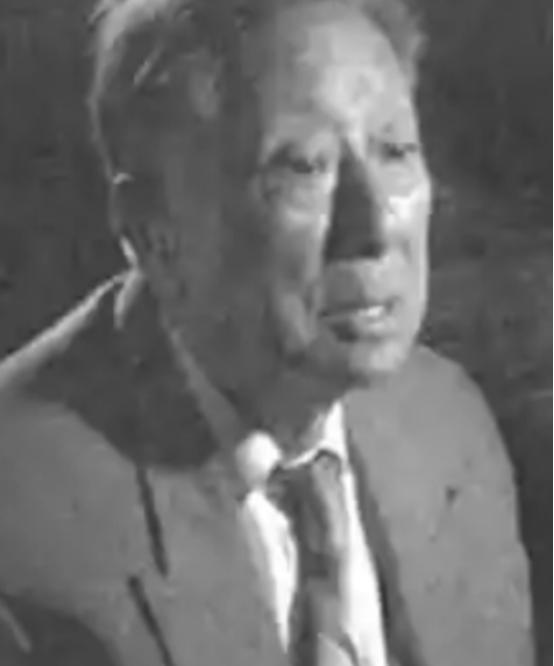一位抗战老兵回忆说:“每次打扫战场的时候,要是发现日寇伤兵,我们都会补刀,不是我们残忍,而是那些伤兵会向我们扔手榴弹,很多战士就是这么牺牲的…” 为什么同为军人,日军伤兵会如此极端,宁愿拉着敌人同归于尽,也不愿被俘虏? 我们很多人看电视剧,以为战场上缴枪不杀是天经地义的。但在那个年代,面对日寇,这套规矩常常行不通。他们中的很多人,从穿上军装那刻起,就不再被当作“人”来对待,而是被彻底异化了。 有两个真实的故事,能帮我们撕开那个时代的伪装,看清老兵话语背后的真相。 第一个故事,关于一个叫苏克己的医生。 1937年,淞沪会战打得最惨烈的时候,苏克己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的副队长。他是个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,为人忠厚,是真正的医者仁心。 8月23日,他们去救护一名被击落的中国空军飞行员。手术刚做完,日军就摸过来了。情况紧急,苏克己他们决定带着重伤的飞行员转移。 他们一行人,有医生,有护士,打着清晰的“中国红十字会”旗帜,背着印有红十字的药箱。这是国际公认的战地中立、应受保护的标志。 路上,他们遇到了三个乔装成农民的日寇。苏克己怕引起误会,还特意用流利的日语说明:“我们是红十字救护队!” 结果呢? 日寇根本没理会。苏克己、助医刘中武、护士谢惠贤和陈秀芳,全部惨遭杀害。苏克己医生本人,被日寇残忍地肢解成了六块。 这起暴行震惊了世界。 朋友们,份后都会被如此虐杀,你还能指望这支军队的士兵,在受伤后会“文明”地投降吗? 他们从根子上就蔑视《日内瓦公约》这类国际准则。在他们眼里,只有征服和毁灭。苏克己医生的遭遇,血淋淋地揭示了老兵所面对的,是怎样一群毫无人性的对手。 如果说苏克己的死,是日寇对外在的残暴;那第二个故事,则揭示了他们内在的扭曲。这个故事,和粟裕将军有关。 1942年,粟裕将军指挥新四军在斜桥伏击战中,缴获了一门日军的“宝贝疙瘩”——九二式步兵炮。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。 丢炮的日军指挥官叫保田兼一,是个中佐。他为了抢回这门炮,几乎疯了。 同年9月,中秋节刚过,保田兼一带着一百多人,气势汹汹地来偷袭新四军第七团,结果一头扎进了粟裕布下的包围圈。 战斗在滥港河上的谢家渡打响。保田兼一腿部受伤,带着残兵退守到几间民房里。粟裕将军指挥部队将其团团围住。 当时天降大雨,粟裕说:“这是及时雨!敌人援兵来不了,这股敌人也别想跑了。” 保田兼一成了瓮中之鳖。接下来,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举动。 他身边还有不少日军伤兵。为了自己能轻装逃命,保田兼一拔出军刀,逼着那些受伤的、还能动的士兵,排队走进熊熊燃烧的烈火中,让他们为“效忠天皇而死”。 你没听错,他是让自己的伤兵活活烧死,以摆脱“累赘”。 而他自己呢?他让没受伤的士兵扶着他,想坐船逃跑。 这是什么样的“武士道”?对同胞的生命冷酷到如此地步!一个指挥官,能亲手把自己的伤兵逼进火堆,那他平时给士兵灌输的是什么思想? 就是“宁可死,不能降,更不能被俘虏”。 在这样的高压和洗脑下,一个日军伤兵,当他躺在地上,面对中国士兵时,他脑子里想的恐怕只有一件事:拉个垫背的,用手榴弹“玉碎”,这样才对得起天皇,才不会像保田那样被长官逼着去死。 老兵的话,我们现在再回头看,就能理解了。 “补刀”,是一个被逼出来的选择。这是在和一群“非正常”的敌人作战。他们不尊重你的仁慈,反而会利用你的仁慈。你试图遵守规则,他们却在利用规则杀你。 但最有力的对比,恰恰也发生在保田兼一战死的后续。 保田兼一最终没能逃掉,在我军的集火下,一颗子弹正中他的前颚,当场毙命。 战斗结束后,粟裕将军做了一个决定。出于人道主义,新四军将保田兼一在内的日寇尸体,归还给了日方。 日寇接到尸体后,还专门给粟裕将军写了感谢信,信里说:“贵军战后归还战骸,宽仁厚德,诚贵军政治之胜利。” 看到这个对比了吗? 一边,是日军指挥官逼着自己的伤兵跳火坑;另一边,是新四军在胜利后,依旧保持人道主义,归还敌军指挥官的尸体。 一边,是日军连红十字医生都不放过;另一边,是我们的老兵在无数次被手榴弹炸伤战友后,才被迫学会了战场上的“残酷”。 所以,老兵回忆中的“补刀”,它所承载的,根本就不是嗜血和残忍。 它承载的,是苏克己医生被肢解时的冤屈;是那些被保田兼一逼入火海的日军伤兵的绝望;更是我们无数战士在伸出援手或靠近时,被拉响的手榴弹夺去生命的惨痛教训。 我们是一个讲“仁”的民族,但侵略者用刺刀和手榴弹,给我们上了最血腥的一课。铭记历史,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一代人的牺牲,到底有多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