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,韩国人非常的愚蠢,他们竟然放弃了汉字,不再使用汉字。汉字是连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一种方式。可是他们却放弃了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,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,感谢您的支持! 美国投资界的老爷子巴菲特在一次闲聊中提起了韩国的文字改革,他皱着眉头说:“韩国人这事儿干得可真不聪明,好端端的汉字怎么说扔就扔了?” 在这位九旬老人看来,汉字就像是东亚文化圈的隐形桥梁,把中国、日本和韩国紧紧连在一起。可偏偏韩国人亲手把这座桥给拆了,这让他实在想不通。 要说韩国人放弃汉字这事儿,还得从七十多年前说起。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,新成立的韩国政府就开始琢磨着要打造独特的民族认同。当时有个叫“语言纯净运动”的风潮席卷全国,政府号召大家把日常用语里的汉字词都替换成纯韩语词汇。 比如说“食堂”要改成“饭屋”,“新闻”要变成“报纸”,连人名地名都要改用韩文来写。这股风潮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愈演愈烈,当时执政的朴正熙政府把这件事当成了重要国策。 到了1970年,韩国教育部突然下发通知,要求全国中小学停止汉字教学。这个决定来得特别突然,就好像一夜之间,孩子们课本上的汉字都消失了。政府给出的理由是:纯韩文的谚文更容易学,能让全民快速扫盲。 这话确实不假,韩文字母确实比汉字简单易学,但问题也随之而来——整整一代人就这样与汉字文化断了联系。 现在的韩国年轻人打开古籍,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场面:《三国史记》读不懂,《高丽史》看不明白,连家谱都认不全。 这些用汉字书写的古籍就像天书一样摆在面前。有个在首尔大学读历史系的女生说过,她为了研究朝鲜王朝的《承政院日记》,不得不像学外语一样从头开始学汉字。她说那感觉特别奇怪,明明是自己祖先留下的文字,却要像破译密码一样费力。 在韩国的古宫景福宫里,游客们常会盯着匾额发呆。那些苍劲有力的汉字题词,很多当地游客已经念不出来了。导游们得特意准备两种讲解——用韩文给年轻人讲,用汉字词给老年人解释。 这种文化断层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,老一辈人写的书信,孙子辈要看不懂了;祠堂里的祖宗牌位,年轻一代也认不全了。 反观隔壁的日本,虽然也经历过文字改革,但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。明治维新那会儿,日本人也讨论过要不要废除汉字,但最后还是决定保留。现在日本人把汉字和平假名、片假名混着用,既保持了文化传承,也没影响现代化进程。 在东京街头,你能看到汉字书写的店招和广告;打开报纸,汉字词随处可见。日本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汉字,中学毕业要掌握两千多个常用汉字。这种传承让日本人能轻松阅读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这些古籍,文化血脉从未中断。 韩国国内对这件事的争论一直没停过。支持恢复汉字教育的人说,这是找回文化根脉的必要之举。反对者则认为,纯韩文教育更符合民族精神。 双方各执一词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2018年韩国教育部曾经想在中小学恢复汉字教育,结果在网上被骂得狗血淋头,最后只好不了了之。 有趣的是,虽然官方不教汉字,但民间学习汉字的热潮却悄然兴起。现在韩国的书店里,汉字学习书总是摆在显眼位置。很多家长偷偷给孩子报汉字补习班,大公司招聘时也悄悄看重应聘者的汉字水平。这种现象很像是在弥补当年的遗憾。 巴菲特的这番话之所以引人深思,是因为他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: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,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需求?韩国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证明,彻底割裂传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文化代价。而日本的例子则说明,守正创新未尝不是更好的选择。 走在首尔街头,你能感受到这种文化割裂带来的微妙影响。年轻人用韩文发短信、上网,老一代人却依然习惯在重要文件上用汉字签名。 医院里,医生开处方时还在用汉字药名,因为同音字太多的韩文容易搞错。法律条文里也保留着大量汉字术语,因为纯韩文表达不够精确。 这种文字上的纠结,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。既要保持民族特色,又要融入国际社会;既要向前发展,又怕丢了根本。这种两难处境,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。 如今,随着中韩交流日益密切,情况又在悄悄变化。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意识到,掌握汉字不仅是为了读懂古籍,更是打开东亚文化宝库的钥匙。 首尔的一些私立学校开始增设汉字课程,不少大学生把汉字能力写在简历的显眼位置。这种自下而上的转变,或许预示着新的转机。 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,更是文化基因的载体。韩国人用半个世纪完成了一场文字实验,这场实验的得失成败,值得每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深思。 在全球化时代,如何既保持文化独特性又不自我封闭,既拥抱现代文明又不割断历史脉络,这是个需要智慧来解答的命题。巴菲特的直言不讳,恰好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的契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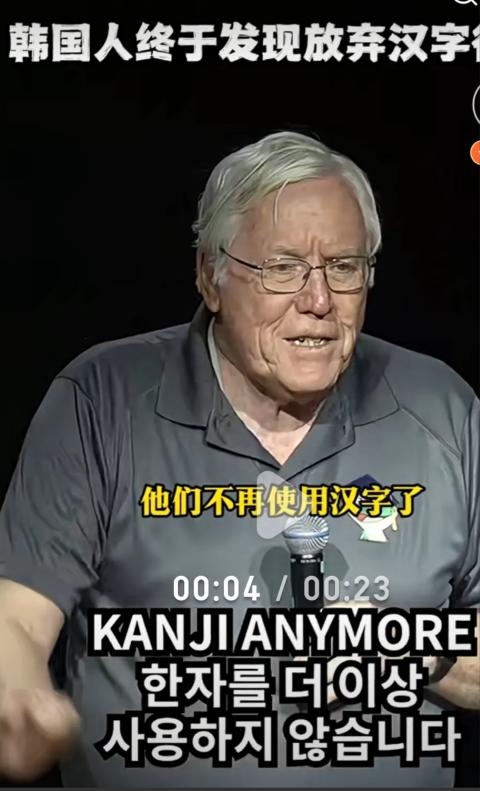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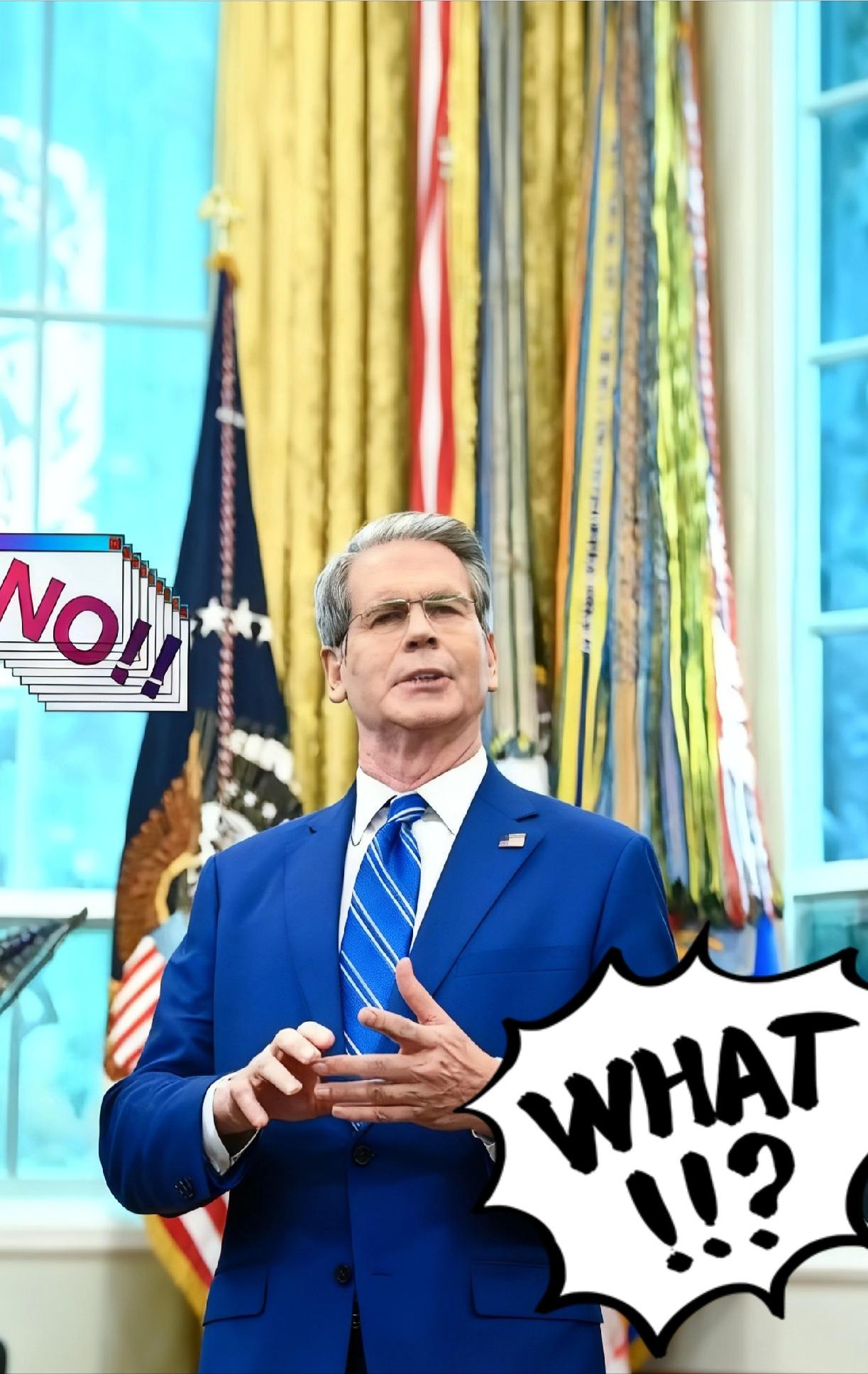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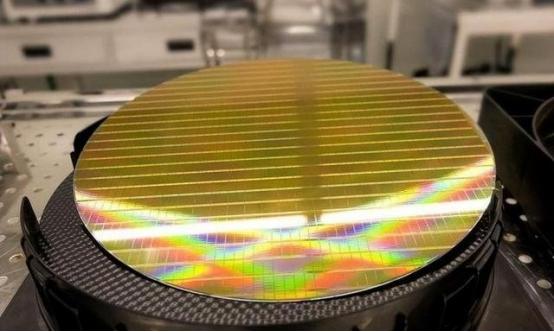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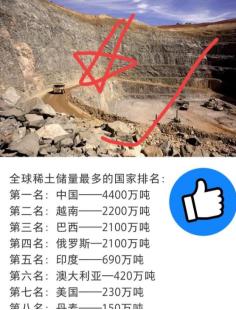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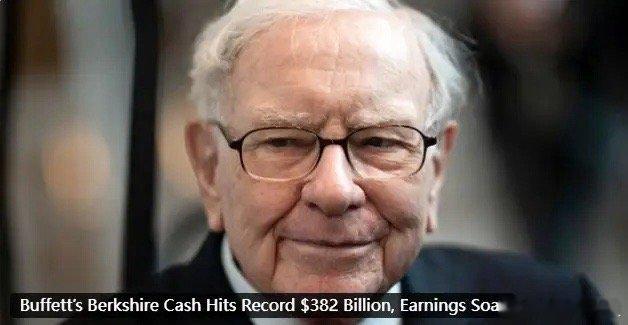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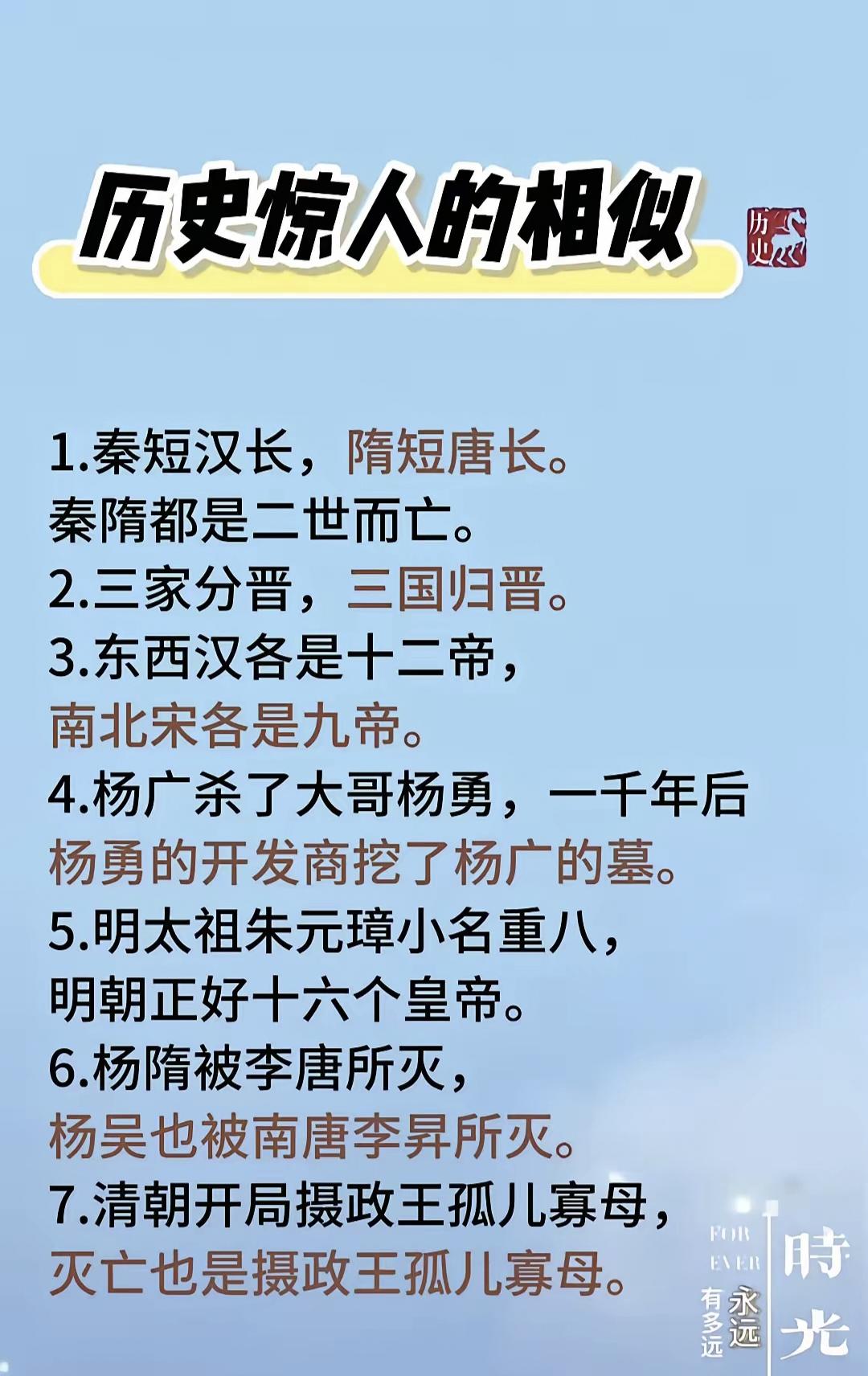

远方的云
人家棒棒不急我们急个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