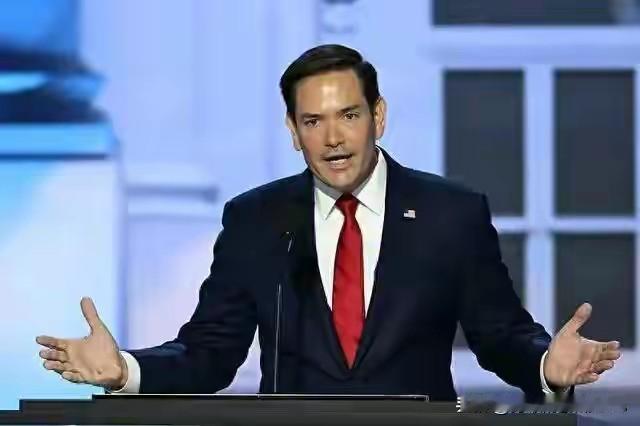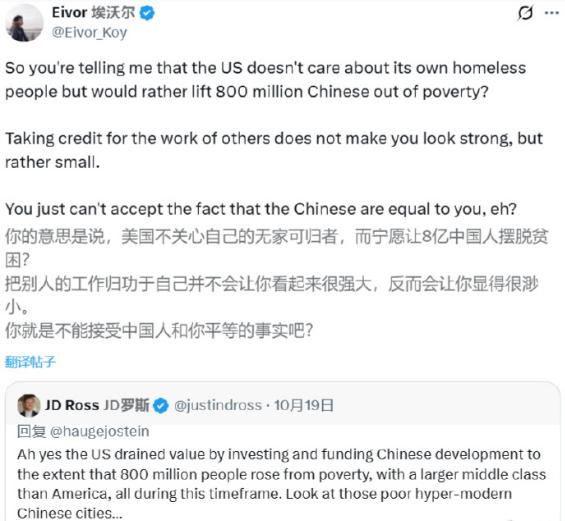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曾感慨万分地表示,美国根本就不是中国的竞争对手,原因很简单,就是中国人可以不以赚钱为目标,而在美国,不赚钱的事是没人干的。 这样的差异,在重大工程的推进中尤为明显。中国的高铁网络从无到有,如今运营里程突破四万五千公里,覆盖九成以上百万人口城市。 早期建设时,许多线路穿越西部山区与偏远地区,运营初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。但这些线路打通了资源运输通道,带动了沿线经济发展,让原本闭塞的乡村接入全国市场。 负责建设的央企从未因短期盈利问题放缓推进节奏,因为项目背后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。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则呈现另一番景象。 东北部的铁路系统已有百年历史,设施老化导致事故频发,改造升级的呼声持续了二十年却进展缓慢。 私人资本测算后发现,改造工程投资回收期超过三十年,且难以保证稳定盈利,始终不愿投入。政府虽多次提出计划,但受制于预算审批与资本游说,资金迟迟无法到位。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宽带网络覆盖上,美国农村地区至今有近两千万人无法使用高速网络,根源仍是私人运营商认为偏远地区投入产出比过低。 中国的这种发展逻辑,在民生与公益领域同样有清晰体现。 英大信托作为央企,近年设立多个慈善信托,投入资金支持北京东城区的智慧养老、公共服务人员帮扶等项目。 这些项目没有直接盈利点,却解决了基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,仅内蒙古化德县的帮扶项目就直接惠及超过一千六百人。 企业还参与乡村振兴,出资修缮重庆罗家村的河堤,解决当地灌溉难题,这些投入都不以短期赚钱为目标,而是践行社会责任。 美国的资本运作则更看重短期回报。 金融领域的资金更多流向能快速获利的投机业务,2024 年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突破七百亿美元,而投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增速连续五年低于百分之三。 医疗领域,创新药研发集中在癌症、罕见病等高价药领域,因为这类药物利润空间大,而普通慢性病的廉价药研发则因盈利有限被长期忽视。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公共服务领域出现明显供给缺口。 两种逻辑的背后,是不同的体制支撑。 中国的国有经济在能源、交通等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,能够按照国家规划投向周期长、风险高但关乎长远发展的领域。 五年规划的连续实施,让产业政策保持稳定,一个战略可以持续推进十年甚至更久。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,保障了非盈利但重要的项目能够落地。 美国的资本则深度影响政策制定。 高昂的选举费用让政客依赖大企业资助,政策倾向不可避免地向资本利益倾斜。游说集团在华盛顿频繁活动,将资本诉求转化为具体政策。 2008 年金融危机时,政府动用公共资金救助金融机构,形成了利润私有化、损失社会化的局面,更凸显了资本在其体系中的主导地位。 鲁比奥的感慨,实则指向两种发展逻辑的碰撞。 中国的家国情怀让发展超越了单纯的盈利考量,更多关注全民福祉与长远利益;美国的资本至上则让发展聚焦短期回报,容易忽视公共需求与长期战略。 这些差异不是竞争中的对立,而是不同路径的选择。中国模式下,资本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,创造了独特的发展优势;美国也在探索资本与公共利益的平衡。 无论是中国高铁穿越群山,还是慈善信托扎根基层,家国情怀驱动的发展都在书写着务实的答卷。 这种不被短期利益左右的坚持,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,民生福祉持续提升,也为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。在不同的发展逻辑中,尊重各自的路径选择,汲取彼此的经验,正是全球发展中珍贵的正能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