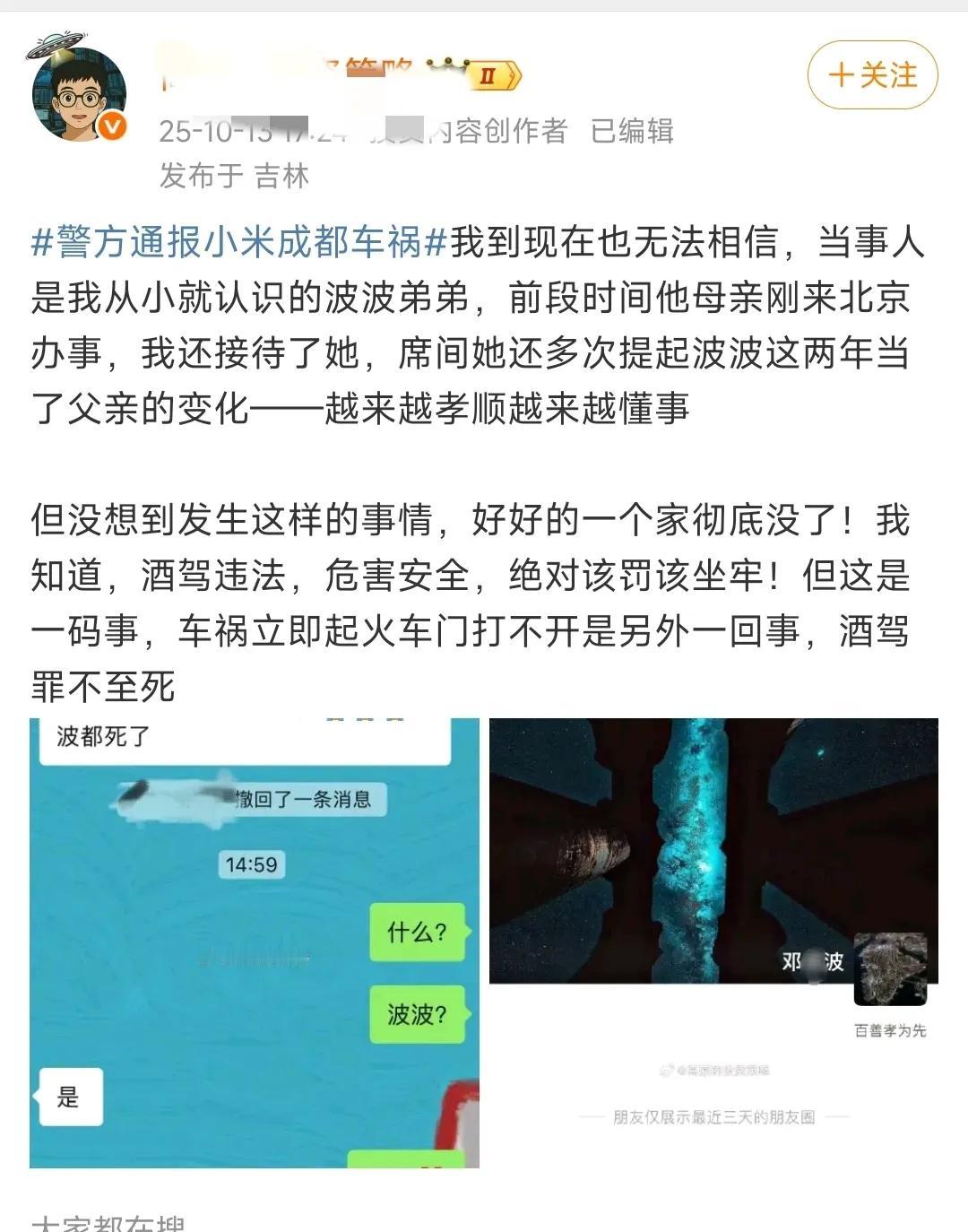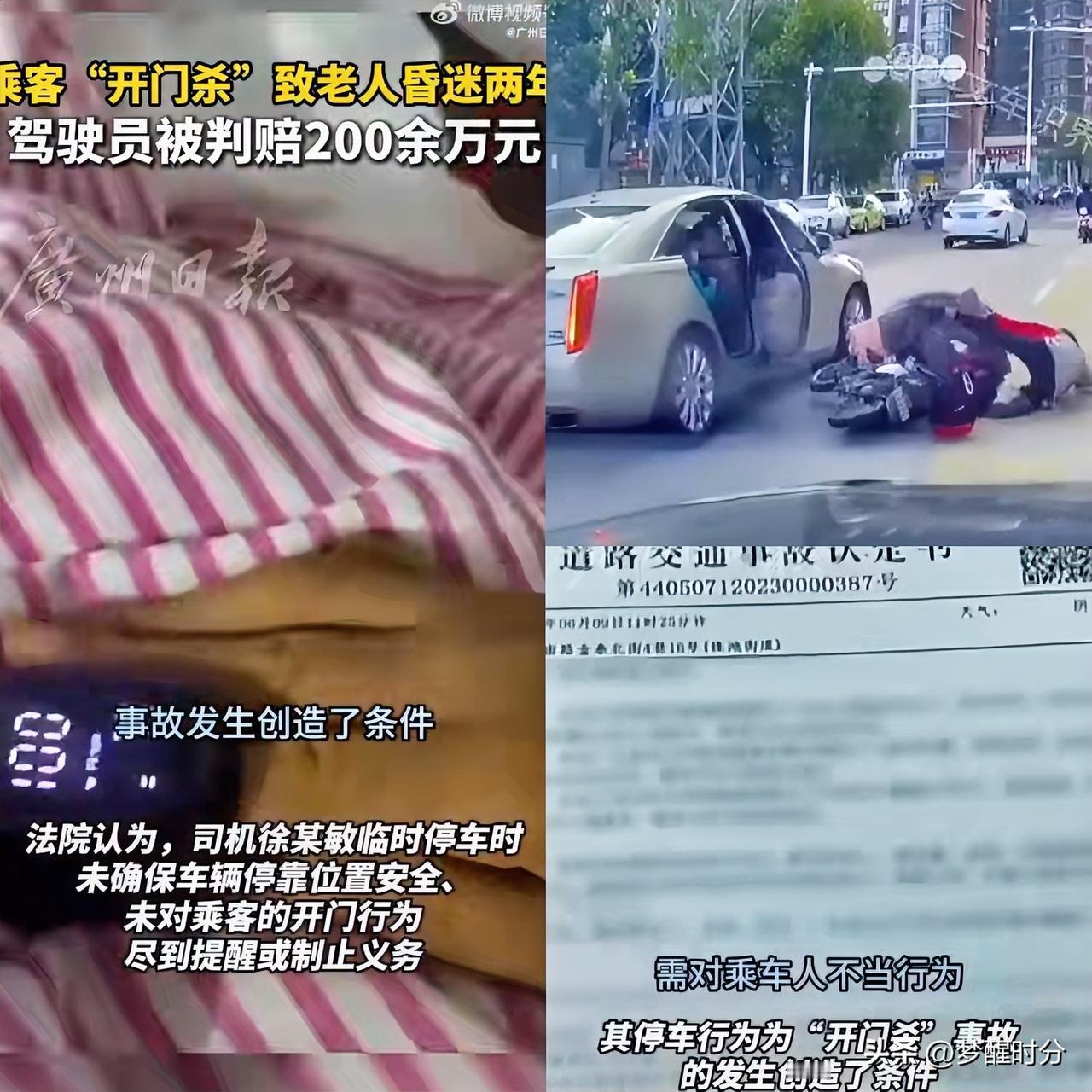江苏南通,一独居老人遭遇车祸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,侄孙为此垫付了医疗费、丧葬费。事后侄孙向保险公司索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时,却吃了闭门羹。保险公司只同意赔偿医疗费与丧葬费,其他一概不认。双方僵持不下,闹上了法院。 今年7月,江苏南通的一起交通事故判决,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侄孙王某,他的叔公王某岗在车祸中不幸离世,王某忙前忙后垫付了所有费用,可最后法院却驳回了他索要死亡赔偿金的请求。 这事儿听起来有点让人意难平,但它却像一把手术刀,精准地切开了法律对“赔偿款”的复杂定义。原来,这笔钱得分两半看,一半是能报销的“账单”,另一半是需要“凭身份领取”的特殊权利。 在司法裁决中,法院对王某预先垫付的医疗费与丧葬费予以全盘支持,体现了法律对公民合理权益的切实维护,彰显了司法公正公平之精神。道理很简单,这些是车祸直接造成的花销,有凭有据。保险公司理应根据责任划分(双方同责),把这个窟窿补上。这就像你帮朋友垫了钱,拿着票据去报销,天经地义。 但案子的真正焦点,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,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法律清清楚楚地规定,这两笔钱不是死者的遗产,不能像存款和房子一样继承。它们是专门用来补偿和安慰特定人群的。 谁是这个“特定人群”?法律给了个标准答案:“近亲属”。死亡赔偿金,是为了弥补近亲属未来可能减少的生活来源;精神抚慰金,则是为了安抚他们失去亲人带来的巨大悲痛。此两笔款项,系直接“发放”给在世近亲属,与逝者无涉。其仅着眼于生者,并不在已离世者的权益范围之内,纯粹关乎生者之权益。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问题:谁才算法律上的“近亲属”?王某的身份是“侄孙”,听着挺亲,但在《民法典》的亲属名录里,翻来覆去也找不到他。法条列得很明白: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孙子女等,就是没有侄孙。 有人可能会说,王某多年来一直照顾叔公,这难道不算“不是亲人胜似亲人”吗?法院也查了,叔公王某岗终身未婚无子女,父母兄弟都已不在,但生前有自己的租地收入,能做饭购物,生活井井有条,并不依赖侄孙的供养。 王某的照顾,更多是出于血缘亲情和道德上的关怀,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善举。但在法律层面,这并未构成一种稳定的、相互依存的“扶养关系”。法律的天平,砝码是严格的权利义务,而非情感的远近亲疏。 这个判决,让很多人觉得法律有点“不近人情”。一个做了所有该做之事的晚辈,最后却没能得到全面的法律支持。然而,这恰恰彰显了法律维系自身庄重威严的特质。法律的严肃性于其而言至关重要,此情形正是这一特性的有力体现。如果随便一个远亲甚至朋友都能主张这两项赔偿,那权利主体就乱了套,潜在的纠纷可能会更多。 这起案件真正刺痛我们的,是它暴露了现行法律在面对社会变化时的局限性。如今独居老人、丁克家庭越来越多,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被打破。很多老人晚年依靠的,可能就是邻居、朋友、或者像王某这样的远亲。 这些心怀善意的照顾者,倾付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,为他人撑起一片温暖。可他们自身的权益,又该凭借何种途径与举措,得以周全保障呢?此乃一处极为显著的法律空白地带。它宛如暗夜中的黑洞,潜藏着诸多不确定性,亟待填补,以免引发更多棘手的法律问题与社会矛盾。 与其事后在法庭上争论情与理,不如在事前用法律智慧做好规划。比如,像王某岗这样的独居老人,完全可以在生前订立一份“意定监护协议”,白纸黑字指定他信任的侄孙王某作为自己的监护人,明确其权利和义务。 如此这般,便为日后权益争取增添了一道坚如磐石的法律保障,使其更具确定性与权威性,能在关键时刻为权益保驾护航。 再比如,社区如果能建立“邻里照护档案”这类记录,也能在关键时刻,为这些非法定亲属的付出提供有力的证据。南通这起案件的判决是现有法律框架下的标准答案,但它也向整个社会抛出了一个沉重的问题:当家庭结构不断变化,我们的法律,该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,多一些温度? 信源:原文登载于现代快报2025年10月15日关于《独居老人发生交通事故去世,侄孙起诉索要死亡赔偿金被驳回》的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