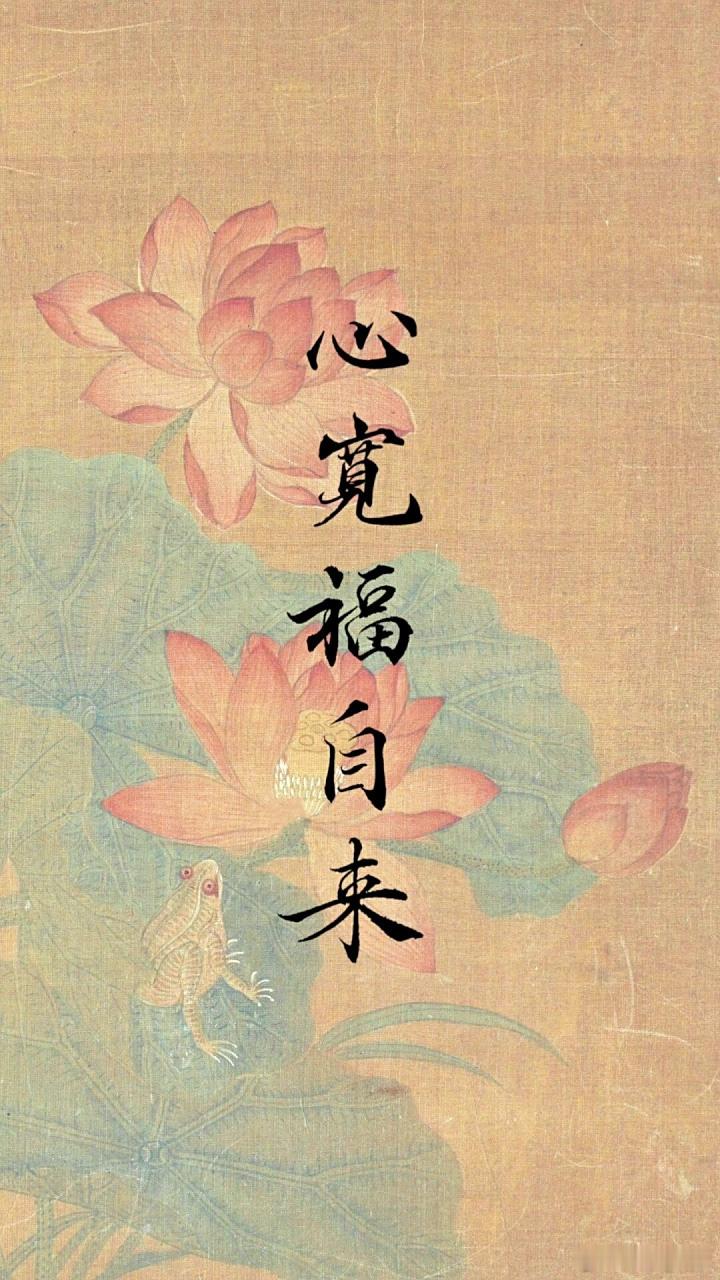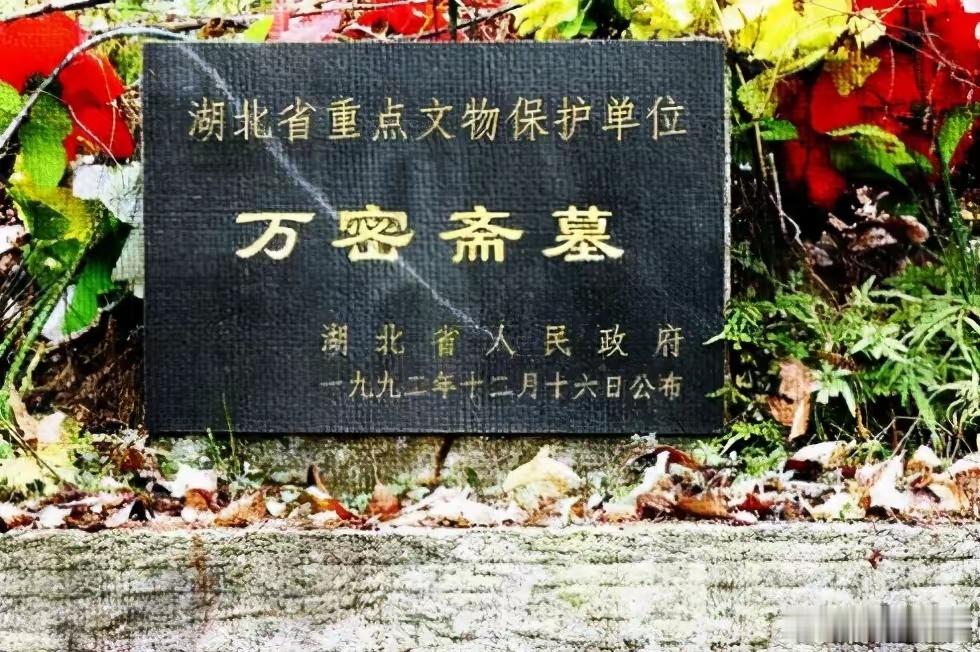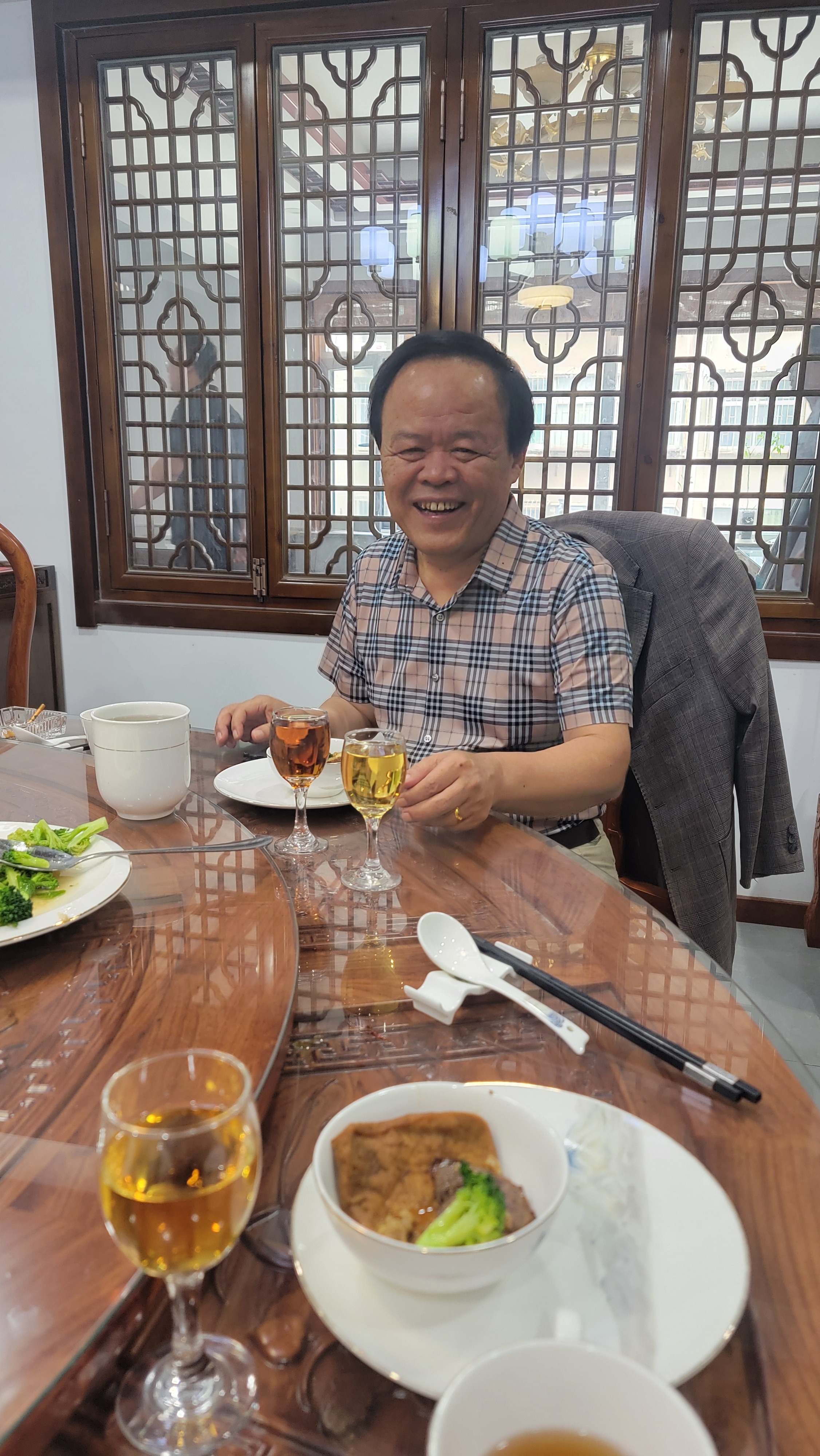张锡纯将消渴分为两大类,一类是肺热津涸,一类是气化不升!
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论“消渴”,不仅用药独到,更以深厚的理化思维阐释中医“气化生津”的原理。他认为,消渴并非单纯的“热伤津液”,而是“元气不升、气化失常”所致。为此,他创立了名方“玉液汤”,主治各种口干多饮、小便频数之证,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糖尿病。
玉液汤的组成颇为精炼:生山药,生黄耆,知母,生鸡内金,葛根,五味子,天花粉。
张锡纯说,这方之所以能止渴,是因为它“升元气而生津液”。其中黄耆为君,主升清阳之气;葛根佐之,助其上达。山药、知母、花粉滋阴润燥,使阴阳交感、气化得以进行;鸡内金健脾化饮,使糖质得化为津;五味子则敛肺固肾,防止津液外泄。诸药合用,气能升、津能生、阴阳交融,渴自可止。
更令人称道的是,张锡纯以物理化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医“气化生水”。
他举例说:若把一壶凉水放在热炉上,壶外很快会凝出水珠滴下;但当壶被加热后,水珠反而不再出现。原因是炉中有火,氢气上升,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生成水蒸气,遇冷凝结为水珠。当壶变热,水珠即刻蒸发,不再显现。
人体亦然——若腹中气化旺盛,清阳上升,其中挟带“氢气”,与肺吸入的“氧气”相合,便能在肺中化生津液,润泽全身。若肺体过热,就像热壶,津液即刻蒸干;若气化不升,则氢气不上,津液无由生成,人便口渴难止。
因此,张锡纯将消渴分为两大类:一类是“肺热津涸”,应清肺润燥;另一类是“气化不升”,应升补元气。
若心火过旺、灼伤肺津,还须清心泻火,使心肺相安。他认为后者在临床更常见——病者并非真热,而是中气衰微、气化无力。这正是玉液汤的施治之本:通过升清阳、助气化,使津液自然生。张锡纯的比喻既形象又科学,把古人“气化生津”的概念,用近代化学语言讲得通透明白。
他还特别指出,气化的发生离不开“真火”。
若脾胃湿寒、阳气衰微,就像炉心无火,纵有壶水,也无法化气成珠。这种情况若不温阳扶气,再多滋阴清热之药都无济于事。所以他强调,消渴之证,虽多阴虚,但常夹寒湿与阳虚,治时须“辨寒热虚实”,不可一味清凉。
正因如此,他又提及《金匮》中的“八味肾气丸”之所以加桂、附者,正为温补真阳,使气化得行;后世治消渴亦有加干姜、白术以健脾暖中者,其理皆同。
张锡纯治病极重脉象与气机之辨。他记载一位少年,咽喉干渴不解,饮水无数仍不止渴。诊其脉微弱迟濡,显为中气下陷、脾阳不足。于是用“四君子汤”加干姜、桂枝尖,一剂而渴止。若依常法用清热润肺之药,反易伤阳,使渴更甚。由此他总结,临证不辨虚实寒热,最易误入“以热治虚”的陷阱。
此外,他也提醒,若消渴因湿热郁阻中焦所致——如口苦、胸闷、舌苔黄腻、尿黄短赤——则应以清化湿热为先,可选“苍柏二妙散”或“越鞠丸”等方酌加化湿理气之药。
可见,张锡纯并非拘泥一方,而是根据气机升降与寒热虚实灵活施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