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10月,福州台江那座爬满岁月痕迹的老宅里,99岁的高秀美在睡梦中安详离去。孩子们在她枕头边发现了那个伴随她半生的木盒子——里面装着聂曦的军装照、当年没缝完的半只袜子,还有一张她亲笔写的纸条,只有短短一句:“我去找聂曦了,家里的事,你们好好守着。” 没人知道,这个到最后都笑着说“这辈子值了”的老太太,曾把多少眼泪砸进了灶台的柴火里,又把多少苦难揉进了针线的纹路里。 高秀美刚嫁聂曦那几年,日子是真的有盼头。聂曦是福州本地人,比她大几岁,读过师范,后来投笔从戎跟着吴石将军做事,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当副官。再忙也总记着家里,每次回家要么揣块花色布料,要么拎袋刚出锅的福州鱼丸,总念叨“你带着孩子辛苦,得补补”。1949年前后,聂曦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有时半夜蹑手蹑脚进门,身上带着淡淡的油墨味,只含糊说句“在忙公务”。高秀美从不多问,只是默默把他皱巴巴的军装熨烫得平平整整,她哪能想到,丈夫口中的“公务”,是冒着生命危险给解放军传递军情,更想不到这“公务”会让他永远留在了海峡对岸。 1950年6月,聂曦和吴石、陈宝仓、朱枫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,消息过了大半年才偷偷传到福州。那天邻居攥着张模糊的报纸剪片,凑到她跟前小声说“聂副官怕是没了”。当时她怀里抱着刚满两岁的小儿子,手里还攥着给聂曦缝到一半的袜子,听完没哭,只是慢慢把袜子叠好塞进抽屉,转身进厨房生火做饭。锅里的水开了,蒸汽模糊了她的脸,她照样给老人盛饭、给孩子喂粥,脸上连一丝波澜都没有。直到深夜孩子们睡熟,她才蹲在灶台边,对着聂曦常年用的那只空碗,眼泪一滴滴砸在冰冷的柴火上,连抽气声都不敢大一点——她太清楚“敌特遗属”这四个字有多沉,哭出声,可能连这个家都保不住。 从那以后,高秀美就在老宅门口摆了个针线摊,缝补衣服、纳鞋底,一分钱一分钱地攒着养家用。有人故意刁难,把破得没法补的衣服扔到她面前,阴阳怪气说“敌特的老婆,这点活都干不好?”她不还嘴,捡起来抱回家,熬夜用自己攒的新布剪出补丁补上,第二天准时送回去,分文不多要。福州的冬天湿冷,她的手冻得又红又肿,针都捏不住,就凑到嘴边哈口热气接着缝;夏天太阳毒,她撑着把破伞坐在路边,中暑了就灌口凉水,缓过来继续低头干活。 媒人踏破了门槛,说的人家有工厂工人、有机关干部,都劝她“找个人搭伙过,能轻松点”,她每次都摇头:“我男人还在等着我呢,孩子们跟着别人,哪能不受委屈?”后来聂曦哥哥家穷得养不起孩子,她又主动把侄子接来家里,有人说她“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,还添张嘴”,她只是笑笑:“这是聂家的根,我得守住。” 每天晚上,她都会给两个孩子讲聂曦的事,从不说“你爸是特务”,只反复说“你爸是个好人,在外面做正事,以后你们也要做正直的人”。孩子上学时,有人在背后议论“那是敌特的孩子”,她就每天提前半小时送孩子去学校,拉着老师的手深深鞠躬:“孩子没错,求您多照看照看。”腰弯下去的那一刻,她把所有的委屈都压进了心里。 就这么熬了几十年,直到上世纪80年代,吴石案终于平反,聂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那天政府工作人员上门送烈士证明时,高秀美已经快70岁了。她接过那张盖着红章的纸,手止不住地抖,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,然后慢慢走进里屋,从衣柜最底层拖出那个木盒子——里面除了聂曦的照片和半只袜子,还有她攒了几十年的粮票,每一张都叠得整整齐齐,像是在等着主人回来用。她把证明轻轻放进盒子,扣上盖子时轻声说:“谢谢你们,他终于能回家了。” 之后的日子,她还住在那座老宅里,院子里聂曦当年亲手种的榕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。每天早上她会扫扫院子,给榕树浇点水;下午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缝缝补补,偶尔跟邻居聊聊天,从不提过去的苦。有人问她这辈子值不值,她总是笑着说:“守着他的念想,看着孩子们好好的,咋不值?” 高秀美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,却在历史的风浪里,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、一颗从未动摇的心,守住了丈夫的清白,守住了聂家的血脉,更守住了普通人最珍贵的情义。比起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英雄,她的故事或许不够轰轰烈烈,却藏着最动人的力量——那是在苦难里不低头、在等待里不放弃的坚守,是一个女人用一辈子写就的“情”字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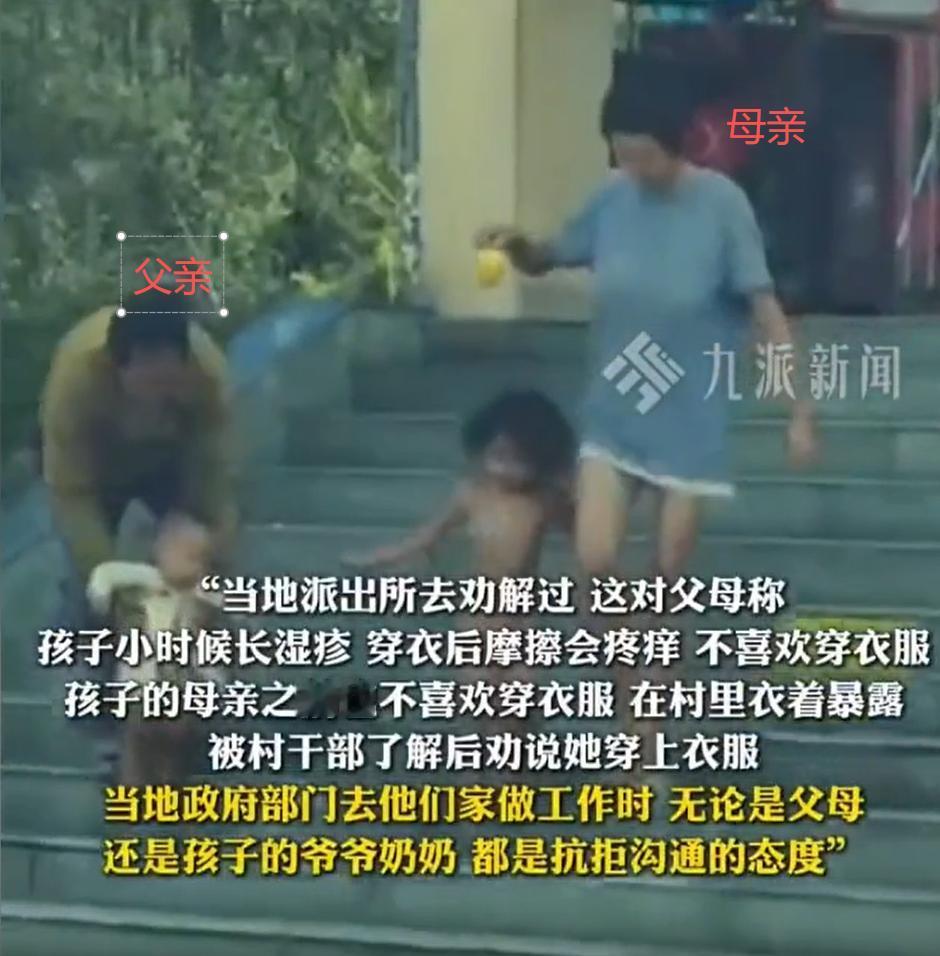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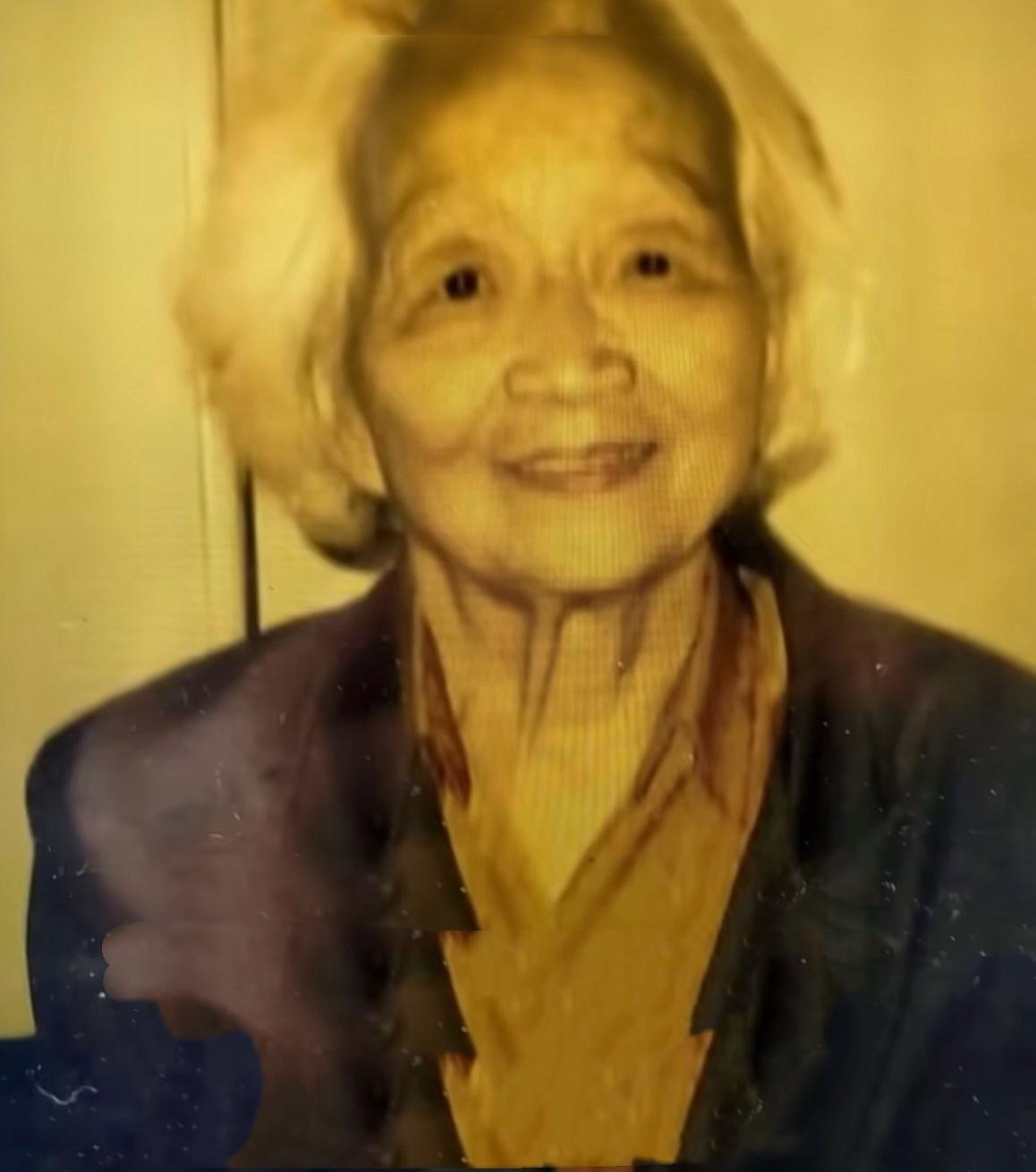

用户75xxx73
人如其名[点赞]
过程
[点赞][点赞][点赞]
放飞的码头
致敬,烈属[作揖][作揖][作揖][玫瑰][玫瑰][玫瑰]
用户10xxx44
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是敌特家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