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,曾国藩胞弟的曾孙女曾昭燏,登上了南京灵谷寺,随即纵身跃下。事后,人们在她的大衣口袋中翻出了一张字条,上面留有短短8个字,却让人潸然泪下。 “我的死,与司机无关。” 就这么一句话,平淡得像是在交代一件日常琐事,却像一枚针,精准地刺入人心最柔软的地方,让人潸然泪下。这位女性,就是曾昭燏。 她在南京中央大学,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恩师,国学大师胡小石。胡先生的藏书楼,成了她的第二个家。跟着老师,她一头扎进了金石、古籍的海洋里。也就是在这里,她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,考古。 1935年,她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:放弃在读的研究生学业,自费去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。 在伦敦的博物馆里,曾昭燏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成千上万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。那一刻,她的心被深深刺痛了。她暗下决心,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,建立我们自己的博物馆事业,再不让国宝流离失所。 仅仅一年,她就以一篇《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》的优秀论文拿到了硕士学位。毕业后,她又前往德国国家博物馆实习。可就在这时,国内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。 毕业典礼那天,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去庆祝,她却一个人默默地待在实验室。她说:“祖国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战,我何必花时间参加这种只为个人荣誉的典礼。” 家里的信来了,劝她时局动荡,暂时不要回国。但一顿午饭,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。那天,她和一位德国教授用餐,教授聊起早年去北京十三陵的经历。当时路况很差,同行的美国人抱怨说:“这路是什么年代修的?”旁边的中国向导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大概两三千年前吧。”那个美国人瞬间沉默了。 外国人尚且对中国一条破旧的古道心怀敬畏,身在异乡的自己,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国土被践踏,文明遭劫掠?1938年,她毅然回国。 回国后的曾昭燏,立刻投身到战火中的文物保护工作。她加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,在昆明、在李庄,那些艰苦的岁月里,她和同事们一起,整理、发掘、保护着中华文脉的火种。 她对文物的爱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因为战火蔓延,一批刚出土的文物无法带走,只能就地掩埋。她亲手在石板上刻下字,恳求后来的发现者:“后人有掘出者,幸加珍重护持……庶不负先民创作之艰难,而瘗者保护古物之苦心云耳。” 1948年底,国民政府准备将大批顶级国宝文物运往台湾。当时,很多人选择跟随前往,但曾昭燏拍案而起,她四处奔走,大声疾呼:“运出文物,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,则主持此事者,永为民族罪人!” 新中国成立后,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,与北京的夏鼐并称为“南曾北夏”,那是中国考古界的黄金时代。她对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,从展陈设计到文物说明,事无巨细,亲力亲为。 她在院里立下规矩:搞文物工作的,绝不允许私人收藏古董。为了以身作则,她把自己家传的一套清代瓷茶具都捐给了国家。 她的个人生活,却简单到了极致。有一次,一位来访的苏联专家好心问她,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她只是笑着回答:“我已经嫁给博物馆很多年了!” 她把所有的爱,都给了那些不会说话的瓶瓶罐罐,给了那份她视为生命的事业。她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,还受到了主席的接见。那时的她,无疑是站在事业的顶峰。 然而,命运的吊诡之处就在于,它给了你耀眼的光环,也可能给你带来沉重的枷锁。 “曾国藩后人”这个身份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成了一份无法摆脱的“原罪”。她不得不一次次地写检讨,做汇报,在大会上剖析自己的“封建家庭烙印”。这些无休止的内耗,像砂纸一样,慢慢磨损着她的精神和热情。 真正的打击,接踵而至。1957年开始,她身边的人一个个出事了。她最敬重的二哥曾昭抡被打成“右派”,妹妹精神失常,侄子被开除公职……亲人的遭遇,像一座座大山压在她心头,让她喘不过气。 最后一根稻草,是恩师胡小石的离世。恩师的倒下,让她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无力与脆弱,也彻底击垮了她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 1964年12月22日,刚从疗养院出来的她,对司机说想去灵谷寺走走。她把车停在山下,将一大袋苹果递给司机,平静地说了声“我上去散散心”。 谁也没想到,这竟是诀别。 当人们找到她时,只在她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那张字条:“我的死,与司机无关。”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,没有宏大的遗言,没有对时代的控诉,只有一个学者、一个善良的人,对一个普通劳动者最纯粹的体谅和保护。她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离去,给一个无辜的人带去任何麻烦。这份临终前的悲悯,比任何史书上的宏大叙事,都更具穿透人心的力量。 好友陈寅恪听闻噩耗,悲痛地写下:“高才短命人谁惜,白璧青蝇事可嗟。”是啊,如此才华,如此品格,却落得如此结局,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。




![把溥仪成功改造了,比杀强太多了[6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313084385197706283.jpg?id=0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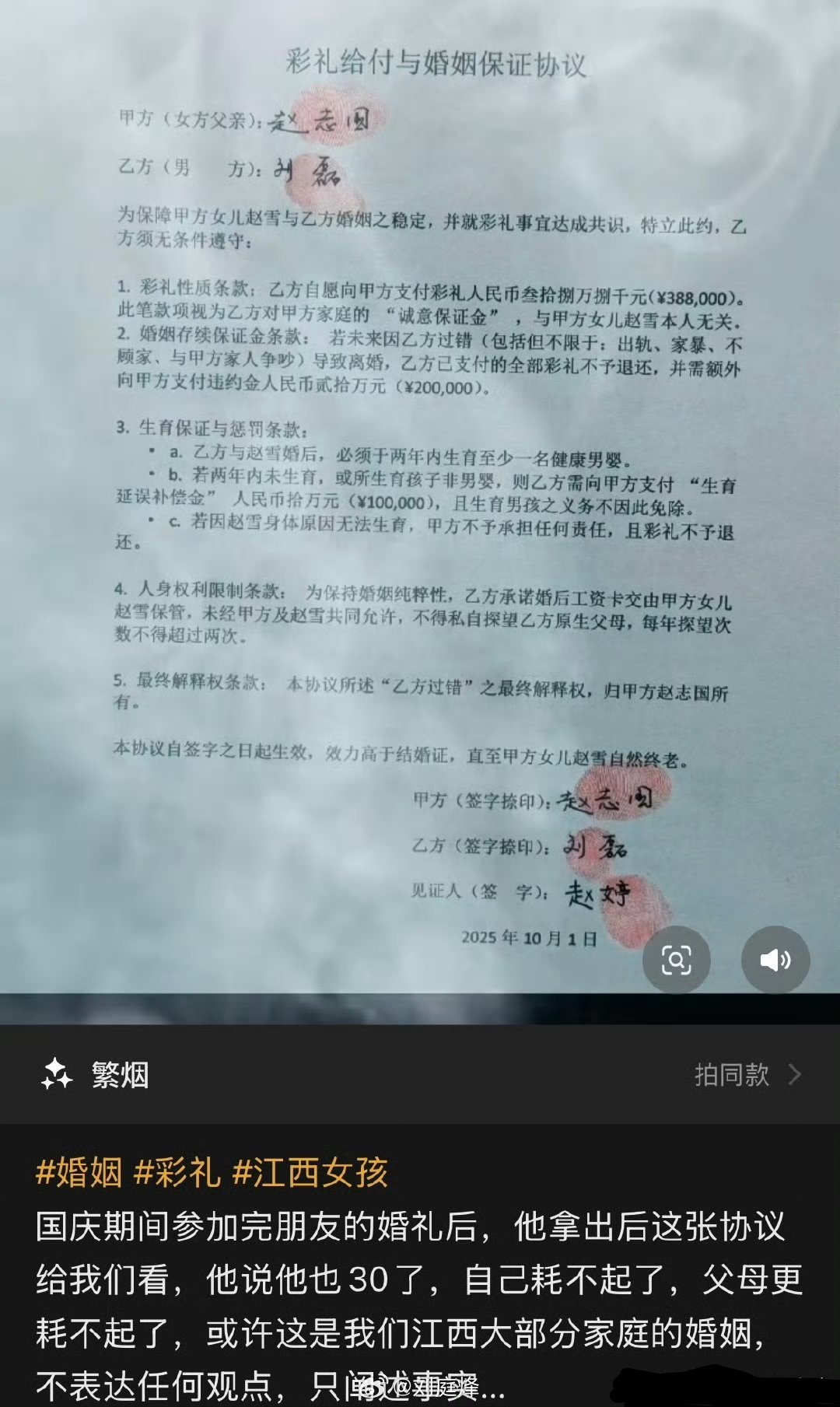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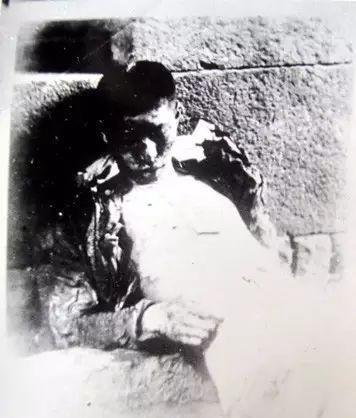

小沉℡
有良知的人[作揖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