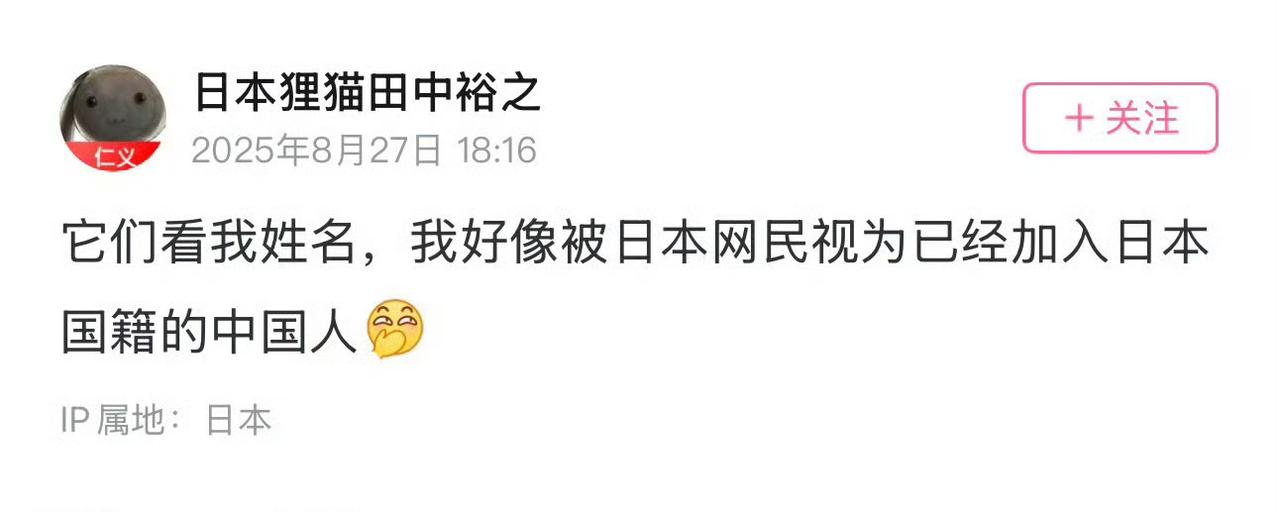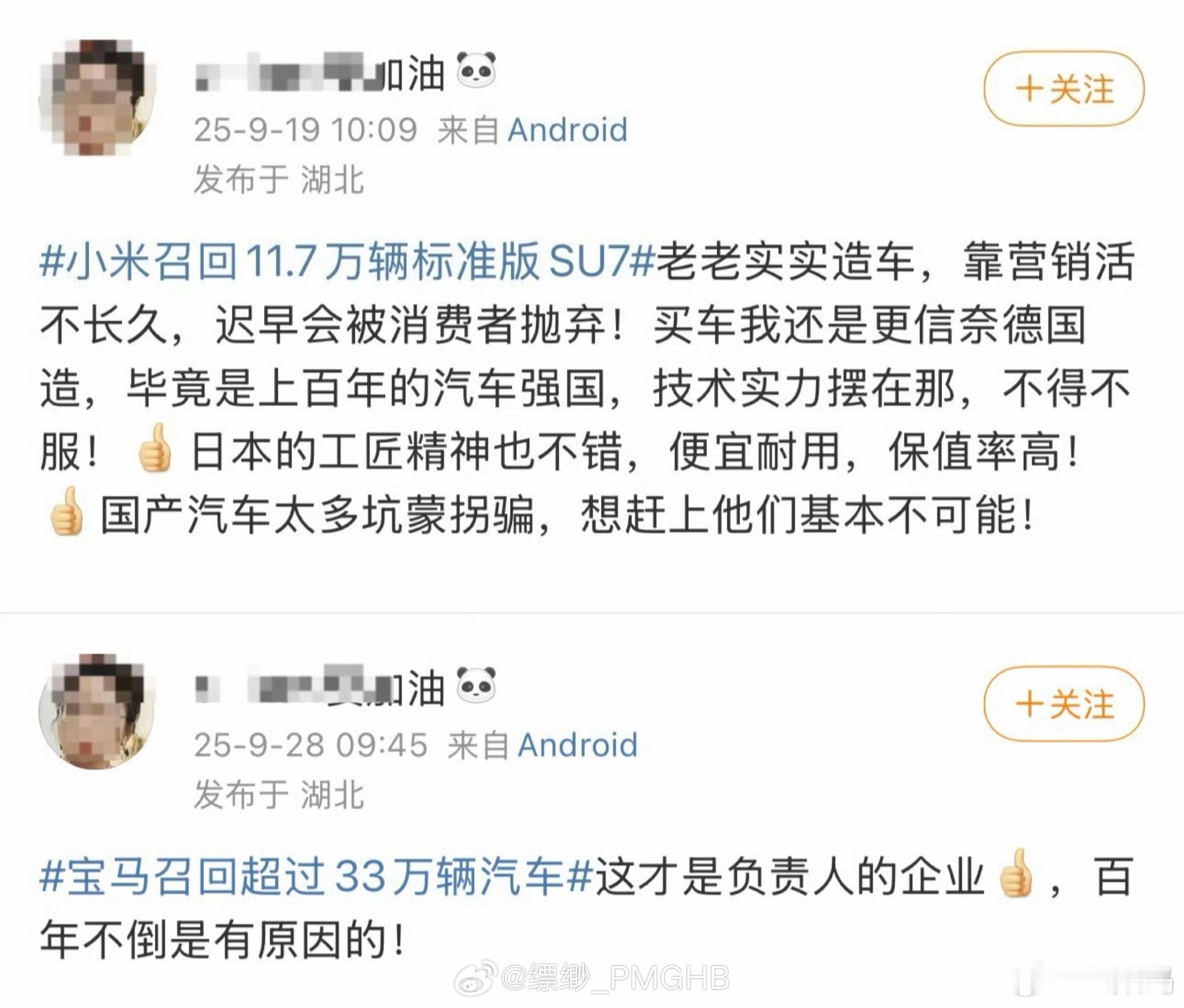1637年,法国一名叫费马的律师提出了一个数学猜想,然后在空白处写道:“我有一种完美的证法,因空白太小,写不下!”可直到350年后,牛津大学的教授安德鲁才完成该猜想的验证。 猜想不过一行字,解开却要三百年。这不是阴谋论,也不是史诗电影,而是真实发生在数学史上的“浪漫悬案”。 一个律师随手写下的“我写不下”,彻底把几代顶级天才逼疯,有人为它差点自杀,有人为它孤独七年,最后的胜利者甚至是在阁楼里偷偷搞研究,像在拍《谍影重重》。 这不只是一道数学题,更像是人类理性和执念的一次较量。 如果你以为改变世界的,只有总统令、科技革命或一场战争,那你可能低估了一个法国律师的“手欠”。 1637年,皮埃尔·德·费马在一本拉丁文的数学书边上,潇洒地写下这么一行字:“我有一个完美的证明,但这个空白太小,写不下。” 他不是数学家,不是贵族,也不是教授,就是个搞法律的业余数学爱好者,请注意,他不是没写出来,而是说“这里写不下”,这就像一个人告诉你他会飞,但因为屋顶太低,就先不表演了。 就这句话,成了数学圈的“悬案之王”,就像有人在公共厕所门上刻了一句谜语,结果全世界的博士都开始试图解锁它。 问题本身其实不难懂:当 n>2 的时候,xⁿ + yⁿ = zⁿ 有没有整数解?看起来像小学生练习题,结果成了数学界的“鬼打墙”。 而这道题最诡异的地方是:它既不涉及核能,也不解决气候问题,甚至连个鸡蛋价格都影响不了,但它却像一只蚊子,在最安静的夜里嗡嗡作响,让所有人都睡不着。 有人说,费马大定理不是数学问题,是耐心问题,从18世纪开始,就有无数数学家前仆后继。 有一批人像拼图玩家,一点点在n=3、n=5上找突破口,欧拉、勒让德、狄利克雷都贡献过一块拼图,但离全图还差十万八千里。 德国数学家库默尔差点破解了,但他发现工具箱里缺了一把关键的“扳手”,于是他干脆自己制造了一套新工具,代数数论里的“理想数”概念,但他还是没能拆开这道“锁”。 到20世纪早期,这道题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阴影,德国富豪沃尔夫斯凯尔失恋后准备自杀,结果研究费马研究上头,连死都忘了,最后决定把钱拿出来设立奖励。 这事听起来像段子,但是真的发生过,最神奇的是,破局的钥匙,居然藏在完全不同的领域。 上世纪50年代,两个日本数学家谷山丰和志村五郎提出一个看似离谱的猜想:椭圆曲线和模形式之间,其实是“同一个东西”的两种语言。 这句话的意思,大概就像说猫和WiFi其实是一个系统的两个侧面,听起来玄乎,但不完全没道理,这个猜想当时没人搭理,谷山丰最终在31岁时自杀,志村则一人默默推进。 直到1986年,德国数学家弗雷忽然冒出一个想法:如果费马大定理错了,那就能“生出”一种不可能存在的椭圆曲线。 这就像说,如果地球是方的,那就能造出一辆能穿越时间的自行车,你当然不信,但逻辑上讲得通。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主角,可能是历史上最文艺的数学家,安德鲁·怀尔斯,英国人,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。 他几乎完全退出学术圈,整整七年,躲在家里阁楼,用最原始的方式,纸和笔,一点点推演。 每天早上泡一杯茶,穿上毛衣,爬上阁楼,写公式写到太阳下山,他说自己就像在黑屋子里摸索,偶尔摸到一把椅子,直到某一天终于找到了灯的开关。 1994年9月19日,他写下最后一步,合上笔盖,独自坐在屋里哭了20分钟,这一次,没有漏洞了,130页的证明,最终发表,这场跨越358年的马拉松,终于落下帷幕。 这不是一道题,这是人类的执念,很多人不理解:这有什么用?搞这个定理,能造火箭吗?能治癌症吗? 答案是:不能,但它能证明一件事,人类的好奇心和执念,有多强大,因为这个定理,数学家们不得不发明全新的工具,比如椭圆曲线、模形式、伽罗瓦理论,甚至意外推动了密码学的发展。 一个律师的涂鸦,一句“写不下”,成了整个数学世界的引擎,怀尔斯的七年孤独、谷山的遗愿、沃尔夫斯凯尔的悬赏、库默尔的失误…… 每一个失败和尝试,都像是接力棒,一代代传下去,有人说,费马当年可能根本没有那个“完美的证明”,他大概只是证明了n=3和n=4的情形,然后以为都能用这个办法搞定。 但这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那句“写不下”,就像一根火柴,点燃了几百年的热情。 人类最伟大的能力,不是发明飞机、互联网或AI,而是对一个“无解”的问题,穷尽一生去寻找答案。 哪怕它只是一句,“写不下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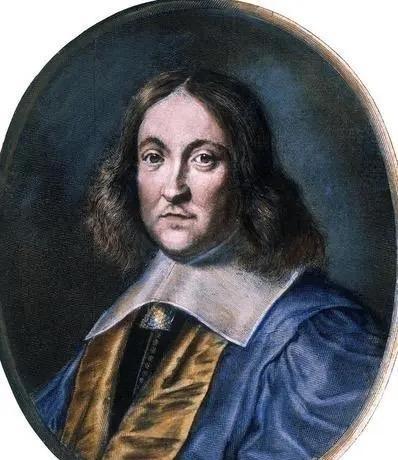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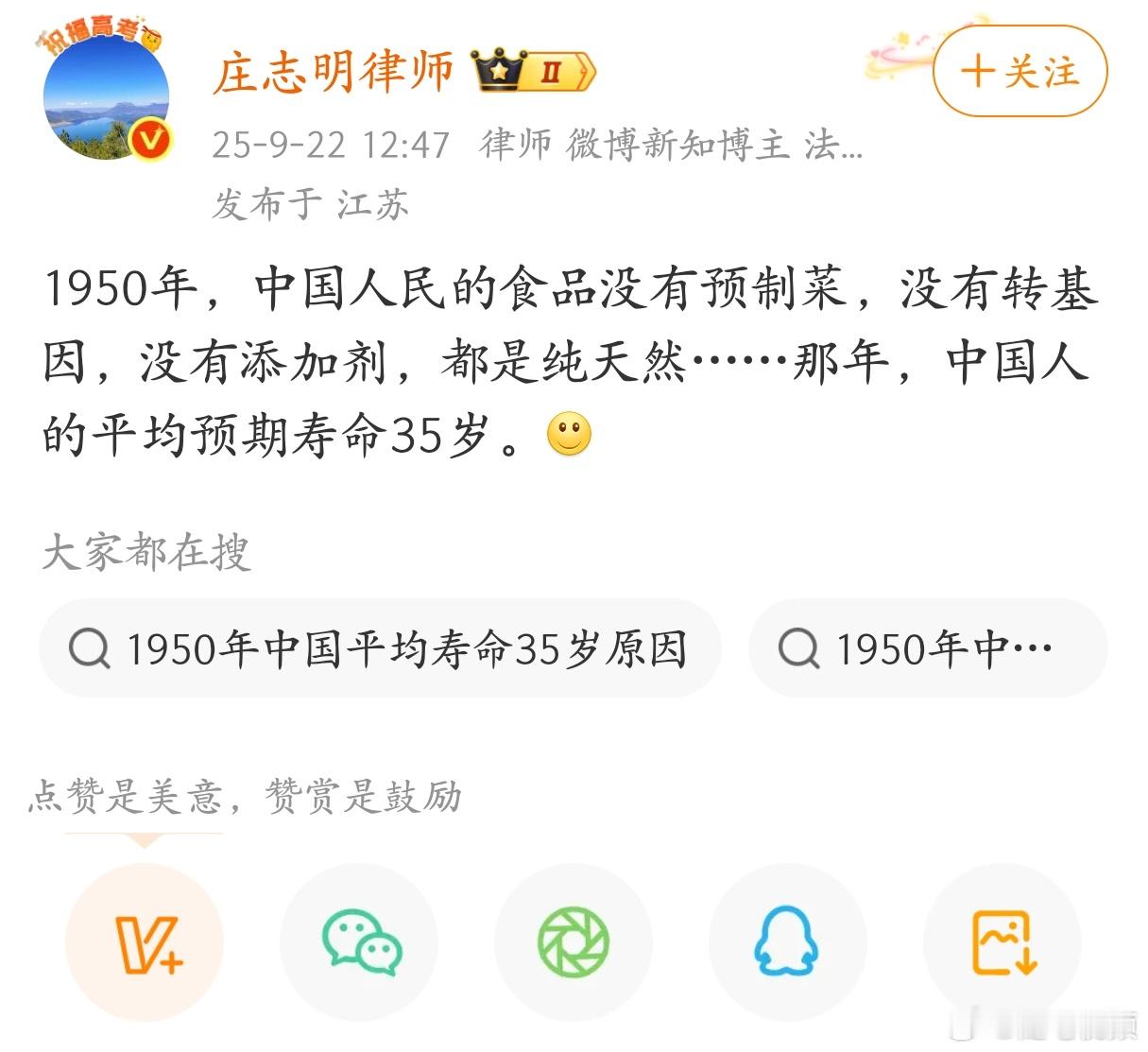

![《移不动,信不过,联不通》我还以为就我的苹果是这样呢[吐舌头眯眼睛笑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4835984402598136439.jpg?id=0)
![一开始还没完全看懂,把眼睛眯起来就看懂了[笑着哭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6946156965148236767.jpg?id=0)
![就等这天呢,立了规矩,结果轮到自己就不认了[吃瓜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9667063374717142495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