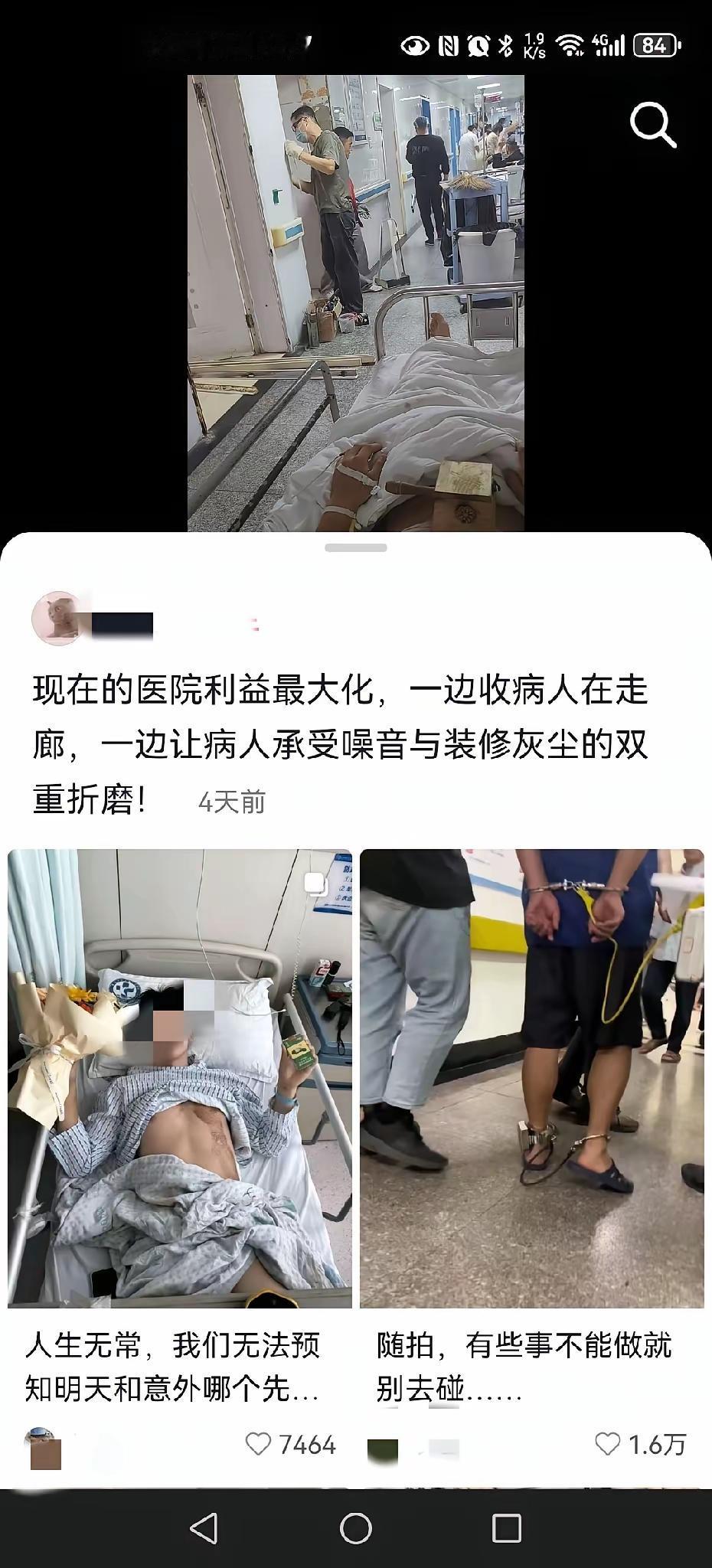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,妇联专门派人,把女医生韩秀荣强行带走。对此举动,韩秀荣问:“你们要干什么?把我带去哪里?”根本没有得到回答,不久后韩秀荣就被送到呼和浩特,在内蒙当了一名医生。 韩秀荣被带走那天,白大褂袖口还沾着没洗干净的碘伏痕迹。 前一分钟她还在河北邢台地区医院的妇产科诊室里,给一个胎位不正的孕妇做检查,手里捏着刚画好的胎位示意图,正跟孕妇家属解释注意事项,后脚就进来两个穿干部服的女人,直接架住了她的胳膊。 她当时急得声音都变了调,盯着桌上没写完的医嘱本,想跟同事交代一句“记得提醒李婶明天来复查”,可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,就被拽着往外走。 她那会儿32岁,从河北医学院毕业刚满8年,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妇产科副主任。老家在邢台农村,小时候亲眼见过邻居家的媳妇因为难产,找遍了周边三个村子都没找到懂接生的人,最后母子俩都没保住。 从那天起,她就攥着拳头跟娘说“我要当医生,专给女人看病”。后来她真考上了医学院,毕业时放弃了去北京大医院的机会,回了邢台——她总说“咱老家更缺医生,我得在这守着”。 这些年,经她手接生的孩子得有几百个,医院走廊里常有人抱着娃来给她送鸡蛋,说“韩大夫,这是您接生的娃,来认认恩人”。 被带上火车时,韩秀荣的心一直悬着。她不知道家里人会不会着急——早上出门时,丈夫还在院子里修自行车,跟她说晚上想吃她做的白菜猪肉炖粉条; 五岁的女儿攥着她的衣角,让她下班带块水果糖回来。现在自己突然被带走,连张纸条都没来得及留,他们找不见人该多慌? 火车一路向北,窗外的景色从绿油油的麦田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坡,再后来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,她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:妇联的人到底要让她干什么?为什么连个解释都没有? 到呼和浩特的时候是傍晚,天已经有点凉了。来接她的是当地医院的两个护士,接过她简单的行李,只说“韩大夫,跟我们走吧,医院还有病人等着”。 她跟着走了十几分钟,才看到所谓的“医院”——几间砖瓦房,窗户玻璃上还贴着补丁,门口挂着“呼和浩特市郊区医院”的木牌子。 走进诊室,她愣住了:只有一张旧检查床,听诊器的胶管都裂了口,药柜里除了青霉素、红药水,就只有几包益母草冲剂。 当晚就有病人找过来,是个牧民的妻子,怀孕七个月,肚子疼得直冒汗。 韩秀荣来不及多想,洗手消毒,用仅有的设备检查,发现是先兆早产。她一边安慰产妇,一边让人烧开水、找干净的纱布,凭着经验给产妇做保胎处理。 折腾到后半夜,产妇的腹痛终于缓解,牧民握着她的手,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“谢谢大夫,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”。 看着牧民感激的眼神,韩秀荣心里的委屈突然少了点——不管为啥被带到这,治病救人总是没错的。 后来她才慢慢知道,那时候国家正在号召支援边疆医疗。呼和浩特郊区还有不少牧区,牧民们看病要走几十里路,尤其是妇产科医生,整个郊区就只有一个老大夫,还快退休了。 妇联之所以没提前跟她商量,是因为任务急,怕有人因为家庭原因犹豫,耽误了当地病人。 知道真相的那天,她在诊室里坐了很久,想起老家那些等着她看病的乡亲,再看看眼前这缺医少药的草原,突然就懂了:哪里的病人都需要医生,这里比邢台更需要她。 从那以后,韩秀荣就扎在了草原上。没有设备,她就用手摸胎位,凭听诊器判断胎心; 药品不够,她就跟着牧民学认草药,用蒲公英、马齿苋给轻微炎症的病人外敷;牧区的病人来不了医院,她就背着药箱,骑着医院配的马,跟着牧民去草原深处。 有一次大雪天,一个牧区的产妇难产,她骑着马在雪地里走了三个小时,马滑倒了两次,她的裤腿都冻成了冰壳,可到了产妇家,她顾不上暖手,立刻投入接生,最后母子平安。 产妇家人给她端来热奶,她喝着喝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——那是她第一次觉得,自己来这里,是真的选对了。 她在呼和浩特一待就是28年,直到59岁退休。这期间,她带了8个徒弟,都是当地的年轻人,她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,还跟医院申请添了新的接生设备。 退休那年,好多牧民骑着马来送她,手里拿着奶豆腐、风干肉,说“韩大夫,您不能走,我们还想让您给娃接生呢”。她笑着说“我不走,退休了也在这住,你们有事还能找我”。 韩秀荣的故事,藏着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担当。她没被提前告知去向,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,一开始也有委屈和困惑,但当看到病人需要时,她还是选择扛起医生的责任。 那些年里,她用自己的医术,在草原上守护了无数母亲和孩子的平安,也把一份医者的温暖,留在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。这样的选择,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,却藏着最朴素的善良和坚守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