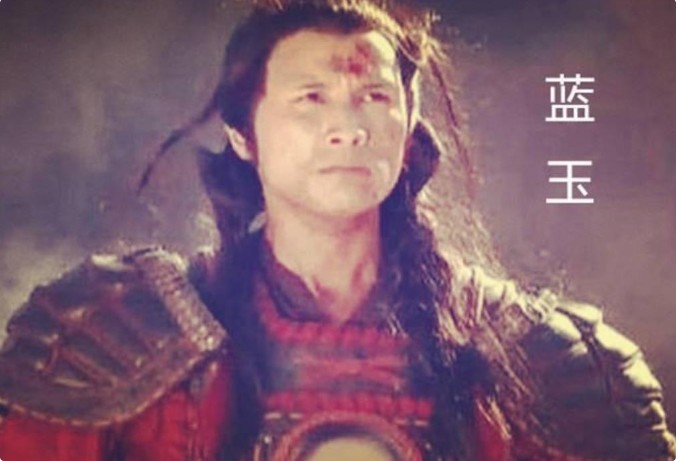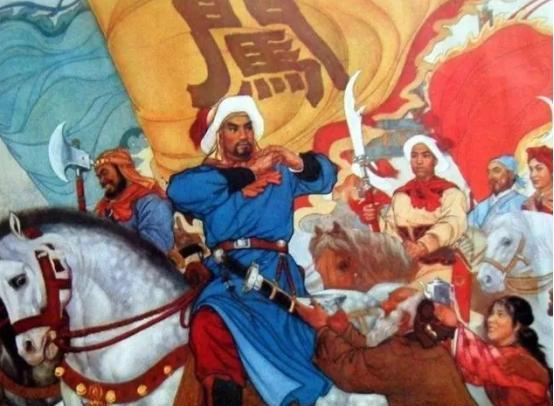1368年,元顺帝逃离前,告诉朱元璋:你是真龙天子,把天下交给你,也就放心了。拿得起,也放得下,元顺帝的心态,在亡国之君中没得说,独一档。 二十五万明军铁骑在徐达、常遇春的率领下已陈兵城郊,元都城破在即。 而这位大元王朝的末代君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,并未如宋徽宗般坐困愁城,也未如崇祯帝般决意殉国。 他站在宫城高台之上,遥望北方故土说出了:“朱元璋乃真龙天子,此天下交予他,吾心可安。” 元顺帝的统治,贯穿了元朝最后的动荡岁月。 他并非无能之辈,早年也曾励精图治。 1351年,黄河泛滥,民不聊生,红巾军起义烽火燎原。 年轻的顺帝试图力挽狂澜,恢复科举以选拔贤才,罢黜贪官以整肃吏治。 然而,整个元帝国早就腐败不堪,宫廷内斗更甚于外患。 权臣扩廓帖木儿也就是王保保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争权不休,宗室诸王各怀心思,朝政陷入瘫痪。 与此同时,南方的朱元璋,从一介布衣崛起,以“驱逐胡虏,恢复中华”为号,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,势力迅速壮大。 1367年,朱元璋发布《谕中原檄》,正式誓师北伐。 历史的洪流,已非个人意志所能阻挡。 当徐达、常遇春的北伐大军势如破竹,逼近大都时,元朝宫廷陷入一片恐慌。 朝堂之上,主战派主张据坚城死守,与社稷共存亡。 而贪生怕死之辈却力劝皇帝北逃,避其锋芒。 群臣争吵不休,元顺帝端坐龙椅,此时的他心中明镜一般。 “大都虽坚,然民心已失,军心涣散,强敌环伺,困守孤城,不过是重蹈北宋“靖康之耻”的覆辙。” 他脑海中浮现宋徽宗、宋钦宗被掳北上,受尽屈辱的悲惨画面。 身为黄金家族的后裔,成吉思汗的子孙,他绝不允许自己与宗室妃嫔沦为阶下囚,承受那等奇耻大辱。 此时,他决定必须走,而且要体面地走。 而朱元璋深谙政治之道。 大军压境之际,他并未急于攻城,而是先遣使者入城,试图劝降。 这既是展示“仁义之师”的姿态,也是给元顺帝一个台阶。 元顺帝拒绝了面见使者,却并非傲慢或胆怯。 他提笔蘸墨,写下了一首名为《答明主》的诗。 诗中,他承认天命已归新主:“金陵使者渡江来,万里烟云绕燕台。 信知海内归明主,亦喜江南有俊才。” 他坦然接受王朝兴替的规律,甚至流露出对朱元璋这位“江南俊才”的认可。 末句“我今北去返林泉,呼吸晴光意豁然”,则委婉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北归草原,而非投降。 这首诗,言辞恳切,不卑不亢,既维护了帝王最后的尊严,也为朱元璋的和平接收预留了空间,堪称政治智慧与文人风骨的绝妙结合。 收到诗作后,朱元璋心领神会。 而明军放缓了攻势,围而不打,实则是为元顺帝的撤离留出时间窗口。 1368年闰七月的一个深夜,元大都健德门悄然开启。 元顺帝并未仓皇出逃,而是安排撤离。 他命人妥善封存太庙典籍、宫廷档案,下旨留守官员不得抵抗,务必保全城中百姓。 随后,他携太子、后妃及少数心腹重臣,乘着夜色,离开了这座象征着蒙古帝国无上荣光的都城。 车驾驶向居庸关,奔向北方的草原。 元顺帝的北归,并非彻底的放弃。 抵达上都后,他迅速整合力量,册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,也速为梁王,试图联络辽东、云南、高丽等地的旧部,意图重整旗鼓,收复失地。 然而,大厦将倾,独木难支。 1369年,明军继续北进,上都失守。 元顺帝再退应昌,连续的颠沛流离,加上壮志难酬的郁结,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。 1370年四月,年仅五十一岁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。 临终前,他口中仍喃喃念及“收复大都”,但是病重的他深知复兴大元终究是一场幻梦。 消息传至南京,朱元璋的反应颇堪玩味。 他并未因对手的消亡而欣喜,反而展现出一位开国帝王应有的气度与远见。 他遣使北上吊唁,并郑重其事地追谥妥懽帖睦尔为“顺帝”。 这个“顺”字,既是对其顺应天命、主动退避行为的盖棺定论,也暗含了朱元璋希望借此安抚蒙古贵族、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考量。 朱元璋还下令编纂《元史》,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,并将部分蒙古贵族遗骨送还草原安葬。 元顺帝的选择,不是懦弱的逃亡,而是在无可挽回的败局中,为自身、为家族、也为曾经统治的这片土地,争取到的最大的体面与尊严。 他避免了玉石俱焚,保全了黄金家族的血脉,使得北元政权延续数十年,维系了蒙古文明的薪火。 元顺帝,以他的方式,为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,画上了一个虽败犹荣、令人深思的句点。 主要信源:(搜狐网——“元顺帝北逃,早知如此何必当初!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