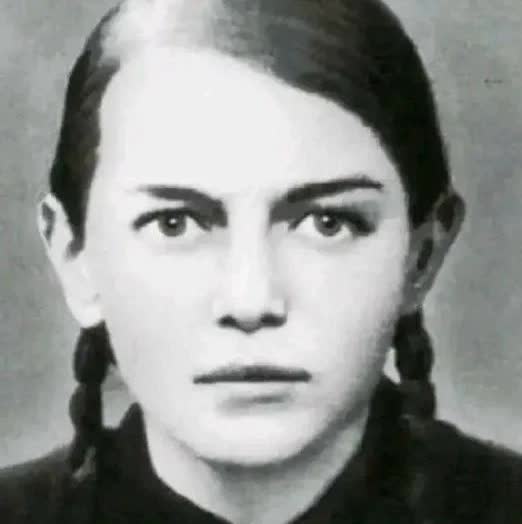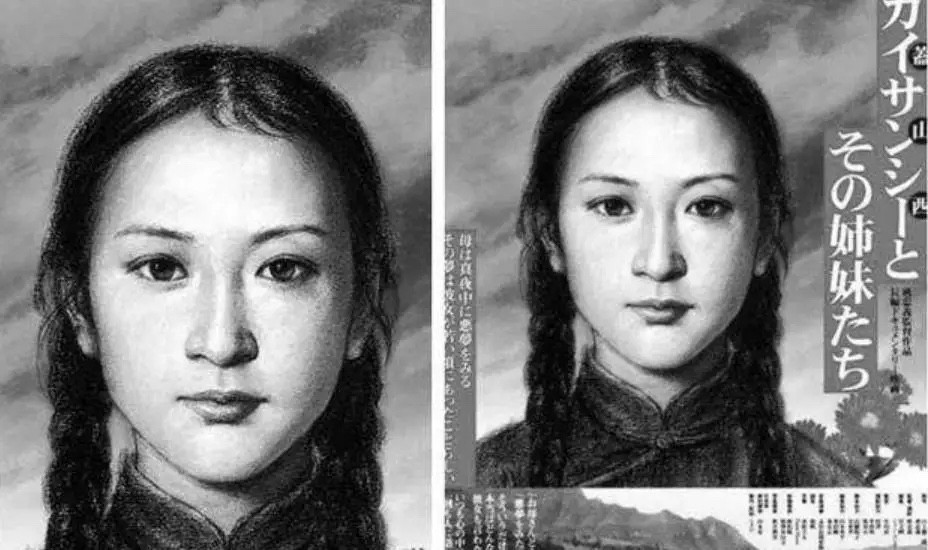1790年,一艘载有221名女囚的军舰从英国出发,到了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之后,人们惊奇地发现,200多名女囚竟同时怀孕了…… 1789年11月,这些女囚——年龄从12岁到60岁不等——被塞进了“朱莉安娜女士号”的底舱。她们中有偷面包的少女,有因债务入狱的母亲,甚至还有被诬陷的普通农妇。 舱底的空间狭小到连转身都困难,人均不到半平方米,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和呕吐物的味道。没有窗户,没有通风,温度常年维持在32℃以上。 她们每天蜷缩在黑暗中,啃着硬得像石头的饼干,嚼着咸得发苦的猪肉,渴了就喝带着铁锈味的淡水。 更有甚者,船长尼古拉斯将她们当作“商品”,在停靠里约热内卢时,公然让她们“接客”,每人收费1先令。反抗?等待她们的只有鞭打和更深的锁链压痕。 在这些女囚中,有一个名叫玛丽·韦德的14岁少女。她因偷了一件价值3先令的棉布裙而被判流放,瘦弱的身躯在舱底几乎站不稳。 起初,她也曾哭喊着求饶,但渐渐地,她学会了咬紧牙关,用破布条帮同伴擦拭伤口,用沙哑的嗓子哼唱童谣安慰那些崩溃的女人。 航程中,她亲眼见到有姐妹因疾病和虐待死去,尸体被草草扔进大海,溅起的水花像是在嘲笑她们的命运。 可玛丽没有放弃,她告诉自己:“只要活着,就有希望。”11个月后,当船靠岸时,玛丽挺着孕肚走下甲板,怀里的孩子虽是屈辱的产物,但她却紧紧抱住,喃喃道:“你是我的新生。” 总督菲利普面对这群“特殊移民”,眉头紧锁。殖民地本就男女比例失衡,16个男人才能分到一个女人,社会秩序岌岌可危。于是,他下令设立“女性工厂”,将这些孕囚和婴儿集中管理。 然而,条件之恶劣令人发指:工厂里没有足够的食物,婴儿只能喝稀薄的粥水,30%的孩子活不过一岁。 更残酷的是,殖民当局推行“强制婚配”政策,男囚犯可以用一件破衬衫“认购”一个妻子。 玛丽·韦德也被迫嫁给一个陌生男人,她没有选择,只能低头接受,因为她知道,只有这样,她的婴儿才能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。 时间快进到几年后,玛丽的孩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她用双手在殖民地的荒地上开垦出一小片菜园,用粗糙的布条缝制孩子的衣物。 她不再是那个舱底里瑟瑟发抖的少女,而是一个坚韧的母亲。她的后代,成为澳大利亚首批欧裔新生儿的一员,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。 历史数据显示,到1820年,殖民地57%的居民都有囚犯血统,这些女囚的后代,用汗水和生命,奠定了这片大陆的根基。 回望1790年的“朱莉安娜女士号”,那是一艘载满屈辱与罪恶的船只,但它也承载了生命的延续。 玛丽·韦德的故事,只是221名女囚中的一个缩影。她们在最黑暗的舱底里,用微弱的哼唱守护希望;她们在最残酷的制度下,用颤抖的双手托起婴儿的未来。 或许,正如牧师理查德·约翰逊在1790年布道中所叹息的:“用妓女建设道德社会无异于沙上筑塔。”但谁又能想到,这些被锁链捆绑的女人,最终用她们的血泪,浇灌出一片新大陆的生机? 1790年的女囚船事件,早已被历史尘封,但那些在锁链中诞生的摇篮,却仍在诉说生命的顽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