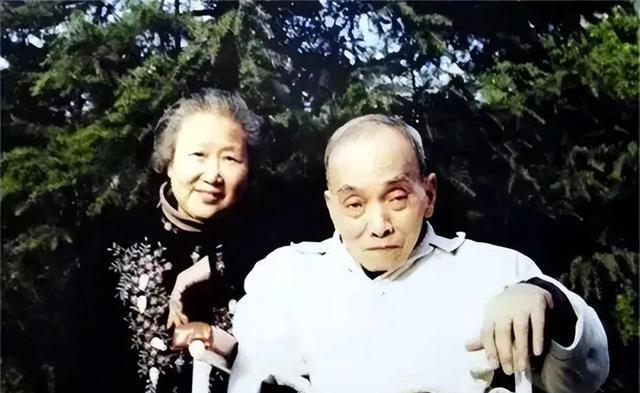1981年,电力部一些老同志联名向中央反映,对李鹏出任部长表示担忧。他们认为这位52岁的水电专家资历尚浅,难以服众。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,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,感谢您的强烈支持! 1981年北京某次高层会议的气氛格外凝重。 电力工业部老旧的吊扇在天花板上缓慢旋转,搅动着室内弥漫的烟草气息,却驱不散围绕在52岁李鹏身上的争议漩涡。 几位鬓发斑白的老干部攥着联名信,坚持认为这个“年轻人”压不住电力系统的阵脚。 尽管他已在吉林丰满水电站的轰鸣机组旁工作过二十余个春秋,尽管他曾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寒夜里翻译过成摞的俄文技术手册。 陈云的手指突然叩响桌面,声音不大却让全场静默。 “苏联伏尔加河畔的水电站图纸,他亲手描摹过;东北电网的故障抢修,他带人三天三夜没合眼。” 他目光扫过会场,落在反对者紧锁的眉头上: “现在搞改革开放,难道还要论胡子长短定交椅?” 墙上的电力调度图映着他清癯的面容,那张标注着全国缺电区域的地图,正需要新鲜血液来点亮。 这场风波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。 1948年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,刚满18岁的李鹏怀揣着周恩来亲赠的钢笔,在颠簸车厢里默背俄语单词。 七年留苏生涯,他在零下三十度的车间记录水轮机数据,伏案绘制的水电站结构图摞起来有半人高。 1955年归国时,他婉拒了部委岗位,主动选择深入松花江畔的丰满电厂。 当老工人们看着这个戴眼镜的“洋学生”徒手钻进尚有余温的发电机组检修时,怀疑的目光才逐渐转为信服。 然而1980年的电力部会议室里,资历的坚冰仍未融化。 某位反对者私下抱怨: “我们在战壕里摸爬时,他还在学俄文字母呢!” 这种质疑背后,藏着更深层的焦虑——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工厂因缺电停产,上海纺织女工在烛光下加班,广东新建的特区机器时常停转。 老干部们守着计划经济的老办法,对“集资办电”“引进外资”等新词充满警惕,唯恐这个留过洋的“技术派”会颠覆运行三十年的体制。 转机发生在暴雨夜。 辽宁电网突发故障,三座城市陷入黑暗。 刚被提名为副部长的李鹏直奔调度台,在闪烁的仪表盘前连续指挥十八小时。 当备用机组轰鸣着重启,控制室灯光亮起的刹那,满眼血丝的他指着屏幕上跳动的负荷曲线对值班员说: “看见没?这里藏着未来十年的用电需求。” 这场危机处理报告被陈云放在案头,成了打破僵局的关键砝码。 任命通过后,李鹏的办公室彻夜长明。 他案头摆着三样东西:苏联导师赠的工程计算尺,东北工人送的搪瓷缸,还有张被红蓝铅笔划满的电网改造图。 1982年春天,当大亚湾核电站的奠基石在南海之滨落下,当初的反对者受邀观礼时,有人望着塔吊林立的工地喃喃: “原来电还能这么‘发’……” 七年后,全国发电量较他上任时翻了一番,那些曾质疑“年轻人”的老同志,终在退休茶话会上举起茶杯: “当年是我们眼拙了。” 历史总在回响。 2018年某新建特高压变电站的开工仪式上,总工程师指着控制室里银发的李鹏照片对年轻团队说: “记住,技术不会老,怕的是思想生锈。” 窗外,智能巡检无人机正掠过绵延千里的银线,像一只振翅的鹏鸟。 主要信源:(澎湃新闻——李鹏任电力部长前曾遭多人联名写信反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