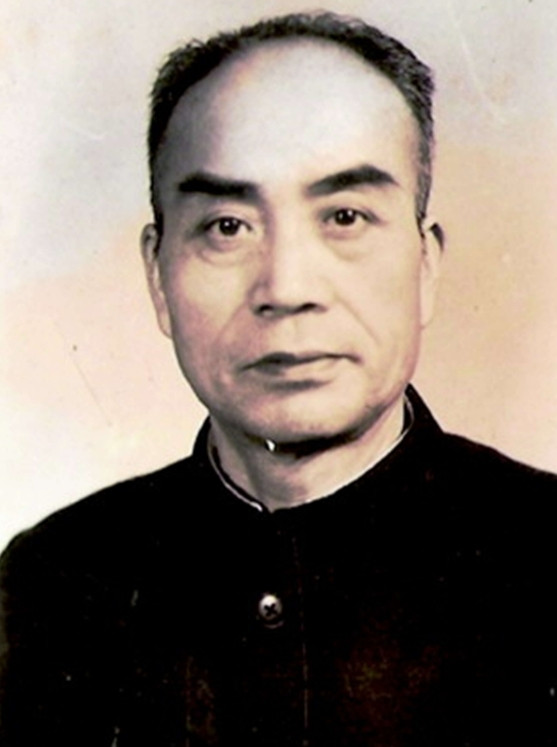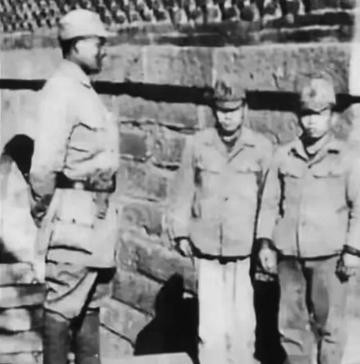1938 年,台儿庄战役,16 岁的 “狼兵” 韦容松正在巡逻,途中他碰到了由 6 名日军组成的特工队,他决定干掉他们! 夜色像浸了血的破布,蒙在台儿庄的山头上。韦容松的草鞋陷在泥浆里,每拔一步都带着 “咕叽” 的声响,混着远处炮弹的轰鸣,像极了老班长临死前的喉鸣。 他把步枪攥得发颤,枪管上还留着淞沪战场的弹痕 —— 那是老班长用身体替他挡住刺刀时,子弹擦过枪身留下的印记。 侦察班失联已经四个时辰。韦容松顺着他们的足迹爬上坡,草窠里突然绊到个硬东西,伸手一摸是只冰冷的手。 借着炮弹炸开的火光,他看清了:七八个弟兄横在地上,领章被血泡得发黑,伤口都在胸口和咽喉,是刺刀捅的。 他往手心啐了口唾沫,摸到怀里爹给的纸条,糙纸边缘被汗浸得发卷,“倭寇除尽日,我儿还家时” 几个字磨得快要看不清。 山坳里飘来烤肉的香味,混着日军特有的羊膻味。韦容松趴在茅草丛里,睫毛上挂着草籽,看见六个人围着篝火,穿的是桂军的灰布军装,脖子上却都系着白毛巾 —— 那是日军特工的记号。 一个矮个子正用刺刀挑着块肉,腰间晃着的九七式手雷,在火光里闪着冷光。他们脚边扔着侦察班的步枪,枪托上刻着的 “48 军” 番号被踩得模糊。 韦容松摸了摸腰间的四颗手榴弹,木柄被体温焐得温热。他数着对方的呼吸声,五个脑袋耷拉着,放哨的靠在树干上,刺刀插在土里,枪管随着打盹的动作一点一点往下沉。 云层刚好遮住月亮,他咬开手榴弹的铁盖,金属味混着嘴里的血腥味直往喉咙里钻。 拉环 “咔哒” 的轻响被风吹散。他像扔石头打鸟那样,把四颗手榴弹连成线甩过去,弧线刚好落在火堆边。 第一声爆炸掀飞了矮个子的半个身子,剩下的人还没爬起来,第二颗、第三颗、第四颗接连炸开,火光把山坳照得如同白昼。 韦容松趴在原地没动,直到听见有个喉咙里发出 “嗬嗬” 的声响,才端着步枪摸过去。 那个没死透的日军正往枪套够,韦容松的刺刀已经扎进他的胸口。拔出刀时,血溅在他脸上,和泪水混在一起。 篝火边散落着日军的身份牌,他捡起一块塞进兜里 —— 老班长说过,这是给弟兄们报仇的凭证。 地上还留着半块烤焦的肉,他用刺刀挑起来扔远了,“狗东西,也配吃猪肉”。 回到营地时,天快亮了。韦容松把缴获的两支三八大盖往地上一摔,枪托撞在石头上的声响,惊醒了打盹的连长。 “六个。” 他开口时嗓子像被砂纸磨过,掏出身份牌往桌上一拍,六块金属片在油灯下泛着寒光。 连长摸着他炸破的袖口,突然给了他一拳,“你个狼崽子,命不要了?” 这一拳把他打笑了,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 —— 那是上个月拼刺刀时被鬼子打掉的。 武汉的秋天来得早,韦容松的草鞋磨穿了底。他蹲在战壕里,用捡来的布条缠脚,听老兵说鬼子要发动总攻了。 怀里的纸条被血浸得发脆,爹的字迹洇成一片红。当那颗炸弹滚进战壕时,他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,是没能给爹回信说 “快了”。 他扑上去的瞬间,好像又听见老班长在喊 “趴下”,就像在淞沪战场那样。 台儿庄战役纪念馆的玻璃柜里,六枚锈迹斑斑的子弹壳排成一排。旁边的照片上,韦容松穿着过大的军装,领口别着朵纸做的桂花 —— 那是出发前,村里的阿婆给他戴上的。 讲解员说,这孩子到死都不知道,他爹在他参军后就病死了,临死前还攥着那张没寄出的回信,上面写着 “家里的稻子熟了,等你回来割”。 每年清明,都有穿校服的孩子来献花。他们盯着那六枚弹壳,听这个十六岁少年的故事。 有人问 “他不怕吗”,讲解员总会指着玻璃柜里的半块发霉干粮:“你看,他和你们一样,也会饿,也会怕,但他知道,有些东西比命金贵。” 参考来源:《解放军报》2023年清明特别报道《血色青春:抗战中的少年英雄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