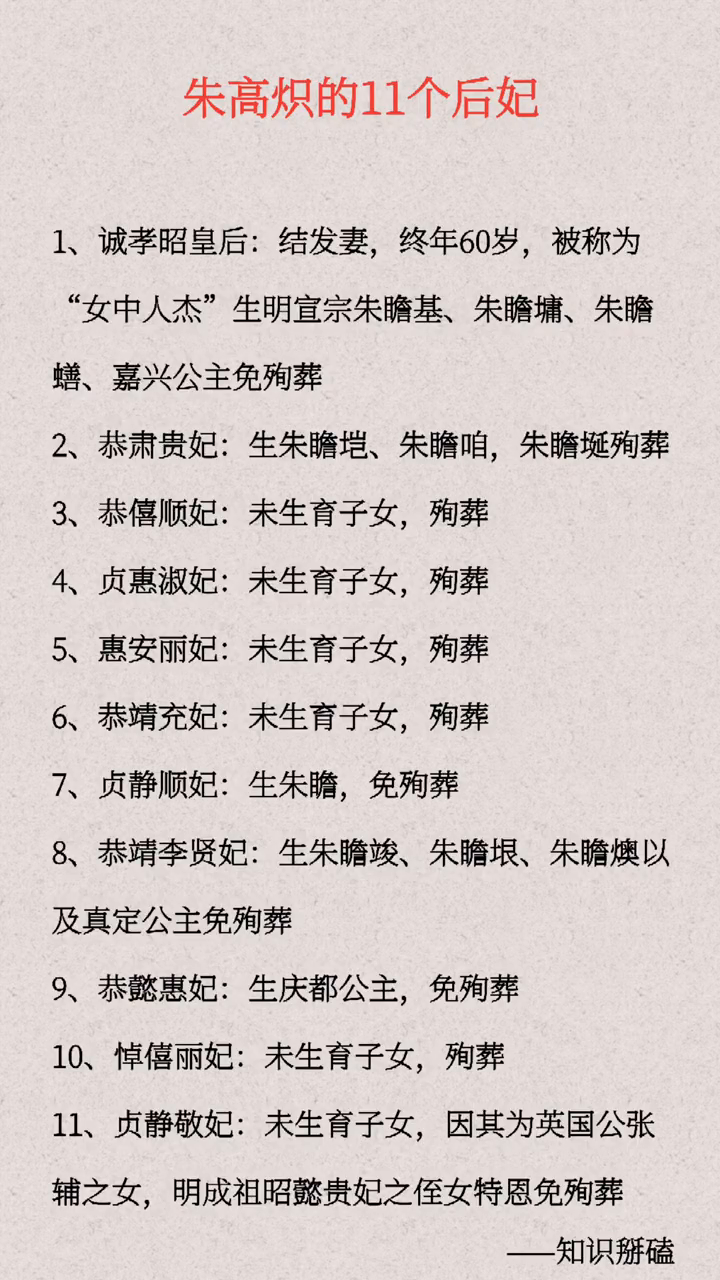1627年,天启帝驾崩,21岁的张皇后守寡。一天,一名太监突然溜进她的寝宫,意味深长的说:“皇后你孤苦无依,不如与我结成对食?” 张皇后正对着铜镜摘凤钗,银簪“当啷”掉在妆台上。她没回头,铜镜里映出那太监弓着的脊背——是魏忠贤身边最得势的王体乾,前几日还在御座前跪着喊她“千岁”,此刻袍角沾着的龙涎香,竟比新帝崇祯赏赐的还要浓郁。 “你可知这宫墙里,敢对皇后说这话的人,坟头草都三尺高了?”她的声音很轻,指尖却捏紧了袖口的玉扣。那玉扣是天启帝亲手给她系的,边角被摩挲得温润,此刻硌得掌心生疼。 张皇后不是普通的后宫女子。 她叫张嫣,出身河南祥符的书香门第,选秀时以“贞静端丽”被天启帝选中,15岁就成了皇后。这姑娘别看年轻,骨头却硬得很。天启帝沉迷木工,朝政被魏忠贤和客氏把持,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,唯独她敢在皇帝面前骂魏忠贤是“阉贼”,还曾搜集证据想扳倒他,可惜被客氏从中作梗,反被污蔑“善妒”,差点被废。 而王体乾,是魏忠贤的“左膀右臂”。 这人原是司礼监秉笔太监,见魏忠贤得势,就主动投靠,帮着构陷东林党,迫害忠良,手上沾了不少血。魏忠贤懒得处理的琐碎事,全由他代劳,宫里人都说“王体乾的话,比九千岁(魏忠贤)的圣旨还管用”。他敢对张皇后说这话,不是疯了,是觉得新帝崇祯刚即位,根基未稳,魏党势力仍在,一个寡妇皇后,捏在手里易如反掌。 “皇后说笑了。”王体乾直起身,语气里的恭敬全没了,带着几分戏谑,“如今万岁爷(崇祯)忙着清算前朝旧账,哪顾得上坤宁宫?您守着这空宫殿,不如寻个依靠——咱家在宫里说了句,谁敢不给面子?” 他往前凑了两步,盯着铜镜里张嫣的脸。21岁的皇后,眉眼清丽,虽素服在身,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贵气,是宫里那些趋炎附势的宫女比不了的。他想要的,不只是“对食”的名分,是借她的皇后身份,在魏党内部更上一层楼。 张嫣猛地转过身,铜镜被带得晃了晃,映出她眼里的冰。 “王体乾,你主子魏忠贤教你‘尊卑’二字怎么写吗?”她抓起妆台上的玉簪,直指对方,“我是天启帝的皇后,是新帝的皇嫂,你一个阉竖,也配谈‘依靠’?” 王体乾脸上的笑僵了。他没想到这寡妇皇后还敢硬顶,可转念一想,她没了皇帝撑腰,再硬又能怎样? “皇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他压低声音,语气狠了起来,“咱家不妨告诉你,客巴巴(客氏)说了,您要是识趣,往后宫里的份例少不了;要是不识趣……当年胡皇后(被废的妃子)的下场,您该记得。” 客氏是天启帝的乳母,与魏忠贤勾结,害死过不少后妃,手段阴狠。王体乾这话,是赤裸裸的威胁。 张嫣的手有些抖,不是怕,是怒。她想起天启帝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说“吾弟(崇祯)仁明,必能护你”,想起那些被魏党害死的忠臣,牙齿咬得咯咯响。 “你去告诉客氏和魏忠贤,”她一字一顿,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,“我张嫣生是朱家妇,死是朱家鬼。想逼我低头,除非我死了!” 她说着,猛地将玉簪往自己颈间划去。 王体乾吓了一跳,慌忙伸手去拦,玉簪尖划破了她的脖颈,渗出血珠,红得刺眼。他知道真逼死了皇后,崇祯再仁厚也不会放过他,赶紧松手,色厉内荏地骂了句“疯妇”,灰溜溜地跑了。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殿门后,张嫣才扶着梳妆台滑坐在地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 她不是不怕,只是不能怕。这宫里,她是最后一个能站直腰杆的“朱家妇”了,要是连她都屈了膝,那些死去的忠臣,那些盼着清明的百姓,还有什么指望? 这事很快传到崇祯耳朵里。 新帝正在批阅奏折,听说王体乾逼宫,气得把朱笔都摔了。他虽刚即位,却早就看不惯魏党专横,只是苦于根基未稳,没法立刻动手。张嫣的刚烈,像一根火柴,点燃了他心里的火。 “皇嫂受委屈了。”崇祯亲自到坤宁宫探望,见她颈间的伤口,眼圈红了,“朕向你保证,不出三月,必除奸佞。” 张嫣扯出个笑,谢了恩,没多说什么。她知道,朝堂的刀光剑影,比后宫的阴私更凶险,她能做的,只有守住自己的底线。 果然,三个月后,崇祯先拿客氏开刀,将她赶出宫,又罗列魏忠贤十大罪状,逼得他自缢。树倒猢狲散,王体乾见势不妙,想带着赃款跑路,被崇祯下令抓回,活活打死在诏狱里,家产抄没,亲族流放。 清算魏党的那天,张嫣站在坤宁宫的台阶上,望着宫里飘起的白幡(魏忠贤党羽被处死的标志),轻轻抚摸着颈间的疤痕。那道疤,成了她的勋章。 崇祯感念她的忠烈,尊她为“懿安皇后”,礼待有加。每当朝堂有难,他都会派人到坤宁宫请教,张嫣从不多言,只捡要紧的提醒几句,却往往切中要害——她虽在深宫,却比谁都懂“民心”二字的分量。 信息来源:部分情节参考《明史·后妃传》《明季北略》及《崇祯长编》中关于懿安皇后张嫣与魏党斗争的记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