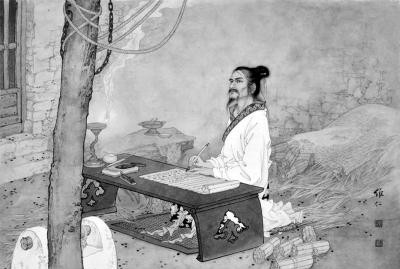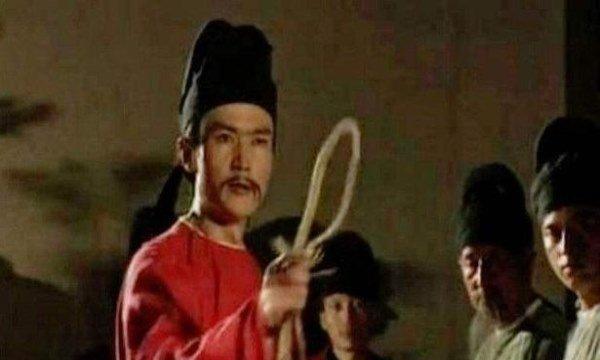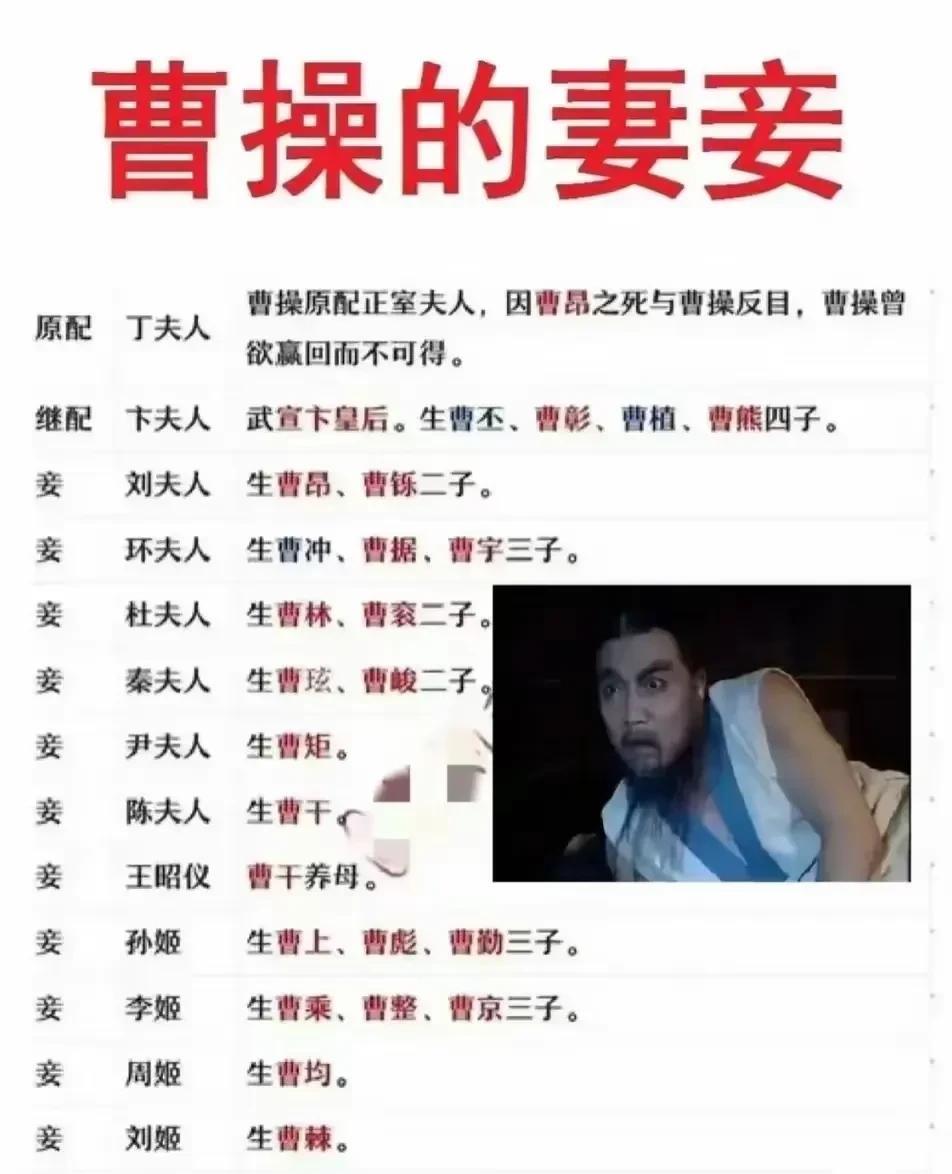公元前99年,司马迁被绑在冰冷的木头架子上,衣服扒得精光,行刑的匠人手起刀落,司马迁由男人变成了一个阉人。妻子柳倩娘心疼的直流眼泪,之后她的选择,至今令人唏嘘落泪。
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的一个史学世家。他的父亲司马谈身为太史令,不仅掌管天文历法,更肩负着记录天下的重任。
而司马迁自幼浸润于古籍简牍,十岁便能通读深奥古文,学识在同辈中脱颖而出。
更难得可贵的是,他十分的热爱学习特别是研究历史,要知道孩子的天性就是爱玩,但是她的童年只喜欢读书。
年轻时的司马迁,渴望用脚步丈量山河,想去感悟历史。
于是他就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他的足迹踏遍华夏南北,在屈原投江的汨罗江畔感受诗人的绝望忠贞。
亲赴儒家圣地曲阜,感受孔子遗风。
深入烽烟四起之地,触摸真实的金戈铁马。
而这些经历都为他日后著作《史记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之后的他子承父业,他爹退休了他上去顶他爹了活,去当官去了。
在公元前99年,当时汉武帝派大将李广利征讨匈奴。
李陵也就是李广之孙,率五千步兵深入敌境担任策应掩护任务。
但糟糕的是李陵遭遇匈奴八万铁骑的重重包围。
他率部血战数日,以寡敌众,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重创敌军。
最终把人都打没粮食也没看,最后这支残兵最终在绝望中溃败,李陵本人被俘。
这则消息在长安掀起滔天巨浪。
满朝文武深知武帝暴戾性情,众口一词痛斥李陵懦弱无能、临阵降敌,以迎合圣心自保。
只有司马迁不肯为自保沉默。
司马迁对李陵还是有点了解的,他坚信李陵力战被围实属无奈,弹尽粮绝而败北并非失节怯懦。
然而这份冷静的判断与微弱的良知,在排山倒海的指责声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他试图在朝堂之上为李陵辩白,陈述战场实情。
但是就是这一辩,给自己整没了。
当时汉武帝就在气头上,他认定了司马迁的“公正之言”是在为叛逆张目。
皇帝怒不可遏,直接将司马迁打入死牢,这是权力对勇气的终极碾压。
依照残酷的汉律,尚存一丝“生机”,可用巨额金钱赎命,或以承受屈辱的宫刑代替死刑。
面对贫困家底根本无法承担的赎金数额,司马迁只能选择第二个方案。
死,不失为一刹的解脱,但是生,却意味着永久性地被世俗社会视为非男非女、尊严尽碎的“废人”。
这个选择痛苦到几乎无法呼吸,一边是保全尊严的清白赴死,一边是忍受生理巨痛与终生耻辱的偷生。
然而,在生死抉择的彻骨黑暗中,一个承诺的光芒从未熄灭,父亲临终时交付于他编纂一部旷世通史的如山重托!
这未完成的使命,像一道刻骨铭心的誓言,压倒了所有恐惧与痛楚。
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宫刑。
这不是怕死而是还有任务在等他,他清楚人终有一死,有人死比鸿毛还轻,有人却能让生命重于泰山。
当行刑后遍体鳞伤的司马迁被抬回家中。
在那个对受刑者极度鄙弃的年代,他被许多人视为耻辱的污点。
唯有一人,一直不曾远离,那人便是他的妻子柳倩娘。
她没有因飞来的横祸和难以言说的残损之躯而离去,也并非迫于礼教勉强留守。
一个妻子对丈夫深沉的爱意,一个理解者对一颗不灭信念之星的敬仰与成全,支撑着司马迁度过那些生不如死的时光。
柳倩娘留在丈夫残破身躯旁的那份恒心与温暖,最终成为护佑《史记》诞生的一道人性光芒。
她的“无声坚守”,千年后读来依然能撞击心灵最柔软的深处。
在巨大的屈辱之下,在身体残缺的阴影中,司马迁拖着尚未愈合的伤体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壮阔的长征。
无数个不眠之夜,他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和心理的煎熬,将生命全部的愤懑、悲凉、不屈与热望化作笔下的力量。
他啥都写,上至轩辕黄帝,下达汉武帝时代,囊括三千年历史风云。
一百三十篇巨著,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,包罗万千,直面真实,开创纪传体例,直斥君王过失,如《封禅书》中不避讳针砭汉武帝求仙之愚行。
当司马迁终于落下绝笔时,他完成的不只是一部史书,而是将个人精神升华为一座超越时代的不朽丰碑。
而这部用血泪甚至一部分生命换取的《史记》,成为照亮后世两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永恒灯塔。
班固、司马光等后来者,都在其基础上书写各自篇章。
其深邃的洞察力与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的求真精神早已融入了中国文脉。
当年刑场上那具残损的身体早已消逝在风中。
但司马迁留给华夏的魂魄却在千年岁月中愈发厚重。
这正是一部真正属于人的精神史诗。
即便命运将其锤击得血肉模糊,他却以超乎常人的精神意志在断壁残垣上,重建了一座后人无法逾越的丰碑!
如今,当我们遭遇不公敢怒不敢言,面对压力选择沉默,因畏惧失去而不敢坚持己见时,那位拖着残躯在油灯下书写真理的身影,依旧如星辰刺破夜空。
真正的伟业,从来不需要完美的躯壳去成就。
有时,最深的破碎恰恰能孕育出最坚不可摧的灵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