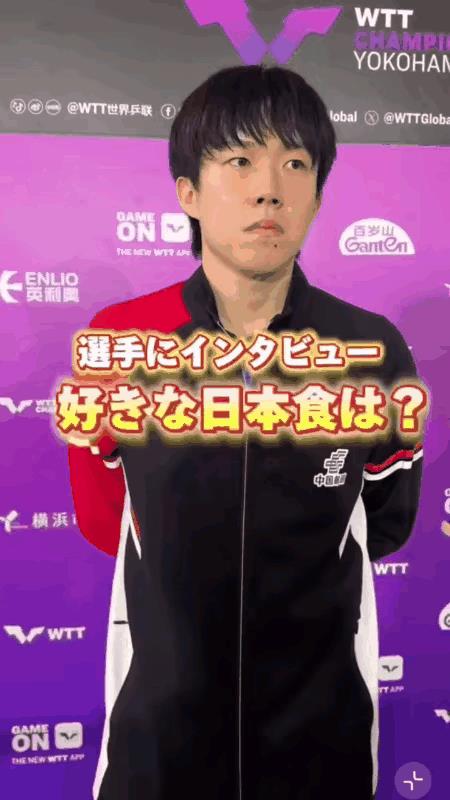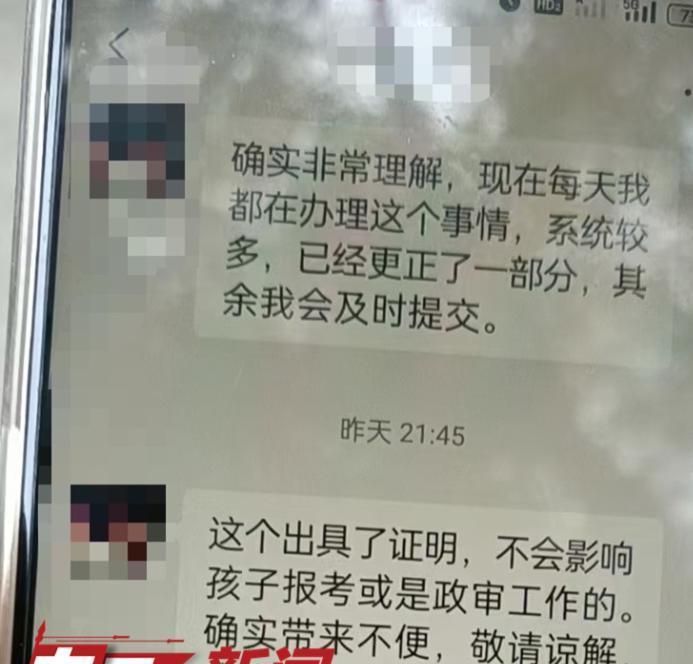1966年,大庆油田发现者谢家荣吞下一整瓶安眠药,在家中自戕。第二天,妻子吴镜侬在他身边发现了一张字条,上面短短十个字令人泪目。
这还要从1913年的上海弄堂说起,那时候15岁的谢家荣攥着窝头挤上北去的火车。
正好赶上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招生,那在当时全国仅招30人,穷学生谢家荣连初中文凭都没有,硬是凭着一股“石头缝里钻劲儿”考了头名。
三年后毕业,全班仅18人拿到文凭,史称“地质界十八罗汉”,他还是最年轻的那个。
这就足以证明这的有多么难。
在他毕业时老师章鸿钊赠他《地质学原理》,扉页题字“为国探矿,方为大用”。
而这话烙进他心里,往后五十年,他的足迹踏遍中国,地质锤磨短了三寸,罗盘针晃白了鬓角。
在1921年安徽八公山,暴雨冲垮山路,谢家荣和助手困在山洞。
他举油灯照岩壁,突然抓起块黑石用舌舔,有煤的涩味!
众人笑他疯癫,但是他却断定,这页岩下必有大煤田!
就在数月后钻机轰鸣,煤层厚达4米,而淮南亿吨煤田就此现世,江南工业命脉由此打通。
他找到不止是媒,还有各种稀有的矿物质。
在福建漳浦野草丛,他趴地三天扒出层状铝土,炼出中国首块航空铝。
之后又辗转南京栖霞山,凭老乡一句“石头长绿毛”,就挖出铅锌银矿,填补华东冶金空白。
之后在甘肃白银厂,指着铜锈石头喊“往下打!”,钻头穿透三层矿脉,新中国第一铜矿诞生。
工人们叫他“谢神仙”,他却摇头,哪是仙?是把鞋底磨穿,把石头看穿!
他总说纸上得来终觉浅,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
在野外考察时,他一个一个的敲石头,亲手记数据,放大镜磨得比眼镜片还亮。
晚上在油灯下画图,蚊子嗡嗡叫,他就往身上抹点煤油。
学生们说,先生的地图比军令状还准。
但凡是他说地下有矿物质的话,那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,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,那就是准啊。
1954年的北京地质局,满墙挂满《中国含油远景图》。
那时候国家刚解放,要找大油田。
谢家荣红笔圈出松辽平原,这里定有油!古潜山构造就是聚油盆!
然而这里可是当时国际公认“中国贫油”,就连一旁的同事嘀咕,老谢又做梦。
但是他却拍桌,大庆地下躺着油龙,不找是罪人!
没想到正如他所说五年后大庆出油,举国欢庆。
庆功会上无人提他,因他正被扣“洋奴”帽子扫厕所。
在1966年,所有的风向变了。
有人翻出他早年的留学经历,说他“里通外国”。
有人指着他的研究报告,说“净搞些没用的石头”。
批斗会一场接一场,他腰不好,站不住,就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。
直到晚年,学生黄汲清才敢说破,松辽盆地是他命名,油田坐标是他亲手标!
1966年夏,地质科学院大院。
68岁的谢家荣被按跪在地,造反派往他脖挂“反动权威”铁牌。
汗滴进眼睛,他忽然笑出声,想起1937年北平沦陷时,日本人逼他当伪北大校长,他连夜翻墙逃往西南。
“当年拒倭寇,今朝成罪人?
批斗会上他梗脖子,我找的矿埋在地下!抹不掉!
深夜归家,却摩挲着矿石标本喃喃,还是你们实在。
死前三天,他将400篇论著捆好,封面写“献给国家”。
罗盘擦得锃亮,这物件陪他五十年,探过矿脉,躲过炸弹,最终在遗书旁静默如碑。
他走后,骨灰盒空置。
儿子谢学锦放入他磨秃的罗盘,指针颤巍巍定在“N”位,像一生未改的信仰。
1982年,国家追授他自然科学一等奖,大庆油田立碑列他为首功。
如今,他发现的煤矿仍汩汩输着工业血脉,他命名的油田仍奔涌着黑色黄金。
所谓丰碑,不必刻于金石,深扎大地的矿脉,即是地质人最硬的脊梁。
人的一辈子很短人,能做的事有限。
但是谢家荣把一辈子交给了石头,交给了脚下的土地,他应该被历史记住,被我们记住。
作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,他对中国矿产资源开发产生深远影响,而且留了诸多的宝藏,让我们永远的将他牢牢的记载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