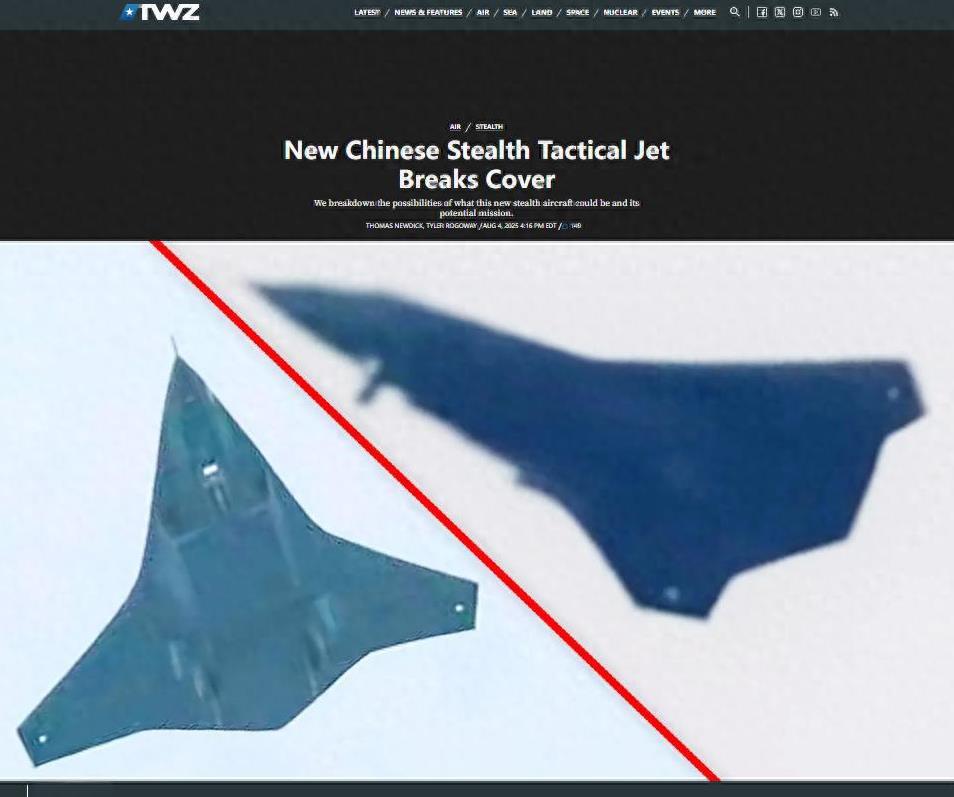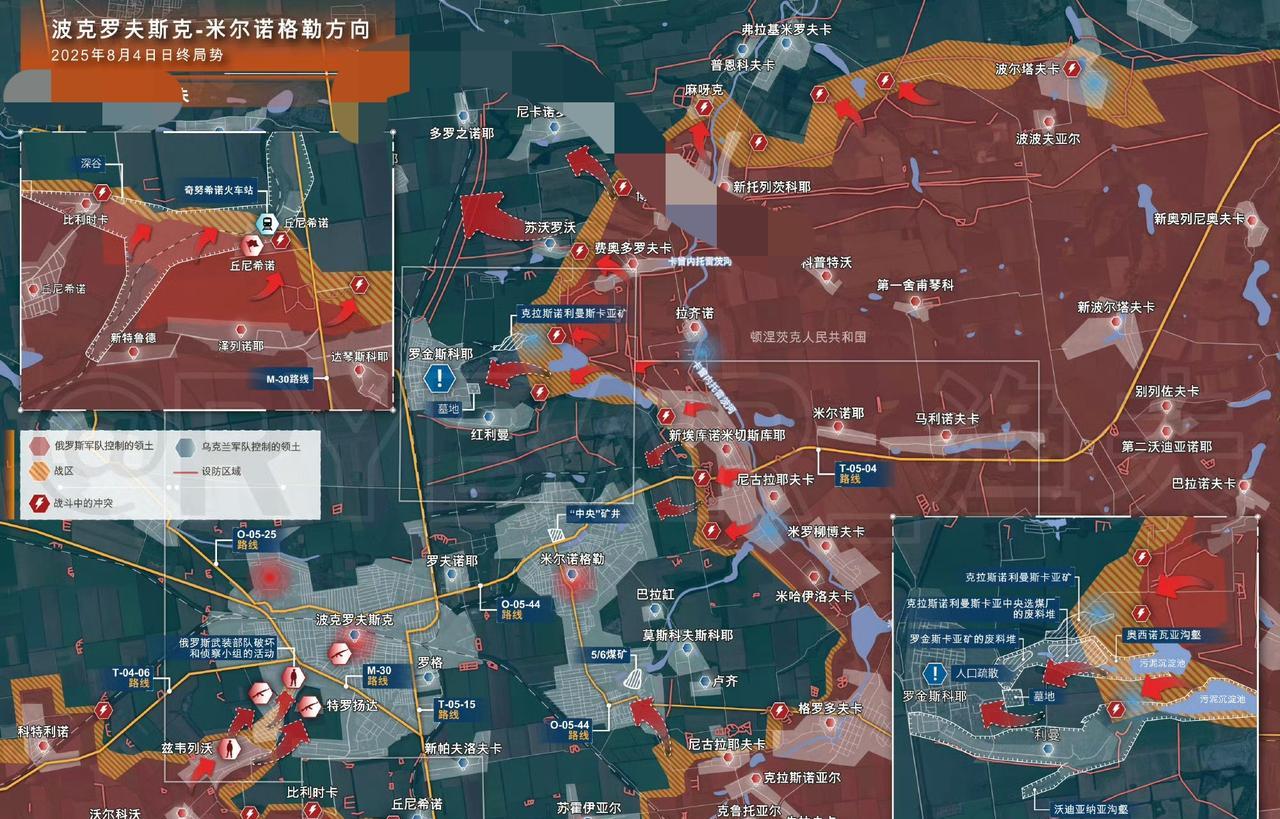2007年,一名军人在部队接受领导检查时,却突然发现他额头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,领导连忙询问刀疤的来历,没想到,就是这一问竟然揭开了一个隐藏六年的秘密...... 2007年秋天的一天,部队例行检查,负责此次巡查的白吕政委走过一排排战士,目光在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掠过,队伍整齐,步伐坚定,每一名战士都神情专注,可当他走到一位名叫卢加胜的士兵面前时,脚步稍微顿了一下,原因很简单——卢加胜额头上那道长约五厘米的疤痕太显眼,深深地刻在皮肤上,像被刀劈出来的一道裂口。 这道疤不像普通的磕碰所致,更不像训练中偶然留下的伤口,它锋利而深沉,像是从极端凶险的搏斗中留下的印记,白政委心里暗暗警觉,他在军中多年,见过太多伤痕,一眼就看出这并不寻常,他担心这可能与打架斗殴有关,或者是一次未曾上报的重大事故,出于职责,他没有放过这个疑点,当天晚上,卢加胜被叫去政委办公室,终于,那段沉默了六年的往事,被一层层揭开。 时间倒回到2001年2月11日,春节刚过,卢加胜结束探亲假,从家乡四川乘坐K148次列车准备返回武昌部队,那时的他已在部队服役六年,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,坐在硬座车厢,肩上的军徽在窗外阳光下泛着微光,列车上人流如潮,春运高峰让车厢变得拥挤嘈杂,乘客们席地而坐,行李堆得满满当当,空气中是方便面的味道和旅途的疲惫。 列车行驶到某段偏远地段时,原本的喧闹突然被一阵骚动打断,车厢连接处传来尖叫和哭声,一阵混乱迅速蔓延,有人惊慌地跑过来,大喊着让人躲避,说前方车厢进了歹徒,很快,一个满头大汗的乘警穿过人群,急匆匆地找到了穿军装的卢加胜。 原来,4号和5号车厢被七十多个手持利刃的歹徒占据,这些人分工明确,成群结队,正在挨个抢劫乘客财物,他们手中的砍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,乘客们被吓得不敢出声,女人紧紧护着孩子,老人低头不语,整个车厢陷入恐惧与绝望之中,乘警人手不足,只能寻求列车上军人的协助。 卢加胜没有犹豫,他迅速起身,沿着狭窄的过道一路向前奔去,途中,他遇到了其他返程中的战士们,共有23人,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单位的军人,但此刻没有人退缩,几句话的交流后,他们形成了临时战斗小组,默契地跟着卢加胜向危险的车厢靠近。 当他们靠近目标车厢时,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,歹徒们正逼迫乘客缴纳所谓的“座位费”,有人反抗就被刀劈伤,鲜血溅在地板上,孩子的哭声和女人的惊叫此起彼伏,那种混乱,已经超出了普通抢劫的程度,更像是一场有组织的暴力袭击。 面对如此悬殊的局势,卢加胜冷静指挥,他将战士们分成几组,从不同方向包抄进入车厢,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局面,他们没有武器,只能就地取材,有人拿起保温壶,有人扯下行李架当盾牌,卢加胜冲在最前面,他知道必须尽快制服带头的歹徒,否则局面会彻底失控。 战斗在狭窄的车厢中爆发,卢加胜在搏斗中腿部被砍了一刀,鲜血染红了裤脚,但他没有停下,继续强攻时,又一把刀划向他额头,一道五厘米长的伤口撕裂了皮肤,鲜血瞬间涌出,他的视线被血模糊,耳边是刀与金属碰撞的声音、战友的喊声和乘客的哭泣,他顾不上伤痛,一边指挥战友堵截逃窜的歹徒,一边继续冲锋。 战斗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,车厢内温度急剧上升,混合着汗水、血腥和紧张气息,直到火车抵达武昌站,警方增援赶到,战斗才终于结束,七十多名歹徒被悉数控制,乘客无一人伤亡,卢加胜不顾自己伤势,协助清点现场,直到最后一名旅客安全离开,他才感到眼前一黑,倒在站台。 被送到医院时,他浑身血迹斑斑,军装都变成了硬壳状,医生诊断他有十三处刀伤,其中额头伤口深及颅骨,差一点就伤到大脑,更严重的是,他失血过多,陷入昏迷整整十天,醒来后,他第一件事不是问自己伤情,而是确认列车上的百姓是否都安然无恙。 出院后,他没有留下姓名,也没有接受任何表彰,他撕掉了诊断书,自己付了8000多元的医药费,穿上干净军装,悄悄归队,他不曾向任何人提起这段经历,面对战友的询问,他只是说是“磕着了”,此后几年,他默默训练、出操、站岗,额头的疤痕随着时间变成了一道醒目的伤印,而他从未解释过它的来历。 这场事件虽然引起了媒体和铁路系统的广泛关注,《解放军报》曾连续报道寻找那位“无名英雄”,但卢加胜始终沉默,由于名字登记时因为方言被误写,他更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,成为一个谜。 直到2007年,白吕政委敏锐地察觉这道疤的异常,顺藤摸瓜查证,才确认了卢加胜的身份,部队、铁路局、当年的乘警都陆续提供了证据,指向这个一直藏在队伍中的英雄,那年秋天,卢加胜终于被公开表彰,可他始终低调,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,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