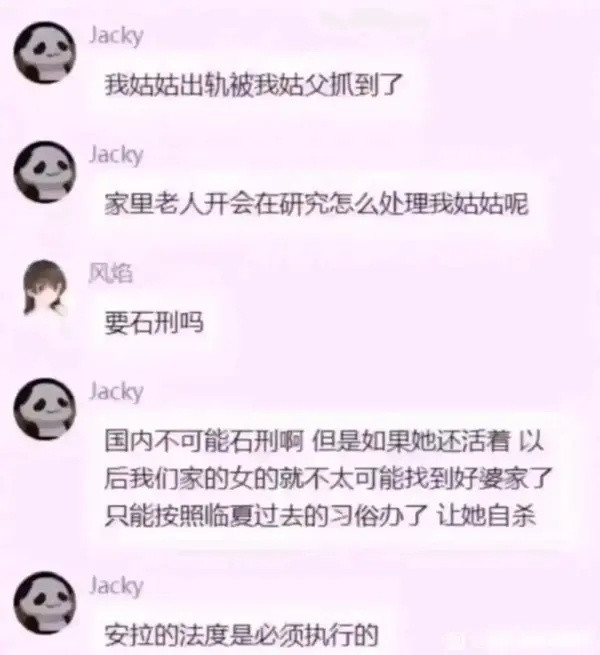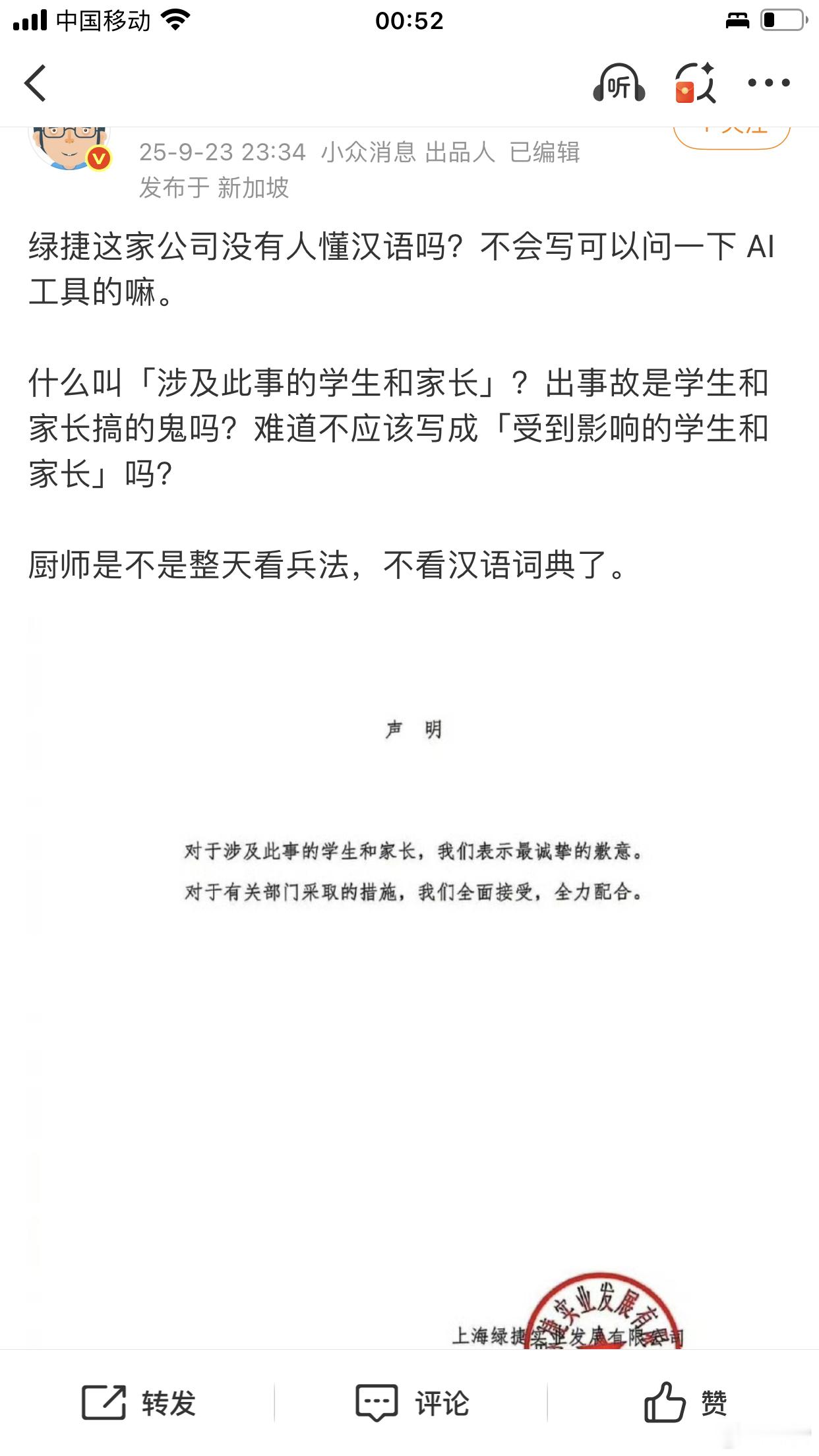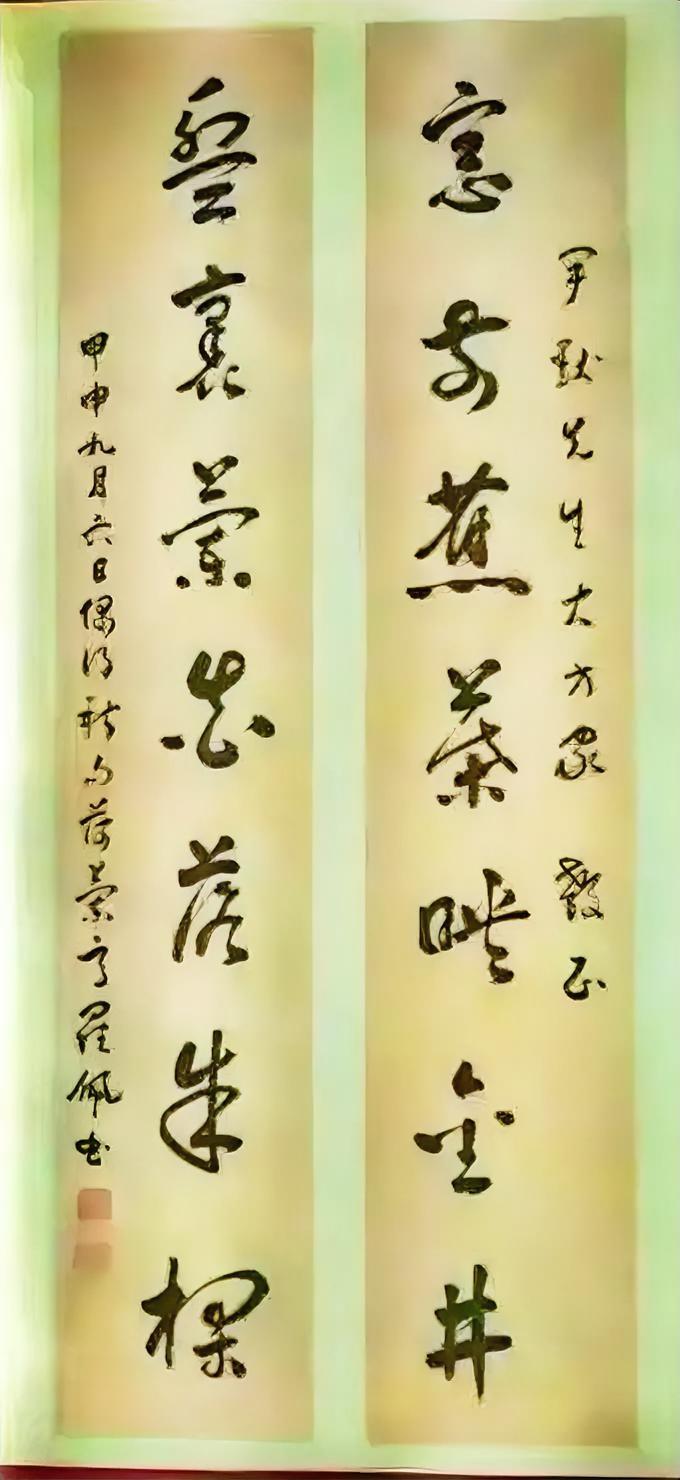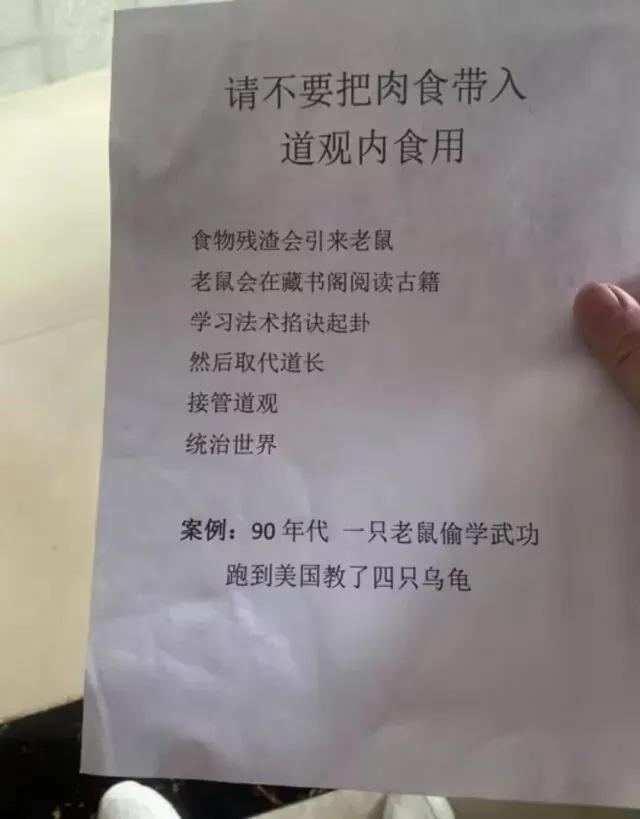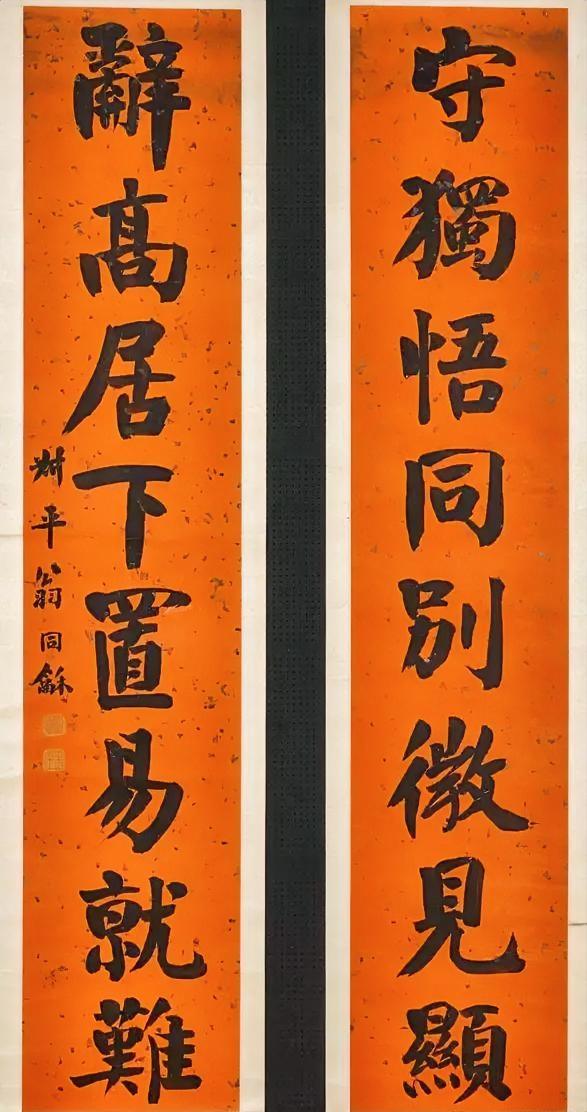宋代,苏东坡和一个和尚吃饭,饭毕他对身边的一个歌妓说:“和尚喜欢你,今晚你好好的侍奉他就寝,让他破戒了,我给你10两银子,还给你找个好人家。若是做不到,就要挨一顿板子。”歌妓满口答应,晚上就去了和尚的房间。 那和尚法号佛印,原是与苏东坡相交多年的好友。这夜月色透过窗棂,在禅房青砖地上洒下斑驳树影,佛印正对着一盏油灯抄经,忽闻门环轻响。歌妓推门进来时,带着一身江南水调的脂粉气,与禅房里的松烟墨香撞了个满怀。 “大师,奴家奉命前来。”她福了福身,鬓边金步摇叮咚作响。佛印抬眼,见她眉梢眼角皆是风月,却在烛光里透着几分难掩的局促。他放下狼毫,指尖还沾着墨汁:“施主深夜至此,怕是误听了苏学士的戏言。” 歌妓从袖中摸出块手帕,缠缠绕绕在指间:“学士说了,成与不成,都关乎奴家日后生计。”她说着便要解腰间罗带,佛印却忽然起身,从案头取过一件僧袍递过去:“今夜风寒,施主若不嫌弃,且披上暖暖身子。” 那僧袍带着日晒后的草木气,歌妓愣了愣,终究还是接过来裹在身上。佛印重新坐下抄经,笔尖在纸上簌簌游走,再没说一句话。窗外虫鸣渐歇,油灯芯爆出个火星,歌妓倚着墙根打了个盹,醒来时天已泛白,身上僧袍被人掖得齐整,案头摆着碗温热的莲子羹。 “多谢大师。”她捧着瓷碗,忽然红了眼眶。佛印合上书卷:“回去告诉学士,贫僧这禅房,容得下清风明月,也容得下施主一夜安睡。” 次日苏东坡见了歌妓,先问银子的事。歌妓把昨夜情形说了,末了从袖中摸出那方被僧袍熏得带了松木香的手帕:“学士若要打板子,奴家认了。只是大师的好,奴家记着。”苏东坡先是一愣,随即抚掌大笑,从钱袋里倒出银子塞给她:“这钱该给,不仅该给,还要多给。” 后来有人说,苏东坡这是故意试探佛印的修行。可细想起来,这场试探里最可怜的,原是那个被当作筹码的歌妓。她在权贵与僧徒的角力中,不过是片身不由己的飘萍。佛印的慈悲,或许不在于守住了清规,而在于他在那个夜晚,把她当作一个需要暖意的人,而非一场考验里的工具。 这故事流传开来,有人赞佛印定力深厚,有人笑苏东坡顽心不改。可少有人问,那歌妓拿着银子寻到好人家了吗?或许在那个年代,她的结局早已写定,不过是从一处樊笼,挪到另一处屋檐下。倒是佛印禅房里那盏油灯,后来总有人说,夜里会透出格外温柔的光,像是在照拂所有不得安宁的灵魂。 其实苏东坡与佛印的交往里,类似的机锋从未断过。他们曾在江上斗诗,在寺中论禅,苏东坡总爱用世俗之事逗弄佛印,佛印却总能以出世之心化解。只是这一次,玩笑里掺了旁人的命运,便显得不那么轻巧了。 想来佛印那晚抄的经,定是《金刚经》。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,他或许不是刻意要守住什么戒律,只是那一刻,对歌妓的体恤,比对苏东坡的输赢更重要。而苏东坡最后那句“多给”,与其说是认输,不如说是忽然懂了,有些底线,原是用来守护弱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