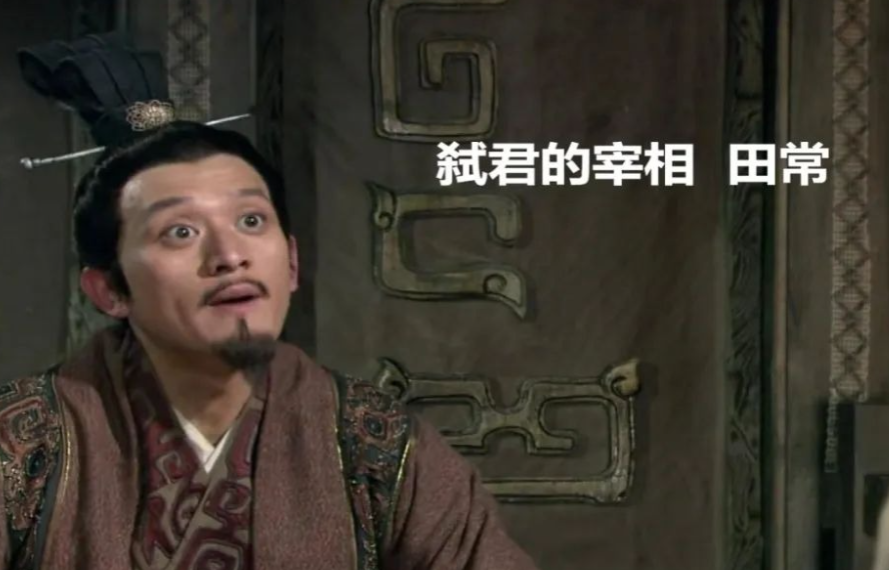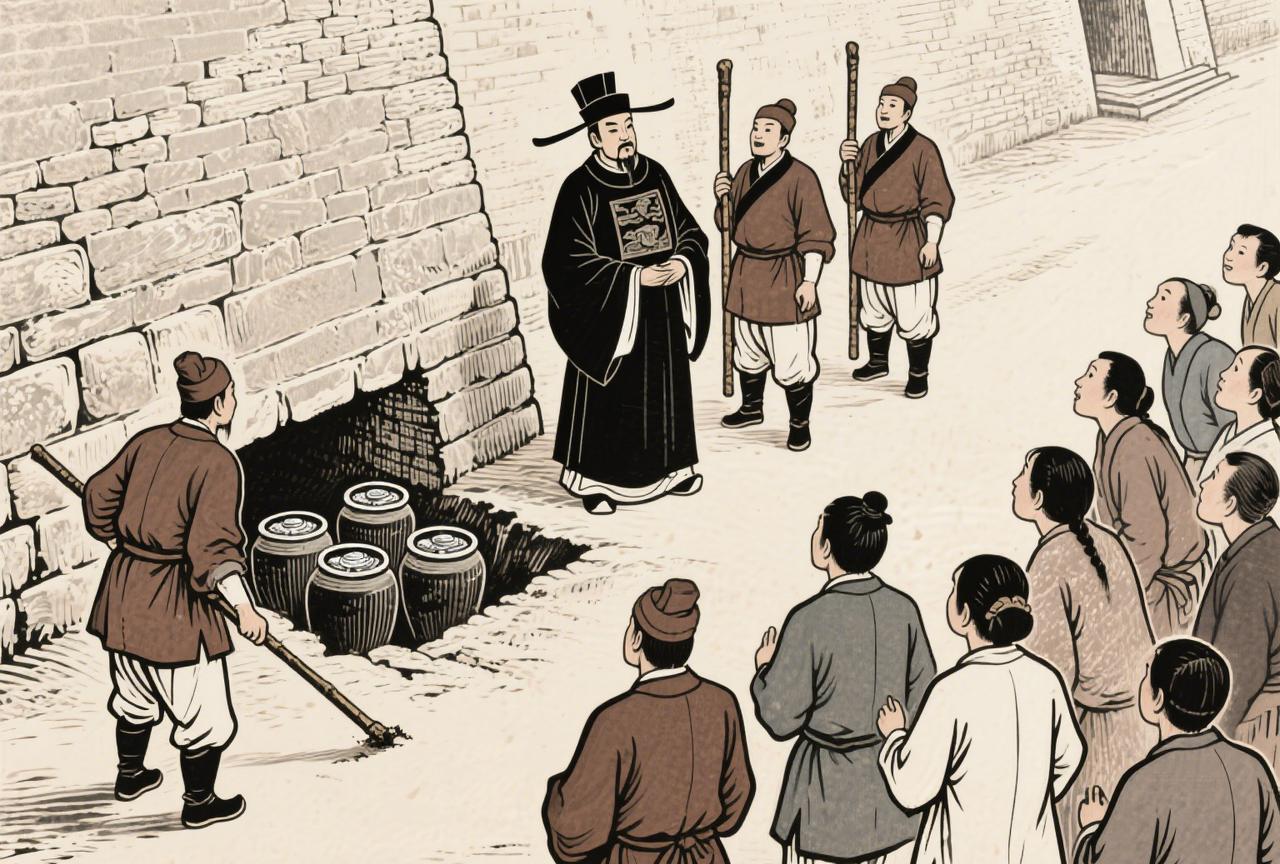春秋时,晋文公将爱女伯姬嫁与上卿赵衰。可没多久,伯姬哭着来找父亲,说自己宁为小妾,不愿当正妻。晋文公以为女儿受到了什么委屈,问明原因后,为女儿的决定拍案叫绝。 那日晋宫的铜壶滴漏刚过巳时,伯姬的裙裾还沾着赵府庭院的湿露。她跪在晋文公面前,珠钗散乱,却不是寻常闺阁女子受了气的模样,反倒像憋着股非要争出个道理的执拗。 “父亲,”她抬起脸,眼尾还挂着泪,声音却清凌凌的,“女儿在赵府住半月,瞧着赵叔的行事,方知这正妻之位,原不是金漆马桶——看着光鲜,里头装的尽是陈腐规矩。” 晋文公手里的竹简“啪”地落在案上。他记得伯姬自幼读《诗》《礼》,连绣绷上的并蒂莲都要依着《周南》的章法来绣,如今怎会说出这样的话? “前日里,赵叔陪女儿去看桑田。”伯姬绞着帕子,指甲掐进掌心,“田埂上有位老妇,抱着个穿粗布短褐的小娃哄。赵叔停下车驾,蹲下来摸那娃的脸,说‘这是赵氏第三代的种’。女儿问,这娃的母亲呢?赵叔叹口气,说原配夫人早年间难产去了,留下这遗孤。’” 晋文公眯起眼。赵衰的原配他知道,是狄人首领的女儿,当年随赵衰流亡时难产而亡,赵衰念旧,至今未续弦。 “女儿又问,为何不接个填房?”伯姬的帕子绞成了团,“赵叔说,填房也是要掌家的,若来了个厉害的,赵氏的田契账册怕要换了主人;若来了个软和的,又镇不住族里的长舌妇。倒不如让这孩子跟着我,我亲自教他行冠礼、读兵书。” 风掀起殿角的纱幔,吹得伯姬鬓角的珠花叮当作响。她突然跪直了身子,眼睛亮得像星子:“父亲您看,赵叔心里装的是赵氏的根基,不是自己的颜面。女儿若去做正妻,免不了要学那些高门贵女,防着妾室、管着仆从,把赵叔的心思都扯到内宅里。可赵氏需要的,是个能把后院打理得清净、让赵叔安心办差的人。女儿虽是公主,却也读过《女诫》——‘主中馈,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’。若能做个妾室,替赵叔分忧,岂不比当个名不副实的正妻更有用?” 晋文公突然想起二十年前,自己流亡狄国时,赵衰曾连夜翻山越岭为他找粮。那时赵衰的妻子正怀着身孕,却把最后半块饼塞给他。后来赵衰的原配去世,他在军帐里对着空了的卧榻坐了整夜,第二天还是照常去练兵。 “好个伯姬!”晋文公猛地站起来,衣袖带翻了案上的青铜酒尊。酒液泼在地上,他却浑不在意,“你当联这女儿是温室里的兰草?当年在狄国,你跟着我在草原上啃酪饼时,怎么没学那些娇滴滴的做派?” 伯姬破涕为笑,发间的玉簪歪到了耳后。她想起昨日在赵府,赵衰的庶子拽着她的裙角要糖,她蹲下来给孩子擦了擦鼻涕,又把自己腕上的银铃解下来系在他脖子上。孩子咯咯笑着跑开时,赵衰站在廊下看了许久,末了对她说:“你比我那死去的夫人,更会疼孩子。” “明日,联便让宗伯去赵府传话。”晋文公弯腰扶起女儿,指腹蹭掉她脸上的泪痕,“赵衰的嫡妻之位,你不当;可赵氏的‘内助’之位,非你莫属。联倒要看看,满朝文武谁还敢说联的女儿只会哭哭啼啼!” 三日后,赵府的张灯结彩换成了素绢。伯姬穿着月白襦裙,头上只戴了支青玉簪,跟着赵衰去拜见宗庙。族里的老人们交头接耳,说这哪像个上卿夫人,分明是哪家大夫的庶女。直到赵衰拉着她的手站在祖宗牌位前,沉声道:“这是晋侯之女,赵氏之辅。” 那天夜里,伯姬坐在赵衰的书房里,替他整理军报。烛火映着她的侧脸,赵衰忽然说:“你可知,我原配临终前,抓着我的手说‘莫负赵氏’。”伯姬头也不抬,将一卷兵书码放整齐:“我知道。可我也知道,赵氏的未来,不在‘正妻’两个字上。” 窗外飘起细雪,落在伯姬摊开的《诗经》上。她翻到《桃夭》篇,轻轻念道: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”声音轻得像落在雪上的羽毛,却让赵衰的眼眶微微发酸。 后来,赵衰的庶子成了晋国的名将,伯姬教的《孙子兵法》起了大作用。而赵衰每每提起这位“侧室夫人”,总说:“我家内助,比那些正牌夫人强十倍。” 再后来,史书里记了一笔:“晋文公女伯姬,嫁赵衰为妾,佐其治家,赵氏以安。”可民间更爱传一句话:“公主不当正妻,要当就当顶梁柱。” (信息来源:基于春秋时期婚姻制度及晋文公、赵衰相关历史背景合理演绎,核心情节为文学创作,旨在通过人物对话展现春秋女性对婚姻与责任的独特理解。文中人物关系及部分细节参照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史料记载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