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1年,一位在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的市方志办的女同志突然嚎啕大哭,吓坏了一众工作人员。她举着一摞信哭着说“这是我爸爸写的,我要带走”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,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,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,感谢您的支持! 2001年夏天,在上海市档案馆里,一向只有翻阅资料的声音,却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猛地打破,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,望向一位中年女子。 她叫“王佩民”,此刻她正死死攥着一叠发黄的信纸,泪流不止,嘴里只重复着一句话:“这是我爸爸写的,我要带走。” 这场突如其来的失态背后,是一个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,她的父亲,正是“王孝和。” 王孝和这个名字,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只是历史书里的一行字,他1924年生,牺牲于1948年,牺牲时年仅24岁。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曾是上海电力公司的骨干,也是一名地下党员,虽然他手里没枪,却在最危险地方,用自己的方式战斗。 可谁也没想到,叛徒的出卖,让他的人生戛然而止。 被捕后,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,但他从头到尾一声没吭,更没有泄露半个同志的名字,他的沉默,保全了整个地下组织。 也正是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,他用铅笔头在粗糙的草纸上,给家人写下了四十多封信,字迹潦草,甚至夹杂着暗语和错别字,只是为了躲过审查,让家人能看懂那份深意。 信里,这位年轻的父亲,反复念叨着那个还未出世的孩子,早在1947年的第一封信里,他就给女儿取好了名字:“佩民”,盼着她能“佩戴着人民的希望”长大,还盘算着要给她买一把银锁。 信中既有对家庭的无限牵挂,也有对事业的决绝:“厂里的工友们都信我,再难也要把罢工坚持下去。” 在牺牲的前三天,他写下最后一封信,纸上还带着血迹:“玉英,我对得起国家,对得起工友,唯一对不起的是你和孩子,告诉佩民,爸爸是为信仰而牺牲,不丢人。” 他的妻子“忻玉英”,同样是个战士,丈夫在法庭受审时,怀着九个月身孕的她不顾一切冲了进去。 当她看到丈夫遍体鳞伤的样子,当场崩溃,她的哭声点燃了旁听席上工人们的怒火,抗议声浪瞬间压倒了法庭,行刑因此被迫中止。 但几天后,敌人还是秘密处决了王孝和,他走向刑场时,神情镇定,甚至带着一丝微笑,衬衫的第三颗纽扣扣得整整齐齐,因为那是妻子亲手为他缝上的。 而忻玉英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战斗,她曾偷偷给罢工的工人送馒头,还曾将丈夫的情报巧妙地藏在煤球里送出去。 王孝和牺牲三周后,忻玉英拖着因悲伤过度而风瘫的身体,生下了女儿,取名“佩民”,她独自一人靠着缝补洗衣,含辛茹苦的将女儿拉扯大,却几乎从不提丈夫的事。 直到十岁,王佩民才从奶奶口中,对着墙上的遗像,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烈士。 但课本里找不到他的名字,报纸上也只有一句“电力工人王孝和英勇就义”的剪报,父亲成了一个模糊而遥远的符号。 成年后,王佩民进了史料部门工作,总会下意识地寻找“王孝和”这三个字,她常常寻访父亲当年的战友,从他们口中拼凑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,一个在酷刑下沉默如铁的硬汉。 直到1994年迁墓,她终于见到了父亲的遗骨,棺盖打开的瞬间,她跪在地上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 母亲在临终前,交给她一个布包,里面是那四十多封家信,一张带血的纸条,上面写着“佩民吾女,爸爸永远看着你”,还有一枚银锁,刻着“为民”二字。 而这枚锁,是父亲在狱中由工友们冒死送出。 直到2001年,当王佩民在档案馆的“工人运动档案”里,亲手触摸到那批官方保存的、父亲用生命写就的信件原稿时,压抑了大半生的情感终于找到了出口。 她这才真正读懂了父亲,读懂了“佩民”二字背后的深意,“佩”是佩服与铭记,“民”是人民,是父亲为之奋斗牺牲的一切。 自那之后,王佩民常常前往龙华烈士陵园,每次前去,她都会带上一支白玉兰,那是父亲在信中提及的花,并且,她开始讲述父亲的故事。 有一次社区讲座,她读到信中“要教孩子做正直的人”,台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突然站了起来,抹着泪说:“我认识你爸爸! 当年他为我们争取工资,被打得头破血流,还笑着说‘会好的’!他没有白白牺牲,你看现在工人们的日子多好。” 直到2005年,王佩民带着自己的女儿参观上海工人运动纪念馆,女儿指着外公年轻的照片问:“外公不怕吗?” 她想起信里的内容,温柔地回答:“他怕过,但他更怕大家永远受欺负,”到了2018年,她将那些珍贵的家信原件全部捐赠给了纪念馆。 现如今,上海工人运动纪念馆里,王孝和的展柜前总是站满了年轻人,他们看着那些泛黄的信纸,听着英雄对家人的牵挂,才发觉一个更真实的道理。 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它藏在危难时的坚守里,也藏在对家人的责任和对后辈过上好日子的期盼里,有些精神,确实不会过时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,静静地流淌。

![谁告诉你上海人精致的?你怕是没见过上海的土著穷人有多穷吧?[捂脸哭][我想静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7757283050861488364.jpg?id=0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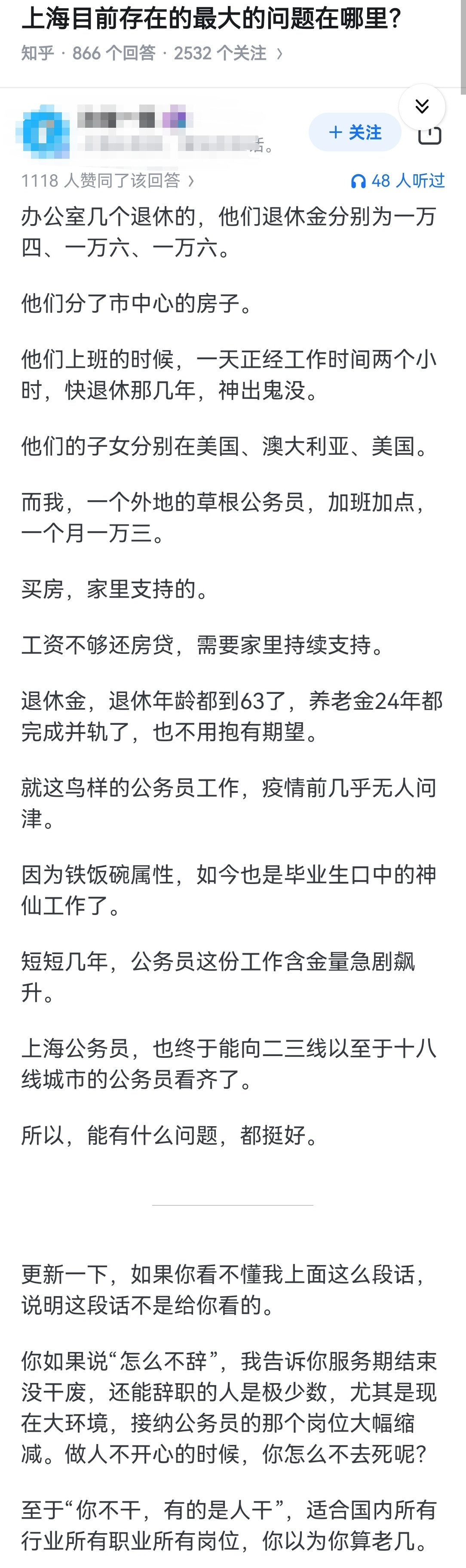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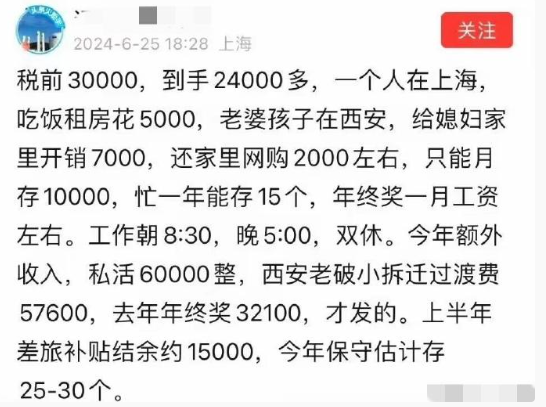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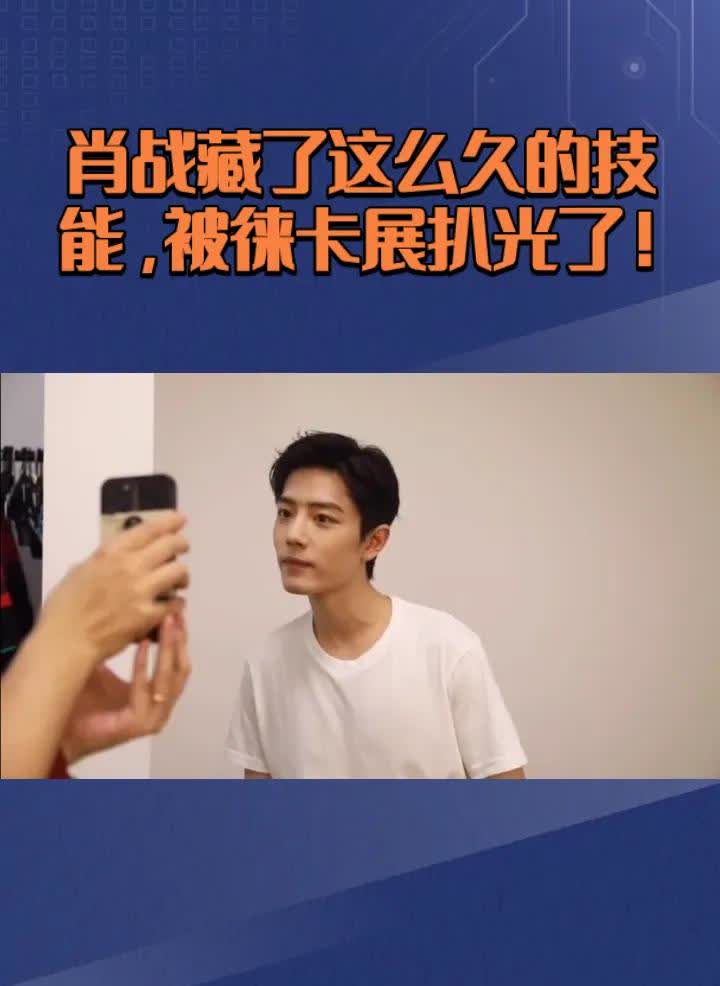

意见
[赞][赞][赞]